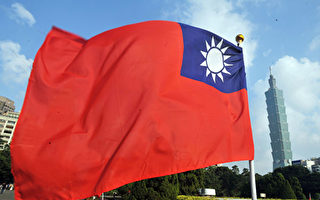【大纪元8月1日讯】
2006年7月12日,星期三,晴,耶路撒冷
今天前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暑校报到。
想起今后几天上网不方便,早起便浏览了一下网上新闻,看见北部边界发生冲突,报道说有两名士兵受伤。想想自从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尽管联合国早已认定以色列撤出了全部黎巴嫩领土,但真主党恐怖组织仍然不时越界制造冲突,挑起矛盾,每次都以以色列妥协而告终。这次既然规模不大,以色列方面损失有限,估计不会恶化。所以并未特别留心。
中午赶到耶路撒冷,先在希伯来大学Givat Ram校园旁边的五星级酒店办好入住手续,随后进入校园,到暑校办公室报到。
这个暑校每年只举办一个礼拜,年年的主题都不一样,但都是社会人文方面的。主办方依主题从世界各大学选取相关研究方面的一流学者作为师资,每人主持一个半小时的研讨班,包括一个小时的演讲和半个小时的研讨。通常入选的都是成名学者。而我的研究方向上全世界也没几个人,一流末流都是一回事,所以今年滥竽充数,居然也被邀请来主持一个研讨班,深感“与有荣焉”之幸。
其实这个暑校比师资更有特色的是学生,那是从世界各名校选拔出来的优秀犹太裔研究生。今年的二十多名学生几乎都来自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欧美名校,而且每校只有一个名额,由当地教授推荐录取。不言而喻,这暑校的目的是聚拢世界各地的犹太青年才俊,在享受与一流学者对话机会的同时也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络,培养他们对犹太祖国的亲近感。
暑校的待遇也非同凡响,海外来的学生学者都享受免费机票。所有参与者只要愿意,都可以在五星级酒店获得一个星期的免费住宿。早餐由酒店提供,午餐在校园里的一个有相当档次的小自助餐厅进行,标准比我参加的几次接待部长级官员的午餐还高。晚餐自理,不过每个人都获得了高额正餐补贴。为了让这笔补贴不会形同虚设,主办方专门向参加者提供了一份耶路撒冷高档餐馆推荐名单,上面各餐馆的菜式、风格、电话地址一应俱全。
主持研讨班的教师没有报酬,不过考虑到每人其实只讲一个小时,那一个礼拜的宾馆加餐费补贴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授课报酬标准。可惜我俗务缠身,竟无暇充分享受,只能在我的研讨班开课前一天赶到。
下午旁听了一堂研讨课,一方面对相关题目有兴趣,另一方面也想熟悉一下学生的情况。主办方在开始时介绍今天的主持教授,只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某某教授,如果有人还不知道某某教授的话,现在就可以离开教室了。”一句话说得我如雷灌顶,心想这才是大学者的境界吧,那些靠一堆头衔和著作来唬人的学者只好算等而下之了,只是不知还要做多少年苦功,才能当得起这么一句评语。学生们看来都认真预习了指定书目,问题问得精彩纷呈,热烈的讨论在下课时竟无法停止,拖了十五分钟才下课。
五点钟回到宾馆,打开电视看新闻,才知道北方的冲突比最初的报道严重得多:在以色列边界巡逻的以军惨遭偷袭,至此已知七名士兵死亡,两人遭恐怖组织绑架。电视画面右下角的醒目标题文字是:“打回黎巴嫩去!”
给朋友Y君打电话。Y的儿子正在当兵。本来服役时Y走了门路,让儿子在军中某机关坐办公室。儿子知道后跟老爹大闹一场,非要到野战部队去,并且向上级提交了请调报告。几经周折,请求终于被批准,被调到某装甲部队,驻扎黎以边界。事件发生后,Y不知为何无法跟儿子联系上,此时全家正焦急不安地坐在电视和电话旁边,一边打电话四处询问,一边惴惴不安地等待电视新闻宣布伤亡士兵名单,祈祷自己的儿子不在其中。
随后又拨通L君的电话。六年前我认识L的时候,他还是位绝对的左翼和平人士,去年单边撤退时,他是撤退的坚定支持者。不过此时愤怒已经让L彻底改变了立场:“我弄不懂我去年怎么会支持撤退。看来那些定居者是正确的,应该把定居点修到黎巴嫩去。”
随后想起今天研讨课上学生的表现,便觉得还是把课再预备一下的好。于是关掉电视,开始看资料。
太太九点才到。天色已晚,就在酒店底层的饭馆用餐。离开房间前又看了一眼电视新闻,知道黎以边界已经是战火连天。餐馆里的气氛却一切如常,钢琴在流畅地演奏肖邦的优美旋律,美丽的女侍者微笑着抱歉说今天的厨师特色菜已经卖完,于是点了一份烤幼仔鸡,太太点了一份主餐沙拉。连饮料算一算只花掉我每日正餐补贴的一半都不到,而这差不多已经是耶路撒冷最贵的馆子了。起身回房时钢琴忽然变奏《祝你生日快乐》,角落里一桌人家欢声笑语,正在庆祝生日。
2006年7月13日,星期四,多云,耶路撒冷
早起看新闻,知道开战已成定局。以色列民意出现前所未有的一致,除阿拉伯人外,左中右均感真主党欺人太甚,今日不冒北方陷入战火硝烟之险,则明日必遭此辈阴险毒手。
因为要用多媒体材料,遂提前半小时赶到教室。大半学生已到,都在旁边的咖啡室享用咖啡蛋糕。跟学生们随便聊聊,发现虽然都是犹太人,秉性却大为不同,欧洲学生大都彬彬有礼,美国学生活泼大方,以色列学生则是一贯的热情豪爽,围上来抢着告诉我他的哪个亲戚在中国,哪个朋友跟中国联系密切,以跟中国有关系为荣,这是时下以色列的风尚,不足为怪。
研讨课进展顺利。出乎意料的是学生的问题并不多,留出来的半个小时问答时间几乎全成了我跟暑校几位旁听教授之间的问答。讨论极为热烈,直到吃午餐时还有人来继续讨论相关问题。
两百公里之外是烽烟四起,炮声隆隆。校园之内则师生济济,坐而论道,整个上午无一字提及时局。
下午暑校组织旅游。耶路撒冷那些胜地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了,便没去参加。携妻在Givat Ram校园漫步。这个校园建在耶路撒冷西部的一座山上,东坡是以色列国家植物园。虽然已是旱季天气,校园内仍然奇花斗妍、绿草如茵,苍松翠柏掩映林间小径,实在是以色列最美的大学校园。因口渴找水,忽然想起十三年前初到以色列时,曾在该校园南端简陋的“阿莱夫”宿舍住过一个月,那宿舍旁边有个简朴的小超市,十三年过去,不知那宿舍和超市是不是还在。走到南端,看见宿舍居然还是老样子,那小超市不但还在,而且连内部格局都没什么变化,十三年前放面包的那个角落放的居然还是那种政府补贴的长圆形廉价面包。那时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又兼囊中羞涩,大米面条都嫌贵,只有这种面包吃起来不心疼,于是天天吃,顿顿吃。如今这种面包香味再次扑鼻而来,把我带回到十三年前的那个八月,仿佛又看见自己在月影稀疏的松林山路间踽踽独行,恍如隔世。
买了两瓶无酒精冰镇黑啤,坐在离宿舍不远的草地树荫下小憩。记起当年进宿舍第一天,迎面的墙上便贴着一条黄蓝色的小标语:“以色列国已到危机关头,禁止卖国!”那是中东和平进程刚起步的时代,反对派也刚刚开始活动,但似乎人人都对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十三年过去,无数仁人志士为阿以和平呕心沥血,乃至流血牺牲,然而努力越多,灾难越重,无论对哪方来说,都是和亦错,战亦错;进亦错,退亦错;动辄得咎,无往不败。十三年的努力连个和平的影子都没换来,冲突反而越来越血腥,今日更或许发展成一场全面战争。也许阿以冲突确实标志着人类智慧的极限,我们或许有能力征服自然,却永远没有能力征服自己。也许真如《圣经》所言,这块土地的生生息息乃是鬼斧神工之造化,人的谋略,只能让神发笑而已。
晚上是暑校的结业晚宴,地点在市中心一家有名的烤鱼馆。馆子在旧城区小街一栋两百年的老宅里。小街错综复杂,没开多远就迷了路。在路边停下看地图,一名显然是下班回家的犹太白领停下来问:“我能帮忙吗?”听清情况后,他看了看我的地图,说这一带的街道改造过了,我的地图已经太旧。随后开始解释如何开到那里去。大概是看出我脸上的表情仍然迷惑不解,他竟一伸手拉开后车门,坐进了车里。“走吧,我带你们去。”他说。沿途聊起来,他一天都从收音机里关心北方战况,急着回家看电视新闻。我们一边开车,一边深感不安。他工作了一天下班回家,还急着去看有关战况的电视新闻。饭馆在他回家的反方向,这意味着他把我们带到饭馆后要多走不少路才能回家。“没关系,今天的天气适合走路。”他安慰我们说。车到饭馆,他还指引我们找到停车场,跟守门的阿拉伯人讲好价钱,看着我们停好车,这才匆匆告别,消失在暮色里。
晚宴上师生之间的气氛仍然欢洽如初,仿佛完全没有战争冲突这回事似的。主菜点了一道蒜蓉汁烤红鼓鱼,那鱼段的脂肪留得恰到好处,吃起来鲜嫩无比,香气扑鼻,唯一的遗憾是黑胡椒研得太细了一点,吃起来缺少若隐若现的辛辣感觉。北方战事正酣,不过是两百公里之外的事情。而此刻我坐在耶路撒冷的夜色里,唯一的不满是美味烤鱼里的黑胡椒研得太细。
对面坐的是暑校一位德国教授的太太。聊起来她七十年代初在以色列长达数月的旅游经历。她说那时她在被占领土与以色列本土之间自由出入,如履平地,而且本地的犹太人阿拉伯人也同样自由来往。她在加沙、伯利恒等地都待了不短的时间,那时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水平跟以色列相去不远,最重要的是:虽然她有意询问,却几乎感觉不到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敌意,敌对活动也很少发生,即使发生也多半是外来的武装分子所为。曾几何时,天翻地覆,两边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死敌。看来把这里的事情弄糟并不始于九十年代的和平进程。人类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越做越好的希望,似乎唯独在这块土地的冲突问题上总是越弄越糟,直到不可收拾。
晚宴结束,国外来的师生都成群走向等在两条街外的巴士,当我们开车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认出了我们。虽然刚刚道过别,却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所有人都挥起双手,兴高采烈地向我们呼叫起来。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在战争迫近的时刻,我内心的平静从何而来。举天下之精英而尊崇之,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本中国传统人生第一大快事,也是犹太人生的第一快事!人类的力量,原不在于强悍和凶蛮,而在于理性与智慧。在我刚到以色列时,便有一位长者告诉我说:“以色列的出色之处不在于打赢了所有战争,挺住了所有压力,而在于在几十年的战火硝烟之中仍有能力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进行一流的研究。在这个麻烦不断的小国里,你仍然能够看到有人在研究艰深的中国哲学问题,而且是高水平的研究。”的确,当犹太复国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军事或者政治机构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建起了一座像样的大学。而当今天你坐在希伯来大学由一流的学生学者构成的课堂里进行精彩纷呈的讨论时,你不会相信两百公里以外的战争会以以色列的失败而告终。这种自信不仅限于眼前,而且包括未来。金钱有易手的那一天,石油有用完的那一刻,真正取之不尽的是人的智慧,是眼前这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课堂。人或许无力改变神的诅咒,但当他面对另一个人的时候,未来把握在他自己的手中,把握在他自己的智慧之中。
2006年7月16日,星期天,晴,特拉维夫
半夜到家,倒头便睡,上午被电话铃吵醒,拿起一听,是老欧。电话显然是从街上打过来的,远远的似乎有救护车或者警车的鸣叫。
“我在海法呢。”老欧说。
“海法?”我还睡意朦胧。
“你没听新闻?真主党的火箭打到这儿来了,刚才收音机里说死了九个人。”老欧说。
“那你还在那儿干什么?”我开始醒过来了。
“无所谓,我打电话根本就不是为这事。你能不能打开《老子》,我有个问题问你。”老欧说。
海法、火箭、伤亡、《老子》,弄不懂这些东西怎么扯到一块儿了。不过我打开了《老子》。
“六十四章。”老欧说。
原来老欧今天约好跟一个朋友讨论《老子》,到了海法,突然想起六十四章的那几个“其”字不知道怎么解,为了在朋友面前露一手,便给我打了这个电话。
那时海法的街头已经空了,居民早已躲进掩体,饭店商场均已关门,真主党的火箭随时还可能打到。老欧却在空旷的街头给我打电话,讨论了半个小时的《老子》第六十四章的那几个“其”字。
于是恭录《老子》六十四章如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
持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持,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
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
所过。以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
张平 2006年7月17日 于特拉维夫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