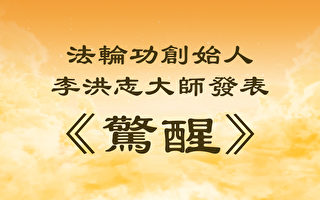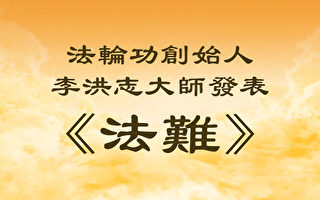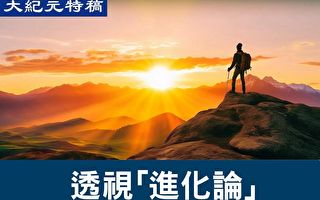【大纪元7月17日讯】来安庆之前,就被这里的大把人杰地灵深深吸引着……从乾隆二十五年至1938年,其间170多年,一直是安徽省府所在地。既然是安庆文化徽州商人构成“安徽”二字,自然在人文上地理上大有其可观之处。
“桐城派”诸位大文豪、陈独秀、徐锡鳞、邓稼先、赵朴初﹔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辛亥革命徐锡麟起义、安庆马炮营起义……古往今来,这些同安庆息息相关的人物与事件莫不在黄梅戏的闲牌散韵中任时光静静淘漱着,把自己的功过荣辱交给了茶馆中的后人品评。
出差办完事情迫不及待地在城中四处游走一番,印象至深的是迎江寺的振风塔和陈独秀墓园。
迎江寺位于长江之滨,寺中无非佛祖菩萨金刚罗汉,雕艺上无一例外地佛祖欢喜、菩萨慈悲、金刚怒目、罗汉怪异,各地同一版本,全部似曾相识。倒是寺中的那座七层高的八角振风塔与全国各地的各处宝塔颇颇不同。外观上看来古朴憨重,与兄弟产品并无二致,等到攀延而上时才发现别有机关。上下都难,上完一层楼梯找不到另一层的台阶,有时转够三百六十度有余方才如获至宝地寻到一条出路,忙不迭地跑上去却又早忘了来时的途径,莫名其妙闯到第七层塔顶算是到了头,用不着极目远眺,便已俯瞰长江和江面上的点点货轮。上午的一场倾盆大雨似乎把江水翻转过来,混浊的江水既不波澜汹涌,也不波平如境,就这样昏昏黄黄地荡溢着,分不清到底是长江还是黄河。如今的江船早已是有船无帆,“孤帆远影”的盛景同样只能出现在影视剧中剧了。回过头来还是觉得这塔虽始建于明代,数度翻修依然形神不改。相传该塔是为了振兴文风所建,400多年来的“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也许就是借了塔的钟灵之气才得以文风大振,想来设计者——当时的北京白云观老道人张文采一定是个妙人儿!放在今天一定是位“高工”,而这塔也因了他老人家的奇思妙想方不枉了“长江第一塔”的英名。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知他老人家是否救过人命,但退而求其次这塔却造得绝无仅有,他想告诉后世什么?世间本无坦途须历经寻觅方可登峰?来路与去路本无更改却来时找不到去路去时记不得来路本是庸人自扰?还是世间的复杂远远不是文人的想象?又或者老道士原本就是个老玩童仅想同后人开个玩笑而已,徒留后人牵强附会同我一样傻呵呵地胡猜乱想?
在进士与状元随着大清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远远流走之后,陈独秀这个晚清小秀才也愤然脱冠,径直走出安庆去领导了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史上也由此嵌入了一位不可或缺的领袖人物。也许历史真的是越久远愈清晰愈公正,无论如何他的墓园和纪念馆再不必隐姓埋名了,墓地周围那浓厚的绿意仿佛上天伸下一只巨灵之掌也不能一把抓透,在中共这个政治环境下虽则连块刻写生平的墓碑都没有,但葱郁无边的草树依然让人感到那是老夫子冥冥之中不息的学者之气。胜者王侯,对王者大量的褒溢之词,公众似乎早已乏味而麻木,而对于讳莫如深的人物和事件却由好奇心及潜在的崇敬感驱使着亟欲一探究竟。
晚景下孤独的大理石白坟包有些落寞,满目的绿色渐渐变得幽暗。双层的汉白玉栏杆围不住这一刻黄昏的苍凉,盛夏的微风中一大群乱飞的麻雀吱吱叫着忽地落在几棵松柏树梢上,青白的石质摸上去有些湿漉漉的。陈独秀毕竟是改写一个时代的人,想想前不久连战与宋楚瑜拜谒中山陵的煊赫,此刻的孤坟益形影只。听过一句西谚——孤独只属于固执的人。固执于学问让他学富五车,固执于于信念让他五度进出牢房,最终固执己见也让他失去了一片江山……天黑下来了,霎时间我有些分不清固执与忍耐有何质的区分与共性。
好象没听说三位夫人中哪位陪他沉睡墓中,情感上顺理成章地应该属于第三位潘兰珍女士。如果说前两位所嫁的陈独秀是秀才和教授,这位女士所追随的却只是个政途不济的落迫文人!在陈氏退出政坛埋头深巷最狼狈最惶惑的日子里,兰珍女士在很久都不知其真名实姓的情形下,只出于对文人的怜惜与仰慕遂携手相伴,陪他走过了颠沛流离的晚年。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位肯付出的无私女人,但成功之后走向衰退的男人背后的女人又岂是“无私”二字所可包容?人性的伟大似乎只有在落寞与失意中的持之不懈才更能详释得淋漓尽致!可悲的是陈独秀在中共内部斗争中被赶下台时,得不到救助,连2位优秀儿子都被内部出卖致死,人生之悲!
一位同伴采了一大束野花放在了墓前,我想这束花更该献给潘兰珍女士!(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