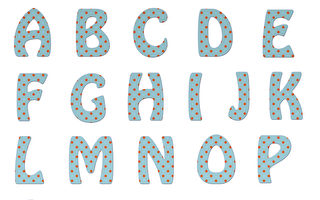【大紀元2016年05月26日訊】讀阮毅成先生《八十憶述》,他在小學時代留下的一篇作文吸引了我。他生於1905年,幼時在江蘇興化上過私塾,1917年隨伯父、當時有名的律師阮性存到杭州,考入杭縣縣立第二高等小學。小學時代的老師,給他印象最深刻、也是影響最深遠的是兩位國文老師,教他寫白話作文的張元孟先生,教他寫文言文的趙敏栽先生。趙是前清的秀才,不但講解精詳,改作文也十分用心,有眉批,有總評,有圈點。而且每改一字,必說明原因,如果他下次也沒有注意,先生就會說:「我對不起尊大人。」直到晚年他還保存有當年的作文簿,並錄了一篇在書中。這篇作文題為《民為貴》,只有短短三百六十字:
處今日共和之時代,莫不曰尊重民意矣。若戰國時代,國君好行專制,大權在於一人,人皆知有君,不知有民矣。君之視臣如土芥,君之視民,更犬馬奴隸之不若矣。惟民貴之說,孟子能首倡之。亦謂國無民,何以為國;君無民,何以有君。國祚有短長,而民意無盛衰也。國運有否泰,而民志無變遷也。是以國政有改革,而民氣初無常變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書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而知天心,即民心也;民意,即天意也。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誰謂民不當貴哉!然而國家既眷念斯民,而人民何以報答夫國家?果其蒿目時艱,為士民者,必先立志。不存苟安之意,不為無用之學。研求政法,可以利濟夫蒼生。探討科學,可以裨益夫社會。開士民之風氣,備國家之任使。藏器待用,固人民之素志也。經濟匡時,亦人民之願望也。人能若是,庶幾不愧為共和國家之國民也歟!
他曾出任浙江大學、台灣大學法學院教授,有法學著作存世,也有豐富的從政閱歷。他在作文簿中任選的這一篇,只是想說明當時對國文教學的重視,與小學生的國文程度。我從中看到的卻是那個時代小學生的大關懷,口氣中露出的不僅是老到,更有「共和國家之國民」 的擔當、責任意識。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就關心「民為貴」這樣的大題目,不管是出於老師的命題,還是學生自己的選題,都讓人心生感慨。他不是一般地闡述孟子的「民為貴」舊說,而是放在新的共和時代背景下,思考這一古老的說法。作為一個小學生,他還沒有能力展開長篇大論,但在短小的篇幅中,他已觸及許多有價值的方向。言雖短,意甚長。
阮毅成此文不是一個個例,生於1904年,曾多年任清華、北大、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的葉公超,也保存了一本南開小學就讀時的紅格子作文簿。其中一篇作文《論團體之精神》,雖老師點評:「劈頭破題,一針見血,惜哉而血不多!」但所論之問題也甚大。翻開《周恩來早期文集》,比他們年長一些的周恩來(生於1898年),小學和中學時代留下的多篇作文,也都與此呼吸相通,比如1914年9月的《愛國必先合群論》、1915年的《共和政體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於人論》,後一文是對孟德斯鳩有關共和精神的闡述。
他們雖處少年時代,落筆之際卻不忘國家社會、人類福祉,議論常溢出個人生活的範圍,超過了年齡的限制,其氣度、格局都有大國民風範。在白話文普及之前,這些文言寫下的作文傳遞的已不是古老的傳統價值,而包含了許多新思想的萌芽。我想起那個時候的小學生課本,關於共和、國民之說,在國文、新修身等不同課程中都有,被學校廣泛採用的商務印書館《共和國新國文教科書》高小第四冊有《大國民》的課文(沿用的是晚清《最新國文教科書》),很好地回答了甚麼是「大國民」:「所謂大國民者,非在領土之廣大也」,非在人數之眾多也,非在服食居處之豪奢也。所謂大國民者,人人各守其職,對於一己,對於家族,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對於世界萬國,無不各盡其道。」
那個時代的小學生筆下關懷之大,立言之高遠,毫無疑問與教科書的熏陶有關,與那個時代的氛圍有關。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教科書,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教育,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風氣,由此陶鑄出來的一時代的學生,誠然因個人性格、選擇、機遇之不同,所走道路乃至各人命運也各不相同,但他們身上仍深深地打上了相似的時代印記。由小學生的作文看一個時代,只是以管窺天,卻也未嚐不是一個有意思的視角。
文章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