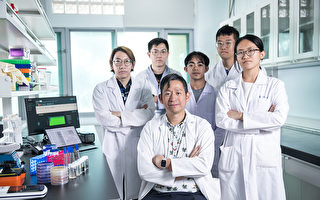【大纪元2012年12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廖凤琳台湾报导)过去20几年来,许多受害台商几乎都有如出一辙的惨痛经验:跟中国大陆方面的人打交道、谈生意,开始的时候,对方会十分客气地给出方便条件,提供各种利益诱因,让投资者对远景产生一种憧憬,愿意出资出力全面配合。然后慢慢地被一步步引入彀中,等意识到情况不妙时,往往已深陷泥潭,难以抽身。
面对“不按牌理出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中共治下,由上到下,一贯娴熟的蓄意枉法,多少台商受骗上当后,游走两岸寻求奥援或以血泪控诉,至今仍无任何一件获得圆满解决的案例,金钱财物的损失是其一,时间、体力、精神各方面的虚耗、折损、伤害、更是难以估计。
年轻台商洪光佑的受害经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付出了超过1亿元新台币的昂贵代价,买到一个教训后,才从恶梦中惊醒,时隔多年,回想起来,仍令他感到扼腕不已!
从家族经营的远洋渔业启航
洪光佑的父母是澎湖人,早年到台湾来创业,靠着一步一脚印的努力奋斗,建立了包括营造、建设与远洋渔业等跨领域家族企业,为儿女们的人生道路铺奠了深厚基础。
洪光佑的父亲在澎湖并没有渔家背景,但不乏讨海维生的亲友,多少耳闻过别人的经验。迁居到远洋渔业大港——高雄后,受到当年政府奖励投资“鲔鱼船钓”政策的影响,一开始是出资入股朋友的渔产公司,让他看到远洋渔业市场的开发潜能,前景可期。
1990年,便正式成立了家族企业“百隆渔业公司”,并独资打造了一艘全新的700吨大型远洋鲔钓渔船,命名为“百隆六号”,以船东身份,经营鲔鱼远洋捕捞生意。
洪光佑在高雄出生、成长,上有两个兄长、下有一个妹妹。身材壮硕,谈吐斯文的他,承袭了父母纯朴笃实的作风,从小到大,一直保持单纯率真的本色处世待人。洪光佑高中毕业,服完兵役后两年,正好赶上父亲投资渔业项目,时年26岁的洪光佑,便跟着父亲一起创业,父亲赋予重任,要他协助渔船经营管理工作。
虽然缺乏社会经验,但洪光佑满怀理想,在业务推展、营运销售的实做努力中,开拓了家族事业版图,公司扩展很快,短短几年时间,又向日本方面增购了两艘二手同类型鲔钓船,加入行列,壮大了百隆渔业规模。
误信中共国企可靠 大举投资华隆海运
然而,鲔鱼在国际市场一直是需求竞争激烈的鱼种,大量滥捕的结果,公海渔获量逐年减少,在国际鲔鱼限量捕捉的规定下,洪光佑的鲔钓船相对受到冲击,后来不得不将“百隆六号”鲔钓船转售出去,留下另两艘维持在大西洋海上作业,百隆渔业公司的远洋鲔钓船舶主要在大西洋海域渔场作业。
1994年期间,渔船在西班牙管辖的非洲迦纳利群岛靠岸,做加油补给的短暂停留,期间认识了大连水产集团在西班牙的子公司“华连”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宣政,在西班牙,他是大连水产国有企业的代表。当时中国沿海,渔产资源有减少趋势,大连水产集团于是投资非洲去开发海外市场。
洪光佑一开始,得到过对方一些帮助,他们协助洪光佑的两艘鲔钓船取得在安哥拉沿海的捕鱼证;后来又一次在公海作业时,由对方协助做海上加油。有了初步接触的良好印象,后来的合作,就变得顺理成章。
1995年,吴宣政、宋文恒挂名代表,用“增加运搬船营运项目”为名,出面邀请洪光佑参加合资企业──华隆海运公司,10月31日,与华连签订代理营运合同,由华连公司代管船舶、船员派送、补给、揽货、运输等所有船务。
洪光佑投资了68万美元,占80%股份,华连占股20%,以8:2的比例,向希腊购买了一艘可以承装1,500吨渔获量的二手运搬船,在北非与中非之间的海上从事当地拖网船渔获的装卸转运工作。
一次航趟大约一个月时间,一年可以跑上10到12趟。洪光佑的远洋投资,重心慢慢由鲔鱼捕钓转向华隆轮运搬船业务。
1996年,吴宣政利用华连公司做为大连市政府“试点改制国营企业”的机会,邀请洪光佑续作投资,洪光佑于是再汇出60万美元,做为由国营改制为民营、扩大规模的周转金。
洪光佑之所以愿意一再投入大笔资金,有观念上的误判,他认为大连水产集团属于中共国有企业,就直觉地以个人的观点来做思考,以为大陆国有企业就像台湾国营企业一样,是国家管制的正规公司,应该是可靠的,不会有倒闭风险存在。
莫名承受债务 被迫接管华隆轮
1997年,洪光佑正式结束所有鲔捞船本业,全心投入运搬船经营。
投资伙伴关系,从1995年10月签约合资开始,合作陆方代表吴宣政,一再告知渔船本身营运状况与营收效益很好,一年多来已有上百万人民币盈利,让洪光佑放心。
因为洪光佑是以投资者身份参与合资企业,占股8成,等于是船东,委由华连公司代理所有船务管理,本身没有实际参与工作,所以也没深究细节。
没想到,1997年12月4日,吴宣政传真了一份资料向洪光佑表明,大连集团结算海外亏损达300万美元,分割给子公司来清偿债务,华连必须承担其中145万美元欠债。
吴宣政以此做为“一年多来上百万营收始终无法清算、回馈给洪光佑”的理由,等于摆明大连水产集团的债务转嫁给了海外毫不相关的台商合资大股东洪光佑来承受。而这个说法,也只是吴宣政个人的片面之辞,债务问题的真实情况如何,难以查证。
洪光佑在1997年底派出台湾会计前往查账,却遭到对方排挤、刁难,有蓄意隐瞒之嫌,会计勉强根据对方交出的账单发票与营运状况估算,至少有89万美元盈余不翼而飞,可以合理的怀疑,这笔款项可能已遭吴宣政挪用,只是苦无对证,洪光佑为此向大连市政府与大连海事法院陈情,请求协助,得到的回应都是不予受理!
为了使先后两笔总数高达128万美元的投资不致落到血本无归的下场,洪光佑只好一再让步,这也给对方步步设局提供机会,致令洪光佑越陷越深,损失越加惨重。
1998年2月洪光佑前往西班牙与吴宣政会面,已成过河卒子,别无退路的洪光佑,签下了股东协议书,等于被迫接管了华隆轮,对方脱手的时候,还不断安慰洪光佑说船的效益好,只要多跑几趟、多载几次货,就可以很快弥补亏空。
但洪光佑实际接管后,发现漏洞百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而吴宣政在此事之后,就失去了音讯,不知去向。
开始收拾一堆烂摊子
洪光佑把包括副总经理宋文恒、船长、船员等原来大连集团之下的老班底,全部留下继续随船工作,因为洪光佑是外资企业,他认为借用富有经验、操作熟练的现成人力,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不用再费心重新安排人事。
老实的台商洪光佑,似乎总是后知后觉,华隆轮是一个严重的烂摊子,自接管以后,他才看清楚其中内情,根本还不及考虑如何挽救被侵吞的资产,就必须先去修补一个又一个漏洞。
原来吴宣政掌管船务期间,捅了几个大漏子:托辞要背负母公司大连水产集团分割出来的145万美元债务,使合资企业赚进的100多万美元,被其挪用,不见了踪影。
洪光佑一接手经营,又冒出一堆烂账,包括船员工资、加油款、伙食补给费用,总共多达20几万美元的积欠款,而且当时船况不好,华隆轮买进来时,已有20几年船龄,使用已超过2年时间,面临每2年必须要开进船坞进行维修工程的一、二十万元开销,这些全部要洪光佑一一买单。
更糟糕的是,这艘船在他们管理期间内,有一次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拉斯港内泊岸时,偷偷排放污水,被巡防员抓到,船只被查扣,被限制出港。吴宣政等人就设法让这艘船半夜开溜,华隆轮因此变成黑名单上被列管的船只,不能再回到西班牙属地靠岸,只能行驶在非洲。
洪光佑接管时,赫然发现他投资的船,好像成了一艘在海上飘泊的幽灵船,必须到非洲迦纳国去卸货,不能靠在欧洲港口,这给洪光佑带来极大困扰。
洪光佑为了后续的正常经营,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将“华隆轮”改名为“杜卡多轮”,重新注册,原来的船籍没有办法丢掉,营运的时候就用“杜卡多”,等于同一艘船有了双重船籍。
宋文恒跟吴宣政在西班牙华连公司都是大连水产方面的代表,宋文恒是子公司副总经理,吴宣政挪用资金逃离后,宋文恒成为洪光佑联系对话的直接窗口。
再成立独资公司 掉入更深的陷阱
洪光佑接管华隆海运,船员丧失了国有企业保障而在海上闹罢工,宋文恒后来回到大连,为船员寻出路。
1998年,宋文恒劝洪光佑在大连保税区另外成立了“京隆水产公司”,洪光佑担任总经理兼法人代表,目的是让海外杜卡多轮上的船员,在工作关系上有“落户”的安全感。
宋文恒又居中促成洪光佑以京隆水产公司做为买方,花了330万元人民币买下辽宁一艘二手运搬船,命名为“京隆轮”,京隆轮与船舶所有人事,都挂在洪光佑申请立案的“美商京隆公司”名下,独资经营。洪光佑一心只想解决问题,没料到反而扯出更多的纰漏来。
杜卡多轮恢复自由之身后,原班人马在大西洋海上的运搬工作,运势仍然不佳;1999年12月,在外海作业时,撞沉一艘西班牙渔船,西班牙船东要求理赔,保险公司也要求查扣,刑事责任未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2月在尼日利亚又因当地买主拒收品质与规格不符的渔货,要求当地政府扣押船只。其实货主是租船的欧洲商人,收货方应找货主理论,但他们找错对象,错把船东洪光佑当成货主,扣押了船东的船。
杜卡多轮因此滞留当地,无法正常营运,被迫停产。洪光佑与大连市府协商,透过中方外交部安排船员回国,为了避免后续纷扰,洪光佑壮士断腕,决定放弃杜卡多轮经营权,弃船返台。
5年来投入在合资企业上的心血,洪光佑没有获得丝毫利润,只是接管了中国一个国营企业的烂摊子,持续帮忙偿还各项欠款而已。船员工资每两年结算一次,船员有来有去,前债清完,后债又来,到洪光佑离开时,仍然背负着20万美元的工资欠款。
2000年4月,杜卡多轮船员返回大连,当时洪光佑被告知,20几人的机票钱,是大连市政府央请中共外交部出资代购,协助船员先行回国,这笔费用日后还是由洪光佑如数承担。
洪光佑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上,好像对方眼中的“金鸡母”一般,任凭一次又一次无理地索求。
“受害人”变成“被告”
回到大连以后,船员不知在何人的授意下,采取法律途径,2000年6月19日,第一次向大连海事法院提告,船员单连鹏等11人,以船东“拖欠工资”的理由,向大连市政府诉请扣押“京隆轮”,要求“大连京隆水产公司”做债务担保,提出80万元人民币担保金,洪光佑急于解扣,几乎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了担保书,船员为后续的起诉案取得有利条件。
6月23日,另一批船员17人,持上述原告提供的担保书,再度在解扣谈判上,要求洪光佑“京隆水产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两次的提告,犯了同样的错误,洪光佑是被告,是债务人,却被要求同时做担保人,债务人做担保人,依法是说不通的,法院根本不该受理,但大连海事法院却受理了此案,是明显的犯错。
其次,依照〈海事法〉中的“诉前扣船”规定,只能根据欠资当事船舶──被扣在尼日利亚的杜卡多轮来作审理,船员不能告大连保税区京隆公司,是“错告”在前,而大连海事法院站在执法立场,应该明白此案不该受理,它却罔顾法律明文规定,“枉法”受理。
这其中还有费人猜疑的许多关键细节,洪光佑一直不明白,他以杜卡多轮船东身份与船员签订的“工资合同”,为什么被偷盖了“京隆水产公司”的公章,显然是蓄意要将合资企业欠下的烂账转移到不相干的独资企业上。
是谁在工资合同上动了手脚?谁提供船员起诉证和“京隆水产公司”的买船合同?尽管幕后指点高人呼之欲出,洪光佑心里也有数,但老实又谨慎的洪光佑,不愿做出节外生枝的揣想,他只希望大连海事法院能依据〈海事法〉:“法院只能扣押当事船舶或同公司姐妹船。”的规定来做判决。
很遗憾的是,大连海事法院刻意避开〈海事法〉,而引用〈民法〉第92条:“债务人应当偿还债款。”,做了“枉法判决”,模糊掉洪光佑兼具“华隆海运”船东(“杜卡多轮”所属公司)、“大连保税区京隆水产公司”负责人与“美商京隆公司”董事长(“京隆轮”的注册公司)三个独立法人、但权责分明的立场。
法官无专业 枉法判决
洪光佑越想越不对劲,6月23日,前往大连海事法院提请“担保无效”要求,但法院仍认定保证人有拖欠工资情事,不但驳回要求,还限制洪光佑出境。
7月21日大连海事法院开庭审理上述两笔起诉,法院根据“担保合同”与“买船合同”,批准扣押京隆轮,裁定15万美元解扣担保金。洪光佑不服,并未依判决去支付这笔款项。
9月期间,法院张贴京隆轮的拍卖公告,并刊登广告,给洪光佑施加压力。大连海事法院副院长徐孝先受理本案时,并未依规定组“合议庭”,针对洪光佑代表美国京隆公司提出的扣船“异议”,去了解被扣的“京隆轮”并非被告“大连京隆水产公司”所有,何况美国京隆公司或大连京隆水产公司都是独立法人,与因欠资闹出问题的当事船舶杜卡多轮,是不应该有任何牵扯的。
但徐孝先避重就轻,以“美国京隆公司”的美国地址不明确等细节,驳回异议,将此案交由法官李杏媛以“独任审判员”来做处理,李杏媛即根据担保书,草率地判决大连京隆公司败诉,仍然维持“扣押京隆轮”的15万美元解扣裁定。审理程序与判决结果,徐孝先和李杏媛有法不依,再度做了“枉法”裁判。
洪光佑当然不服,拟妥诉状并支付了5千元律师费给聘用律师张积才,准备提起上诉,大连海事法院却先一步请张积才转告洪光佑,要他停止上诉,只就船舶所有权进行诉讼即可。
等于明告洪光佑“大连海事法院不受理其上诉案”,张积才因此打退堂鼓,没有站在受害者立场着想,积极为其争取上诉机会,违反了律师的职业道德,也就等于阻断了洪光佑的上诉之路。
洪光佑对于大连海事法院的审案态度感到极度不可思议:“大连海事法院居然不晓得财产(指京隆轮)归属是以登记名下为依据,不是以买卖合同来认定!”
为此,他特别去了解主事法官──大连海事法院副院长徐孝先的个人背景,发现对方出身船员,担任过船长职务,1995年转任大连海事法院工作,当上副院长之后,96年才从吉林法学院一个什么研习班毕业。
走上申诉、上访的艰辛之路
洪光佑进一步了解那个研习班是政协开办的,洪光佑找到主办人询问状况,对方强调那是为一般法官进修而设,培训出来的专业能力,不足以担任法院副院长。
即使徐孝先有船务工作经验,对海事熟悉,但对法律未必熟稔,所以徐很可能是靠着某些关系,先坐上了法院副院长的位置,才临时去恶补一些短期课程,取得一个形式上的资历,就“名正言顺”执起法来。
洪光佑感慨地说:如此速成的法官,审案怎么不会闹笑话?“枉法裁判”的案例,在中国大陆多如牛毛,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0年9月底,京隆轮获解除扣押,是因为洪光佑为免除京隆轮遭到拍卖,向承租京隆轮的福建平潭永利渔业公司寻求协助,永利公司也急需船只运补,因而为洪光佑先代垫了所有解扣金200万元人民币,双方谈妥以此来抵偿租金。
到2003年,永利公司核算前前后后代偿金额,包括船只维修费用,已高达353万元人民币,超过船舶本身市价,因而向洪光提出船只归属权问题,已为申诉疲于奔命多年的洪光佑,早已无心经营生意,最后答应将京隆轮抵让给了永利渔业公司,洪光佑的一份资产,再度化为乌有。
洪光佑一直认为,他的案子得不到合理解决,症结全在于大陆司法人员素质太差,专业水准太低,不然不会做出如此离谱的“枉法裁判”。后来的几年,洪光佑一直在这方面用心,希望透过什么方式,寻求一线生机。
从2003到2007年他继续倾注体力、精神、时间与金钱,争取任何可以重审的机会。2003年他飞到大连,长住了一年多时间,在省市几个单位,来往奔波。
2003年8月,他向辽宁省检察院提出控诉状,指出大连海事法院违法扣押京隆轮事实,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2003年底到2004年初,找过辽宁省台办,当时负责接待的工作员刘树森还请专业法律人士进行评估,私下都明确认定是“枉法裁判”无疑,但刘树森并没有向上申报给检察院做处理,仅建议洪光佑再聘请律师上诉,把案子结了。
后来,洪光佑又利用省政协与人民代表两会召开期间,到两会窗口递状,由他们安排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当时有获接待,但未获受理。
上报国务院国台办 被打回票
洪光佑再透过省政协组织下的台湾同胞联谊会帮忙,由他们做出了一个民主监督的专文提案,以省政协名义发文给大连海事法院要求再深入调查。
不久,洪光佑收到大连海事法院回报省政协的函件副本,针对洪光佑指控枉法扣船裁判,提出了长达11页29条附件做为反驳证据,全盘推翻洪光佑的所有指控,这完全是一份扯皮文件,29件“证据”,十分牵强,而且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当事人出庭“质证”的程序,等于是片面做出来的论述。
2007年,洪光佑针对这份报告内容,见招拆招,再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附上厚厚一叠参考文件,往上申报到中央国务院国台办,苦苦等候回音,最后得到的是,国台办三个字的回应:“看不懂!”所有的苦心积虑,被国台办用一句轻松的话便打了回票!
至此,洪光佑终于明白了一些道理,所谓“枉法裁判”,绝不是当初认知的仅仅是大连海事法院或中国司法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太差而已,他很明确地看到了、领受到了,这是中共以“党”治国,整个全社会腐败官僚系统共同作业的结果。
明明很明确易懂的错告误审案件,却让小老百姓在申诉过程中,煞费周章、饱受折腾,只要抵触中共党的利益,面对的就是官官相护,层层包庇;中共的法律,只是案头的装饰,管你台商、外商或国内底层的小老百姓,不论你多么有理,正义永远无法在中共体制下得到伸张。
洪光佑两手空空、一身疲惫,回到台湾!从1995年至2007年,十几个年头,好像一场噩梦,过去了。梦醒时分,洪光佑愿意重新开始。他还是抱着不灭的希望。
工作之余,他从高为邦2003年成立“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所付出的用心,看到自己可以着力的方向,也很愿意尽一份力量,不是为讨回个人的公道而已,而是为制止中共形形色色的贪赃枉法,为捍卫台湾人民的权益,为免于更多的台商重蹈覆辙,他愿意挺身而出。
2011年2月,辽宁省省长陈政高率团访台,洪光佑曾打电话到陆委会要求安排和陈政高等人见面陈情,遭到拒绝;他又设法联络随行而来,曾经经办过他的案子的大连台办经贸主任刘金海,要求安排见陈政高一面,也被告知正在景点旅游,不再回应。
勿对中共存幻想 政府要强硬起来
洪光佑眼看着陈政高一行人,大剌剌地在台湾南北穿行,想到大连是台商受害重灾区,多少台商的血泪遭遇,至今没有得到解决,陈政高却敢于打出“台商北上,前途无量”的响亮口号,继续来台招商引资,企图诱骗更多的台商与台资,砸入火坑,心里真是悲愤交加。
他与台联办公室取得联系,透过文宣主任周美里举办了一场记者说明会,台联主席黄昆辉出面说明,他在了解洪光佑的受害经历后,忍不住痛批马政府,不肯解决台商受害问题,还放任大陆省长来台招商,无异是“放虎逛街!”
黄昆辉要求政府以后若要让中共高官、省长来台,一定要先接见台商解决问题,否则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政府不能成为中共坑害台商的帮凶。
《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乏实质意义
今年8月9日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签署了《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内容符合中共最惠国待遇、金融业保护等需求,为中资来台大开方便之门;反而是国人期待的“人身安全自由保障”这一部分,中方刻意规避“国际仲裁”,只有含糊空洞的“协处”与“调解”字眼勉强可以援引。
学者专家批评,这是一个缺乏实质意义的不平等条约,台商投资等于还是没有保障。洪光佑说,陆委会某官员曾告诉受害台商代表高为邦,表示“等《两岸投资保障协定》签署后,就会有一个机制、一个平台,做为依据,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签署之后,陆委会在媒体上大做广告,展示投保协议签署后的台湾前景,但“门打开、阮顾厝”的关键台辞,却引发更多的负面联想,似乎暗示着:“陆资要进来了,大家得把自己的家顾好。”
同时官员代表的另一说辞:“《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不是万灵丹!”在在说明,连政府都不敢对投保协议的效能打包票。
洪光佑认为,政府立场应该要强硬起来,而且一定要出面尽快成立专责机构,为过去受害台商召开公听会,订定为台商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方案。过去陆委会的报告说“已受理多少多少台商受害案件了”,他们所说的“受理”,只是把案件做转送而已,在角色扮演上,充其量也只做了一个传声筒的工具而已!并没有真正帮助台商解决难题。
洪光佑知道寄望政府拿出魄力,有一定难度,他希望媒体与民意代表也能为他们伸张正义,同时希望更多受害台商站出来,大量曝光中共坑害台商的种种恶行,越多的声音出来,一定会起到吓阻作用,让对岸知道:台商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肥羊!台湾人民必须自求多福,同心协力,才会活得更安全、更有尊严!(全文完)◇
【台商泪总汇点评】
台商投资“资产”还是“钱坑”?
⊙童文薰
畜牧业需要大量的农作物充作粮食,对地球的污染与负担近来成为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再加上红肉并非优质食物,而禽类虽为白肉,却多有残留成长激素的风险,因此水产品逐渐成为人们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洪光佑从父亲手中接下远洋渔船的事业,不仅极具前瞻性的市场眼光,而且因为进入市场的时间早,基础也打得好。几年的时间就增加渔船,事业欣欣向荣。
但洪光佑随船前往大西洋海域渔场作业,于1994年间认识了来自中国的大连水产集团西班牙代表,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诱往中国投资。从此陷入如同电影《钱坑》般的情节,不仅投入的资金被坑光,最后还要不断拿出钱来填补各种漏洞与损失以及面对员工追讨工资的窘境。这是洪光佑投资之初所始料未及的。
洪光佑与很多台商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误以为大连水产集团属于中共国有企业,于是直觉地以在台湾与世界各地经商的经验来思考,认定在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就像台湾国营企业一样,是属于国家管理的正规公司,不仅信用可靠,更不会有倒闭风险。
洪光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信任中方股东,既没有参与投资公司的实际运作,对于财务报表的真伪以及资金的流向,也疏于防范没有过问细节。以致于在1996年,账面上有上百万美元盈利的公司,却于次年以整个集团亏损300万美元为由,必须由洪光佑占八成股权,大连集团只占二成股权的“华连”公司承担145万美元的欠债,洪光佑还想靠查账以及法律途径解决这个荒谬的“天外飞来的债务”。结果当然也和在中国发生投资侵害问题的其他台商一样,最后不了了之。
人心都相同,洪光佑在1995年投入128万美元,为了保本,洪光佑才会被中方掐住了弱点,一步步进入对方所设的骗局,不仅拿不回投资,还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因为洪光佑投资的公司不是一项资产,也不是一项生财工具,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钱坑。
洪光佑向中方股东讨权利,最后拿到中方抵债的东西,是一艘看起来还有生财价值的“华隆轮”。可是这项表面资产,其实是一项负债,因为这艘船不仅船况不佳,需要动辄20几万美元的维护费,同时还积欠了一堆烂账,包括船员工资、加油款、伙食补给等费用。光是这个部分就多达20几万美元。
因为债务跟着船舶与业主走,因此承接“华隆轮”的洪光佑必须全部买单。包括船员因为所属船舶变为私企,因此失去国有企业的保障(即使是纸上保障,未必能够兑现)。但船员不去找原来的国有企业拿工作年资权利,却以罢工的方式要求洪光佑全部承受。
洪光佑因为一心想解决问题,同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钱坑,一步错步步错,结果成为各方人马的“提款卡”。他遭遇到的手段是所有被掠夺资产的台商都不陌生的:包括“被告不适格”的法院判决,不是雇主的公司却要负担别家公司的积欠工资;没有签署过的“工资合同”上凭空出现公司的印文;被法院限制出境以及扣押船舶,藉以胁迫洪光佑给付金钱;还有一连串的枉法裁判,甚至被中国律师半途抛弃,以致上诉无门。
至此,洪光佑才了解到,中国的法官大多不具备法律背景,做出离谱的枉法裁判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主审他的案件的法官竟然是船员出身,不曾有过完整的法律训练或相应的学位!
有了这项了解为基础,洪光佑犯了第三个错误,让他从2000年起一直到2007年,整整8年的时间里,都以为既然问题出于中国的司法人员素质太差、不具备法律专业能力,那么一定能有其他的方法,比如上访或通过特殊渠道,可以拿回他投入的资金,并免除那些天外飞来的债务。
但是,花了8年的青春岁月,最后的结果都是徒劳。不管是挂在地方政府底下的“台湾同胞联谊会”或者是中共的“国台办”,通通是腐败且官僚,没有一条路走得通。然后洪光佑才觉悟到,不只是中国的司法人员素质差,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么一个掠夺老百姓与台商资产的贪腐结构。
这个觉悟,花了洪光佑13年的时间。13年的青春岁月与可观的资金损失,换来对中共的彻底觉悟。
其实要了解中共用不着13年,《大纪元》出版的《九评共产党》可以让每一个人在两个小时以内完全弄清楚中共究竟是什么。相信洪光佑如果早点认清楚中共的本质,就不会损失钜额资金与大把的青春岁月。
“千金难买早知道”,《九评共产党》就是那个送到众人眼前的“千金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