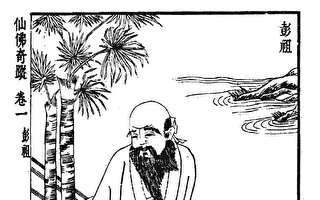武則天曾經召集膝下諸位皇孫朝見,讓他們坐於殿上,觀察群孫嬉戲情況,並且命人取來西域各國所進貢的玉製環、釧、杯、盤等珍物,排列於前後,下令孫輩們極力爭取,利用這種機會來觀看他們自小所立的志向。所有的孫子們,沒有不拚命奔走競逐的,幾乎人人都獲得豐厚賞賜,獨獨玄宗(備註1)一人巍然端坐,不為所動。
武后心中大奇,撫著他的後背說:「此兒應當是太平天子哪。」於是派人取來「玉龍子」賜給他。
玉龍子,是唐太宗在晉陽宮中無意得到的,文德皇后(即唐太宗之妻長孫皇后)常常將其放置在衣箱之中,等到大帝(即長孫)滿月後三日,悄悄取出玉龍子,並特別用紅色絲織品包裹賜給他。此後,經常收藏在內府,一般人難得見。雖然它直徑不過數寸而已,可是製工精巧、玉色溫潤,一看即知非人間所有,因此,成了唐代皇宮的珍寶。
等到玄宗即位,每遇京師乾旱缺雨,必定拿着玉龍子虔誠祈禱,倘若天將降甘霖、大雨即刻要傾注時,把它拿過來仔細看,那玉龍子身上的龍鱗,奮起張開,龍鬣晃動不已,就像要騰空飛起、風雲大作一樣。
開元中,三輔(長安一帶)地區大旱,玄宗再次拿出此寶祈禱,可經過十幾天依然無雨,於是皇帝取出玉龍子,秘密投入大內南邊的龍池中,頃刻之間,雲霧暴起,風雨隨即大作,解除了旱象。
等到他臨幸西蜀一地,車輦儀隊經由渭水,將渡河時,駐蹕(帝王出行的車駕叫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之人,有幾個趁著空檔,跑到河邊洗濯或戲水的,有人就在泥沙中摸得了此寶,將它獻出。皇上聽聞此事,異常驚喜,詳細審視之後,泫然流淚,說:「這是我昔時所寶貝的玉龍子呵,如今失而復得。」此後,每夜之中,玉龍子散發出的光彩,輝映燭照一室。
皇上回歸京城之後,此寶卻被小黃門(即小太監)偷竊去贈送李輔國(備註2),李輔國時常放置於櫃子中。後來李輔國不法行為即將敗露時,一夜,耳聽櫃中有聲響,打開探視,玉龍子已經亡其蹤影。
由此事件,不但可以證明「萬物皆有靈」,而且這些具靈性的寶物,都該是「有德者」才配擁有;一旦所事「非人」,它就會無緣無故失蹤,再去尋覓另一個「有德者」做新主人,是這個道理吧!@
(事據唐 鄭處誨《明皇雜錄》)
【備註1】
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次子,武則天之孫。西元712年,睿宗讓位給李隆基,次年改號開元,即是唐玄宗。玄宗是歷史上十分著名的皇帝,在位長達四十四載,前半期政通人和,呈現「開元之治」盛世,天下太平,物阜民豐,足堪與唐太宗時之「貞觀之治」相比擬。
【備註2】
李輔國,唐肅宗時當權宦官。本名靜忠,曾賜名護國,相貌奇醜無比。李輔國四十歲之前無所作為。安史之亂期間,勸說太子李亨繼承帝位。唐肅宗即位后,被加封為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始掌握兵權,並改名為輔國。之後又因擁立代宗即位,被冊封為司空兼中書令。大權在握后,李輔國更加為所欲為,最後被人刺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