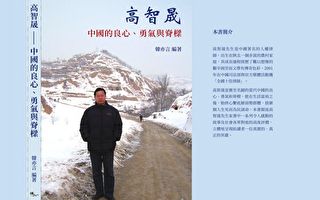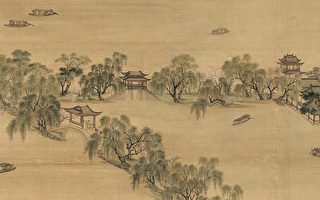(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2月17日訊】1828年秋天,人們發現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被拋棄在德國一個小鎮的廣場上,他身體虛弱,只會勉強走路,智力像個初生的嬰兒,不會說話,能用鉛筆拼寫出名字:卡斯帕﹒荷伯。有人說他是個棄兒,有人說是從英國清教徒的獄中逃跑出來的,但這只能是猜測。人們只知道他一出生就被關在地窯裡,與世隔絕,從來沒有見過陽光、花草樹木和動物。最初他被鎮上的當權者交給一個馬戲團供人參觀,後來一個老教師收留了他,並教會了他說話拼寫、彈鋼琴和許多世俗的知識。他先後兩次遭到不明身份的人襲擊,第二次襲擊奪去了他的生命,當時,離他“誕生”只有五年。卡斯帕﹒荷伯自被發現後,人們就稱他為“歐洲之謎” ,一個多世紀以來,有大量關於他的論文發表,現在,他在心理學裡已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特指與社會隔離所造成的不正常生理和心理現象。
這是個真實的事件。1974年,當時還年輕的德國導演維納﹒赫爾佐格(Werner Herzog)把這一事件搬上銀幕,拍攝了《卡斯帕﹒荷伯之謎》(Every Man for Himself and God Against All-The Mystery of Kaspar Hauser)。這部電影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在次年獲得了戛納電影節評委會大獎。
在當時幾個“新德國電影運動”的幹將中,赫爾佐格是最具哲學家氣質的,他的電影是明顯的“主題先行”的產物,極其風格化,他總是選擇一些人類生活經驗和文明的理解力之外的人物或事件,放在一種與人類經驗保持距離的極端境況下,反省人類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他說:“我在電影中表現我所看到的東西,而其他人從未看到過,也不曾認識它。”那麼,這位稟承了日耳曼人理性傳統的導演,從這個真實的故事中看到了什麼人所未見的東西呢?
首先,他借卡斯帕的眼睛看見了人們的冷漠和自私。在一百多年裡,卡斯帕僅僅作為進行科學研究的對象存在於人類文明的數據庫中,對於“正常”的人來說,他是無法理解的一個謎,一個供人參觀的怪胎,一個手腳五官齊全的動物,唯獨不是一個人,所以無須按人的標準來對待他。他被安置睡在馬廄裡,或關進監獄,衣著體面的紳士、軍官們像檢查牲口一樣檢查他身上的每一處傷疤、每一個關節、每一塊肌肉的柔軟程度,用劍和火來試驗他的生理和心理反應,做這些只為有一個符合科學要求的精確記錄,因為卡斯帕是如此難得一見的一個標本。卡斯帕被火灼傷手指,疼得流出淚來,引來的是圍觀者的轟堂大笑。這也許是他作為人第一次流淚,這第一次就讓他明白了:生而為人,痛苦不僅僅來自肉體的創傷,更來自心靈的屈辱。完成科學記錄後,卡斯帕再無用處,為了卸去負擔,人們又將他作為怪物交給馬戲團去展覽賺錢。一個活生生的人,不論他的身份多麼特殊,沒有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和尊嚴,人生而具有的憐憫之心從不會施加於他,這樣的人群還可以稱為“正常”嗎?
當英國貴族準備收養卡斯帕時,讓貴族老爺惱火的是,卡斯帕竟然不懂得感激他的仁慈,在大庭廣眾沒有一句與貴族的優雅相稱的得體話語,獨自去了一邊織毛衣,做這只有下人才做的活,貴族老爺只能說:“我不理解,我不理解。”他難道真是為收養一個乾兒子,而不是為了滿足自己“仁慈”的虛榮和為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提供一個獵奇的機會?卡斯帕純真出天然,當老教師向他解釋周圍的人們都很關心他時,他一語道破天機:“這些人跟狼一樣。”
也許,換一個一無所有的正常人,就像我們在偉大的古典文學傳統中看到的那樣,卡斯帕感到的冷漠和自私我們一樣可以看見。卡斯帕更重要的意義,是讓赫爾佐格看見了人類賴以驕傲的文明和進步背後的陰影。卡斯帕一來到社會上,具有的是一種天然的人性,然後,我們就看著他一點點被要求理解人類的秩序和文明,這種天真被一點點地污染、扼殺,直至當他不能理解這些而給既定的秩序造成威脅時,最終有一個人來殺死了他。這個兇手並不是某個個人,而是代表了這種病態的文明。卡斯帕死後,人們還要從他的身上尋找畸型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健康。
文明的目的是為人類的福祉和進步,是讓人自身活得更具人性的光輝,在電影裡,赫爾佐格顯然是頗費心思,精心安排了三次卡斯帕與所謂文明的交鋒,讓我們看清了文明已淪為虛偽的裝飾和扼殺人性的凶器。第一次,代表人類神聖價值和情感的教會來可憐的卡斯帕身上見證神的偉大,教士滿心希望他生來在黑暗的地窯中就心懷上帝,卡斯帕說:“在那裡我什麼都沒想過。我不能想像,上帝什麼也不用,就創造一切。”第二次,代表科學和智慧的哲學教授給卡斯帕出了一個邏輯難題,想用他的失敗來增加科學的光輝,卡斯帕用異常天真通俗的解答回敬了傲慢的教授。諷刺的是,女佣聽得懂卡斯帕的道理,對教授的解答則不知所云。第三次,是世俗社會希望他對於人們的“善良”和人世間滿目的美景懂得感恩,已經經歷了幾年“文明人”生活的卡斯帕卻徹底否定了這個冰冷的世界:“對我來說,來到這世上,是在一個可怕的秋天。”看到這裡,你就會明白,卡斯帕注定是個異數,不會被社會所容。
夜色深沉,四野寂靜,墨綠的草地和樹木像人類的同情心一樣曖昧地沉默,背他出來將要棄他於市的父親一襲黑衣,在畫面的中間背對鏡頭端坐著,如一座威嚴冰冷的塔,前景的卡斯帕俯臥於地,顯得那麼無辜和無助。也許,弱勢的、邊緣的個體需要幫助的時候,社會就是這樣一個冷漠威嚴的塔。
盡管如此,赫爾佐格卻並不是個偏激的異教徒,他對人類的友愛和傳統價值仍然投注著脈脈溫情。如果不是這樣,我想他就不會用極為冷靜和克制的長鏡頭來詳細渲染卡斯帕在地窯中骯髒而渾渾噩噩的生活。畢竟,人性的純真不等於蒙昧。而且,最初照顧卡斯帕的農民夫婦,他們可愛的孩子,以及具有偉大的同情心的老教師和他的女僕,他們對卡斯帕的感情在我們眼裡是那麼熟悉和親切,那是親人和親人,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孩子。赫爾佐格的矛頭針對的始終是異化的、散發著腐臭氣息的文明。
電影的攝影風格也值得一說。在《卡斯帕﹒荷伯之謎》裡,赫爾佐格用了自然主義的拍攝手法,絕大多數情況下採用固定機位的長鏡頭,極少運動和變焦以及快速的剪切,有意識地與人物和事件保持距離,把卡斯帕和他周圍的人、環境都冷靜地收入眼中,讓觀眾自己去看,去了解,這樣的手法,完全是因為他的目的是要呈現整個社會對於卡斯帕的態度並對這種態度進行反思。所謂文無定法,方法是為思想服務的,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成就了他的兩部傑作。比如片末那個近兩分鐘的長鏡頭:解剖完卡斯帕的屍體,書記員作完記錄,鏡頭從街道對面看著他心滿意足地從屋內出來,揮手叫了馬車,卻只讓車夫把他的禮帽帶回家,他則要步行回家,因為“這是值得記住的一天”,他得與平時有所不同才行。他們剛剛在卡斯帕的大腦和肝臟發現了不正常的形狀,“使我們最終能對這個怪人做出解釋,真是太棒了”。鏡頭緩緩地向右搖了九十度,不動聲色地看著這個有些滑稽的背影自言自語,沿著房屋夾道的石板路,跟在馬車後面走向城市的深處。科學和冷漠最終取得了對這個可憐的非人的勝利。
片中不時出現一些無人的空鏡,廣漠的田野,默立的樹木,搖曳的水草,幽暗夜色中的一隻白天鵝,陰影層疊的屋頂,霧靄沉沉的遠山,鏡頭靜靜地定在那裡,構圖優美,意境淒清,散發出一種奇異的魅力。有些我看懂了,比如卡斯帕死前那只悄然隱向樹蔭下的天鵝,大部分沒看懂,也許本來就沒有深意,但我相信其中自有情懷,它們讓你的眼睛和思緒不由自主地停下來,什麼也不想,覺得有一樣東西悄悄地進入你心裡。
影片開始的時候,有個近一分鐘的長鏡,陰霾的天空下望不到邊的枯黃蘆葦,在勁風鼓盪下此起彼伏,如驚濤駭浪,翻滾不息,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啊!然後給出了一句字幕:“你沒聽到周圍的恐怖聲音嗎?那大叫的男人要求安靜。”片尾,卡斯帕臨死前說他做了一個夢,一個騎士率領駝隊橫穿沙漠,看見前方出現了山巒,迷了路。瞎眼的老向導嘗了一把地上黃沙說:你們錯了,那不是山,而是你們的幻覺,我們還得往北走。他們聽從向導,在北方找到了城市。卡斯帕說:“這是故事的開始,他們到達那個城市以後的事,我不知道了。”那會是伊甸園還是被上帝之燄吞噬的索多瑪?
一頭一尾,有耳不聽,有眼不見。赫爾佐格真是用心良苦。我仿佛聽到了羅大佑的那首《盲聾》:
地下道的牆上問著今天誰是盲聾
算命的老者受到無知人們過度的恩寵
空中傳來先知的話它是否進入你耳中
潮汐與蟬聲傳來的訊息
──一片朦朧
【明心網】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