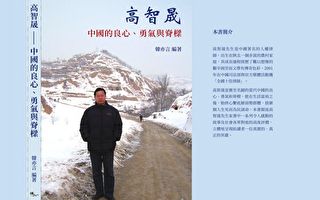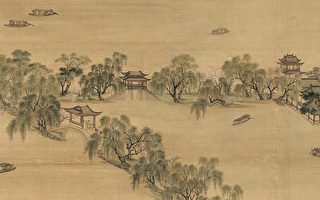(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2月17日讯】1828年秋天,人们发现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被抛弃在德国一个小镇的广场上,他身体虚弱,只会勉强走路,智力像个初生的婴儿,不会说话,能用铅笔拼写出名字:卡斯帕﹒荷伯。有人说他是个弃儿,有人说是从英国清教徒的狱中逃跑出来的,但这只能是猜测。人们只知道他一出生就被关在地窑里,与世隔绝,从来没有见过阳光、花草树木和动物。最初他被镇上的当权者交给一个马戏团供人参观,后来一个老教师收留了他,并教会了他说话拼写、弹钢琴和许多世俗的知识。他先后两次遭到不明身份的人袭击,第二次袭击夺去了他的生命,当时,离他“诞生”只有五年。卡斯帕﹒荷伯自被发现后,人们就称他为“欧洲之谜” ,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大量关于他的论文发表,现在,他在心理学里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与社会隔离所造成的不正常生理和心理现象。
这是个真实的事件。1974年,当时还年轻的德国导演维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把这一事件搬上银幕,拍摄了《卡斯帕﹒荷伯之谜》(Every Man for Himself and God Against All-The Mystery of Kaspar Hauser)。这部电影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在次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在当时几个“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干将中,赫尔佐格是最具哲学家气质的,他的电影是明显的“主题先行”的产物,极其风格化,他总是选择一些人类生活经验和文明的理解力之外的人物或事件,放在一种与人类经验保持距离的极端境况下,反省人类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他说:“我在电影中表现我所看到的东西,而其他人从未看到过,也不曾认识它。”那么,这位禀承了日耳曼人理性传统的导演,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看到了什么人所未见的东西呢?
首先,他借卡斯帕的眼睛看见了人们的冷漠和自私。在一百多年里,卡斯帕仅仅作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存在于人类文明的数据库中,对于“正常”的人来说,他是无法理解的一个谜,一个供人参观的怪胎,一个手脚五官齐全的动物,唯独不是一个人,所以无须按人的标准来对待他。他被安置睡在马厩里,或关进监狱,衣着体面的绅士、军官们像检查牲口一样检查他身上的每一处伤疤、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的柔软程度,用剑和火来试验他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做这些只为有一个符合科学要求的精确记录,因为卡斯帕是如此难得一见的一个标本。卡斯帕被火灼伤手指,疼得流出泪来,引来的是围观者的轰堂大笑。这也许是他作为人第一次流泪,这第一次就让他明白了:生而为人,痛苦不仅仅来自肉体的创伤,更来自心灵的屈辱。完成科学记录后,卡斯帕再无用处,为了卸去负担,人们又将他作为怪物交给马戏团去展览赚钱。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论他的身份多么特殊,没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和尊严,人生而具有的怜悯之心从不会施加于他,这样的人群还可以称为“正常”吗?
当英国贵族准备收养卡斯帕时,让贵族老爷恼火的是,卡斯帕竟然不懂得感激他的仁慈,在大庭广众没有一句与贵族的优雅相称的得体话语,独自去了一边织毛衣,做这只有下人才做的活,贵族老爷只能说:“我不理解,我不理解。”他难道真是为收养一个干儿子,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仁慈”的虚荣和为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提供一个猎奇的机会?卡斯帕纯真出天然,当老教师向他解释周围的人们都很关心他时,他一语道破天机:“这些人跟狼一样。”
也许,换一个一无所有的正常人,就像我们在伟大的古典文学传统中看到的那样,卡斯帕感到的冷漠和自私我们一样可以看见。卡斯帕更重要的意义,是让赫尔佐格看见了人类赖以骄傲的文明和进步背后的阴影。卡斯帕一来到社会上,具有的是一种天然的人性,然后,我们就看着他一点点被要求理解人类的秩序和文明,这种天真被一点点地污染、扼杀,直至当他不能理解这些而给既定的秩序造成威胁时,最终有一个人来杀死了他。这个凶手并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代表了这种病态的文明。卡斯帕死后,人们还要从他的身上寻找畸型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健康。
文明的目的是为人类的福祉和进步,是让人自身活得更具人性的光辉,在电影里,赫尔佐格显然是颇费心思,精心安排了三次卡斯帕与所谓文明的交锋,让我们看清了文明已沦为虚伪的装饰和扼杀人性的凶器。第一次,代表人类神圣价值和情感的教会来可怜的卡斯帕身上见证神的伟大,教士满心希望他生来在黑暗的地窑中就心怀上帝,卡斯帕说:“在那里我什么都没想过。我不能想像,上帝什么也不用,就创造一切。”第二次,代表科学和智慧的哲学教授给卡斯帕出了一个逻辑难题,想用他的失败来增加科学的光辉,卡斯帕用异常天真通俗的解答回敬了傲慢的教授。讽刺的是,女佣听得懂卡斯帕的道理,对教授的解答则不知所云。第三次,是世俗社会希望他对于人们的“善良”和人世间满目的美景懂得感恩,已经经历了几年“文明人”生活的卡斯帕却彻底否定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对我来说,来到这世上,是在一个可怕的秋天。”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卡斯帕注定是个异数,不会被社会所容。
夜色深沉,四野寂静,墨绿的草地和树木像人类的同情心一样暧昧地沉默,背他出来将要弃他于市的父亲一袭黑衣,在画面的中间背对镜头端坐着,如一座威严冰冷的塔,前景的卡斯帕俯卧于地,显得那么无辜和无助。也许,弱势的、边缘的个体需要帮助的时候,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冷漠威严的塔。
尽管如此,赫尔佐格却并不是个偏激的异教徒,他对人类的友爱和传统价值仍然投注着脉脉温情。如果不是这样,我想他就不会用极为冷静和克制的长镜头来详细渲染卡斯帕在地窑中肮脏而浑浑噩噩的生活。毕竟,人性的纯真不等于蒙昧。而且,最初照顾卡斯帕的农民夫妇,他们可爱的孩子,以及具有伟大的同情心的老教师和他的女仆,他们对卡斯帕的感情在我们眼里是那么熟悉和亲切,那是亲人和亲人,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孩子。赫尔佐格的矛头针对的始终是异化的、散发着腐臭气息的文明。
电影的摄影风格也值得一说。在《卡斯帕﹒荷伯之谜》里,赫尔佐格用了自然主义的拍摄手法,绝大多数情况下采用固定机位的长镜头,极少运动和变焦以及快速的剪切,有意识地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把卡斯帕和他周围的人、环境都冷静地收入眼中,让观众自己去看,去了解,这样的手法,完全是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呈现整个社会对于卡斯帕的态度并对这种态度进行反思。所谓文无定法,方法是为思想服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成就了他的两部杰作。比如片末那个近两分钟的长镜头:解剖完卡斯帕的尸体,书记员作完记录,镜头从街道对面看着他心满意足地从屋内出来,挥手叫了马车,却只让车夫把他的礼帽带回家,他则要步行回家,因为“这是值得记住的一天”,他得与平时有所不同才行。他们刚刚在卡斯帕的大脑和肝脏发现了不正常的形状,“使我们最终能对这个怪人做出解释,真是太棒了”。镜头缓缓地向右摇了九十度,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个有些滑稽的背影自言自语,沿着房屋夹道的石板路,跟在马车后面走向城市的深处。科学和冷漠最终取得了对这个可怜的非人的胜利。
片中不时出现一些无人的空镜,广漠的田野,默立的树木,摇曳的水草,幽暗夜色中的一只白天鹅,阴影层叠的屋顶,雾霭沉沉的远山,镜头静静地定在那里,构图优美,意境凄清,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魅力。有些我看懂了,比如卡斯帕死前那只悄然隐向树荫下的天鹅,大部分没看懂,也许本来就没有深意,但我相信其中自有情怀,它们让你的眼睛和思绪不由自主地停下来,什么也不想,觉得有一样东西悄悄地进入你心里。
影片开始的时候,有个近一分钟的长镜,阴霾的天空下望不到边的枯黄芦苇,在劲风鼓荡下此起彼伏,如惊涛骇浪,翻滚不息,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然后给出了一句字幕:“你没听到周围的恐怖声音吗?那大叫的男人要求安静。”片尾,卡斯帕临死前说他做了一个梦,一个骑士率领驼队横穿沙漠,看见前方出现了山峦,迷了路。瞎眼的老向导尝了一把地上黄沙说:你们错了,那不是山,而是你们的幻觉,我们还得往北走。他们听从向导,在北方找到了城市。卡斯帕说:“这是故事的开始,他们到达那个城市以后的事,我不知道了。”那会是伊甸园还是被上帝之焰吞噬的索多玛?
一头一尾,有耳不听,有眼不见。赫尔佐格真是用心良苦。我仿佛听到了罗大佑的那首《盲聋》:
地下道的墙上问着今天谁是盲聋
算命的老者受到无知人们过度的恩宠
空中传来先知的话它是否进入你耳中
潮汐与蝉声传来的讯息
──一片朦胧
【明心网】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