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的時間裏,黃偉被非法關押的時間達五年餘。這,也是迄今看不到任何改變跡象的、實實在在存在著的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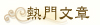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從七月十二日始,就盡早結束陝西省、榆林市及靖邊縣三級地方政府的非法、野蠻關押國內外著名維權律師朱久虎及其他十一名涉油經營者的局面,我及許志勇博士、滕彪博士、李和平律師一同抵陝北靖邊縣。
 2009年5月2日 11:36 PM
2009年5月2日 11:36 PM 上個月,我參加了幾十家媒體在北 友誼賓館召開的一個有涉圓明園防滲工程問題的研討會,會後一記者問我此時想對政府說點什麼,「當今的政府不做事,是對中國公民的最大善舉」,我如是回答。
 2009年4月26日 7:07 AM
2009年4月26日 7:07 AM 我的面前擺放著三個已死去孩子的材料,其中的兩個孩子的照片已在我的寫字桌上擺放久時。僅照片即能證明十一歲的小男孩高棣的活潑、聰明及帥氣。
 2009年4月22日 8:51 AM
2009年4月22日 8:51 AM 現在中央政府已明確規定,大學城不是教育事業,也就不是公共利益,法院根據廣東省政府二○○二年一九七號文決定建大學城的文件來作為拆藝術村的法律文件依據。
 2009年4月17日 12:25 PM
2009年4月17日 12:25 PM 藝術村除了不定期的進行藝術交流外,還舉辦「藝術節」。近年已舉辦過兩屆「小谷圍藝術節」(在行將舉行第三屆「小谷圍藝術節」之際,官商合體者的黑手伸向那裏),邀請國內及海外藝術家聚會,舉行畫展、觀摩、交流。它的影響是深遠的。
 2009年4月13日 8:16 AM
2009年4月13日 8:16 AM 被中外藝術界譽為與法國藝術家聚居地「蒙馬特高地」媲美的廣州小谷圍藝術村已被廣州市及廣東省兩級人民政府的惡行摧毀,但還未徹底摧毀。
 2009年4月10日 2:51 PM
2009年4月10日 2:51 PM 每個稍微有一點現代文明社會常識者都曉得,如果沒有刑事訴訟法律,那麼,刑法對社會關係的保護及調整價值完全與聾子的耳朵之功效無異。沒有憲政機制保障的《憲法》,與沒有刑事訴訟法保障的實體刑法價值毫無二致。
 2009年4月5日 10:54 AM
2009年4月5日 10:54 AM 二○○四年九月,上海徐彙區朱鋼等九位教師在聯合署名的信中寫道:「上海永龍房地產有限公司,委託上海徐彙房地產遷有限公司 遷。
 2009年4月3日 10:49 AM
2009年4月3日 10:49 AM 黃老漢被摧毀前的家,距人民大會堂約三公里。就在黃老漢的房產被蕩維廢墟前的前幾周,在人民大會堂裏,近三千名人民代表激情難抑至雀躍,私有財產被納入《憲法》的保護之列。
 2009年3月27日 3:01 PM
2009年3月27日 3:01 PM 一九九九年還有這麼一件事情,有一天一個朋友打來電話,說「過街天橋有一個很奇特的景觀,你必須去看。」我到那一看,繁華的過街天橋掛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尋找高智晟律師」,橫幅下面是一對夫婦和三個孩子,其中一個是九歲的腦癱病孩。
 2009年3月25日 9:10 AM
2009年3月25日 9:10 AM 偉毅案是我律師生涯中一起刻骨銘心的案子,當時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我們在給孩子打官司的過程中的付出,今天講起來我自己都感動,但社會給我的更多。
 2009年3月22日 8:59 AM
2009年3月22日 8:59 AM 我的一些案件但凡有一點意思的,或者說從新聞的角度看有些新聞亮點的,都是為弱勢群體打的一些免費官司,給受害兒童提供了一些無償的法律幫助,其餘都是經濟官司。
 2009年3月17日 7:30 AM
2009年3月17日 7:30 AM 我曾有一篇文章題目為「政府不做事是對人民的最大善舉」,事實上,它們不去做事也是對它們自身的一種善舉,它們不做事則已,做即全做愚蠢事,這也符合規律,即一群無理 、無道德、完全無自重意識者,亦僅能若此!
 2009年3月14日 5:11 PM
2009年3月14日 5:11 PM 又如,立法者完全認識到毀滅、偽造證據、唆使、引誘證人作偽證具有社會危害 ,應當受刑法罰責,但卻只特別將律師列為犯罪的構成主體,律師據此被科罪者眾,難道立法者能有律師以外的其他人實施上述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 的認識結果?顯然不會荒唐至此,不難看出立法者對律師深深的歧視和戒備心理。
 2009年3月8日 10:17 PM
2009年3月8日 10:17 PM 袁紅冰教授的文章引發我的感慨無盡,連我的夫人前天都不解地問,為什麼你在國內有如此大的名聲,卻從來沒有一家像樣的企業來找你做律師。
 2009年3月1日 10:15 PM
2009年3月1日 10:15 PM 非常感謝袁先生對我的理解,形單影孤的獨處、獨行大致上算得上是一種孤獨,但袁先生文中點到的我的孤獨的內核是,我以我認準的方式去思想、去選擇,這種思想及選擇有時讓人痛苦以至絕望,豈止是孤獨了得。
 2009年2月24日 8:52 AM
2009年2月24日 8:52 AM 命運沒讓高智晟選擇,從他律師執業第一天開始,就匆匆把他拋進了扶羸弱,護一方的角色。很難說這個角色對高智晟最終意味著什麼,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個維權律師要比其他的律師承擔更為深重的道義,付出加倍的艱辛。
 2009年2月10日 4:26 PM
2009年2月10日 4:26 PM 九八年在烏魯木齊,有一次高智晟回家交給耿和一筆錢,耿和一看都是零錢,問是怎麼回事,高智晟告訴她:「當事人給我的代理費都是十塊二十塊湊起來的,那是他們的血汗錢。我的錢掙得越多,我的當事人的苦難也就越多!」
 2009年2月6日 1:59 PM
2009年2月6日 1:59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