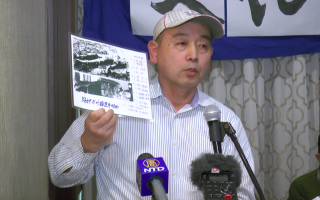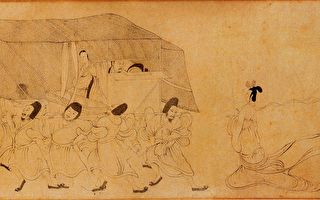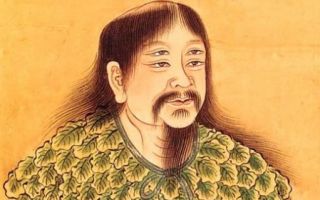(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4月4日訊】張藝謀執導的影片《英雄》上演,引發海內外一片責難。許多人發表文章,批評《英雄》歌頌暴政,取悅當局。為《英雄》辯護的人自然也有,耐人尋味的是,為《英雄》辯護者很少正面反駁批評者的論點論据。他們只是責怪批評者不該追究《英雄》的主題思想和政治傾向。
有人說,《英雄》是藝術片,不是政治片。我們看《英雄》,是為了獲得美的享受。不錯,《英雄》是很美。可是,《英雄》的美,除開自然風光与武打功夫外,更多的表現為法西斯之美。《英雄》是極權主義美學的杰作:宏偉壯觀的大場面,整齊划一的動作,高高在上的偉人和千千万万充當道具的群眾。在那里,偉人是抽象的,被當作歷史規律的體現或集體意志的化身或人民利益的代表;群眾也是抽象的,無個性無面目,其存在的主要功用是烘托偉人及偉人代表的偉大事業。《英雄》的不少鏡頭,在美學上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當年納粹德國的名片《意志的凱旋》。
為《英雄》辯護者拒絕和回避針對故事主題的批評。他們反問批評者:《英雄》是部娛樂片,你們怎麼老批評它的主題思想?這句話剛好問倒了。你不應該用這話去反問批評者,你應該用這話去問導演:既然拍的是娛樂片,為什么偏偏要選擇一部其主題思想會招致非議招致反感的劇本呢?
眾所周知,一般的娛樂片既然以取悅觀眾為原則,它總是力圖避免冒犯公眾的价值觀念,總是力圖讓各色人等皆大歡喜。這就是為什麼象《泰坦尼克》一類好萊塢娛樂大片能夠全球通吃的奧秘所在。我并不很欣賞《泰坦尼克》,我覺得在其中愛情故事喧賓奪主,比不上當年的《冰海沉船》。不過我必須承認,《泰坦尼克》中的這段愛情故事确實也容易讓人感動,起碼不會招人反感。畢竟,生死之戀總是人們共同珍視的一种价值。
《英雄》則不然。《英雄》不能不激起人們的反感。《英雄》宣揚的主題,既冒犯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又冒犯了現代的人權理念;不符合中國人的价值標准,也不符合洋人的价值標准。張藝謀如果事前沒想到《英雄》的主題會是對人們价值觀的挑舋,那是他無知;如果他明知故犯,那說明他要拍的并不是單純的娛樂片,而是“寓教于樂”片。
為《英雄》辯護者還說,《英雄》是商業片,圖的就是票房价值。這种辯護也有同樣的問題:商業片就商業片吧,拍什么不行,為什□偏偏選上《英雄》?好比一美貌少女,追求者如云,她卻偏偏嫁給一位黑幫老大。她說她圖的是錢,可問題是,在眾多的追求者中,有錢人多的是,其中有的是正派,清白,社會地位高或廣受尊崇的,為什么偏偏看上一個黑社會呢?
中國的武俠小說中,好作品多的是,絕大多數的主題都能投合大眾的价值標准,在細節上也不象《英雄》那般悖情逆理。如果選用別的武俠小說作劇本,憑著張藝謀的高超導技和眾明星的出色演出,再加上如詩如畫的景觀和鉅額資金的投入,完全可以創造出同樣的或更高的票房价值。可是,張藝謀偏偏選中了《英雄》,這不能不讓人怀疑,除了金錢之外,導演是否還另有所圖。
如果你告訴我,不選拍《英雄》而改拍別的本子,中共當局雖然也能容忍,但不會鼎力相助;而沒有當局的鼎力相助,《英雄》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商業成功。倘若果真如此,張藝謀拍《英雄》取悅當局之說就落實了。
也有人說,《英雄》招來如潮倒彩,安知不是一种成功的行銷策略?我看不象。《英雄》沒能評上金象獎,估計也評不上奧斯卡,這就無助于提高票房价值。退一步講,用招人罵的方式招攬生意,其代价是自毀人格自毀形象,君子不為。張藝謀拍過很多電影,不過,以后人們提起張藝謀,首先想到的會是這部《英雄》。
*評《英雄》的反歷史虛构
《英雄》宣揚的歷史觀和价值觀受到猛烈批判。為《英雄》辯護的人說,《英雄》里的故事是虛构,何必當真?這剛好把話說反了。正因為是虛构,所以尤其要當真,否則豈不辜負了編導虛构的一片苦心?
大致上說,歷史小說或歷史影劇的虛构有三种類型。第一种類型,如《三國演義》,是在歷史上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加油添醋。第二种類型,人物和事件都是虛构的,但合情合理;不具事實真實,但具有情理真實。《英雄》的虛构顯然和上述兩种都不同。《英雄》的故事發生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中(這一點編導相當強調),但故事本身是虛构的;關鍵在于,《英雄》里虛构的刺秦故事完全不符合情理真實而且違背情理真實,它不僅不是歷史,而且還反歷史。
對歷史進行反歷史的藝術虛构,通常表明作者對歷史真實非常不滿,因為真實的歷史嚴重地違背了作者本人的价值標准。作者對歷史真實的不滿是如此強烈,以致于他認為,只要他還必須在歷史真實或歷史的情理真實的前提下做文章,那麼,無論他怎樣演義虛构,仍然不能夠充分地表達出他自己的价值觀念,所以,他公然地有意地違背歷史真實并且違背情理真實進行反歷史的藝術虛构,以期突顯作者自己的价值傾向。“改造”歷史,就是用自己的价值觀改造歷史。在被改造的歷史中,作者展示給我們的不是歷史,而是作者自己的价值觀。
舉個例,《蕩寇志》就是一部反歷史的虛构。我們知道,《水滸傳》是根据《大宋宣和遺事》中几段記載渲染演義而成。關于《水滸傳》的主題思想,有人說是“誨盜”,有人說是“忠義”,有人說是歌頌反抗,有人說是贊美投降;也有人說統統不是,《水滸傳》的主題思想無關緊要,作者無非是把一段歷史記載給我們編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又好看又好玩的故事而已。
假如說對《水滸傳》這部書,人們還可以見仁見智,有不同的解讀的話(但是,這不同的解讀決非半斤八兩而無高下之分),那麼,對《蕩寇志》我們就不好這樣說了。本來,根据史書(盡管你可以對其可靠性存疑),宋江一伙确被朝廷招安,可是,《蕩寇志》的作者卻要進行反歷史的虛构,去掉宋江等被招安這件事,改成被朝廷大軍毫無妥協余地的徹底剿滅。本來,早在《蕩寇志》問世之前,梁山好漢的故事就流傳了多年,深入人心;《蕩寇志》的作者要寫《蕩寇志》,顯然就決不只是換個法子講一個有趣好听的故事而已。他是以此來表明他對草寇的深惡痛絕,也是力圖對《水滸傳》流行多年造成的閱讀效果“撥亂反正”。作者堅信,梁山草寇犯上作亂,罪該万死,朝廷何能招安?縱然這伙強盜被招安后的下場也不美妙,那終究還是太便宜了這伙十惡不赦的強盜!所以,作者要把人所共知的一段招安歷史生生抹去,硬是讓梁山好漢一個個都死在官軍的刀劍之下。
讀《蕩寇志》,你不能也不該不重視它的主題思想和政治傾向,因為那正是作者的創作意圖;就象你讀寓言不應該不重視它的寓意。
《英雄》的情況与此相似。刺秦的故事流傳了兩千多年(從《戰國策》到陳凱歌),至今不衰。只要你了解有關的歷史,了解此前關于刺秦故事的种种描述及其社會影響,當你看到《英雄》,你很難不強烈地感受到編導者以反歷史的虛构來作翻案文章“古為今用”的創作意圖。
有趣的是,當年《蕩寇志》的作者和辯護者決不諱言該書的主題思想(事實上,他們唯恐別人不關注);而今天為《英雄》辯護者,卻很少有人敢于堂堂正正地為《英雄》的主題思想和价值取向辯護。他們只是一味地顧左右而言它,假裝《英雄》根本沒有什重要的思想觀念要表達。那是否意味著辯護者們自知理虧心虛,知道他們那套道理端不上台面,只能暗示不可明言?
*對歷史須心怀虔敬
我不敢說,對猶太人,宗教是他們的歷史。不過我确實敢說,中國人缺少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國人不是沒有道德的堅守,不是沒有人生意義的尋求。在別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東西,在我們這里,由歷史提供。別人靠宗教,我們靠歷史。
我們不相信靈魂不朽,可是我們相信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就是說,我們相信人可以通過他的德行、言論或功業流傳后世。不朽就是在人類的延續即歷史中不朽。
我們不相信末日審判,可是我們相信歷史的審判。我們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可是我們相信有公正的歷史。
我們不相信有天堂地獄,我們不相信好人死后會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會下地獄永遭懲罰,可是我們相信歷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將遺臭万年。和其他文明古國相比,中國有著最悠久、最丰富、最連續、最完整的歷史記錄。中國的歷史至少有兩個特點:一是它對真實性的堅持,不畏權勢,秉筆直書;一是它對道德裁判的強調,春秋筆法,意含褒貶。
寫歷史而帶褒貶,某些現代西方學者也許不以為然(注),但是它對我們中國人至關重要。“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在中國,坏人不信地獄而無所不為,能讓他們還有所忌憚的也就只有歷史的裁判了。所以,中國的歷史不能不承擔起道德裁判的職能。
文天祥從容就義,鼓舞他的精神支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秦檜設計害岳飛,一度猶豫不決,不是怕生前被清算,而是怕死后遭唾罵,在歷史上遺臭万年。文革中,劉少奇遭毛澤東陷害,百口莫辯,他只能用這樣一句話安慰自己安慰妻子儿女:“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在中國,歷史是好人在現實生活中能一反趨利避害的本能,堅持道義理想的唯一憑借,是不幸者陷身絕境所能保持的唯一希望,也是坏人雖有赫赫權勢但仍不敢為所欲為的唯一忌憚。越是在極端處境,中國人越是感到對歷史的依賴。“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也許有些中國人不曾感覺過這种依賴,他們以為他們不靠歷史也能合乎道德地生活下去。其實,那只是因為他們太幸運,要太膚淺太懵懂,未曾體驗過或思考過人在此一世界中面對強暴与災難時的孤立無助。
陀斯妥耶夫斯基說:“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尼采說:“上帝死了”。不少中國學者對這兩句話闡釋發揮,啟人深思。但這些議論放在中國的語境,則有隔靴搔痒之嫌。因為中國人本來就不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西方的問題是,由于對上帝的信仰衰落,引發了嚴重的道德危机;然而在中國,道德秩序本來就不依賴于對上帝的信仰。我們的宗教是歷史。宗教出危机是人家的故事,歷史出危机才是我們的故事。如果我們的歷史出現了危机,我們的道德也就會出現危机。
林則徐晚年感慨:“青史憑誰定是非?”此話對中國人的意義,大可以和上述陀翁与尼采的兩句話相比擬。我們中國人一旦對歷史產生了怀疑,怀疑歷史能否沉淀出真實,怀疑歷史能否對人物和事件達到公認的道德定論,怀疑歷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換言之,我們中國人一旦失去了對歷史的天真信仰,我們傳統的道德秩序就整體動搖了(這正是現代中國人所面臨的問題)。
極權統治是歷史的大敵。極權統治者精心地、系統地篡改歷史,用謊言淹沒真實。毛澤東要求“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全盤推翻傳統的歷史評价。但反過來這也表明極權統治者和我們一樣十分重視歷史,它是企圖用自己的一套歷史—-包括自己的一套歷史敘述和自己的一套歷史道德裁判—-取代先前的歷史。它要竊取歷史的神圣光環,所以它依然保留了歷史的神圣外觀。
后期極權主義改變了做法。它不能不改變做法,因為到了極權統治的后期,統治者編造的歷史敘述已經破綻百出,失去欺騙效力;它對歷史的道德裁判也前后矛盾,再也無法自圓其說。在后極權時代,統治者一方面要繼續用老辦法編織和构建自己的那套歷史,另一方面則開始鼓勵對歷史的玩世不恭,竭力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消解歷史的神圣性。
象前些年以“戲說”為名的清朝帝王戲和現在的這部《英雄》,這种影劇歌頌專制,暗中配合“主旋律”;如果你要批評,它又推托道這是戲說是娛樂,何必當真。好比有人假裝酒醉罵人,因為是假裝酒醉,他很知道該罵誰不該罵誰;但你若和他理論,他又擺出一副醉態,倒顯得你小題大作了。
撇開真醉假醉不談,這种對歷史的輕浮態度也是令人懮慮的。昆德拉說:“人類反抗強權的斗爭,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斗爭。”強權對歷史的傳統手法是涂抹和篡改,它企圖以假充真,以惡充善;當這种手法失靈后,它就擺出嘻皮笑臉的輕浮模樣。它力圖讓人們相信,對歷史事實的真偽之辨与對評价歷史的褒貶之爭其實都不重要;別把歷史看得那麼庄嚴,那麼神圣。
乍一看去,對歷史的玩世不恭對權勢者和反抗者一視同仁,對善与惡一視同仁。它既消解了反抗者一方的神圣性,也消解了權勢者一方的神圣性,彼此彼此;但實際上,權勢者可以不要歷史,确切地說,權勢者起初試圖利用歷史,因此偽造歷史(想想《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當偽造破產后,權勢者惱羞成怒,于是就轉而糟蹋歷史,嘲笑歷史,搗毀歷史。但我們不能不要歷史。消解歷史的神圣性導致人們只是“活在當下”,以眼前的利害為生活的唯一准繩,因此它有利于權勢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眾,有利于惡而有害于善。
對于缺少宗教的中國人,如果歷史不再神圣,那麼還有什麼神圣?如果中國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將是怎樣的人生?
(注) 西方學者中,也有人主張歷史具有道德目的。如阿克頓,就是那位以“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一名言著稱的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認為,對歷史作出判斷正是歷史學家的責任。歷史學家在無偏見地收集證据之后,他必須依据這些事實作出判斷和對人格作出描述。他贊同愛德蒙.伯克的觀點“真正的政治原則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則”;他告誡歷史學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脫歷史有權對錯誤實施的永罰。”
(原載“北京之春”118期)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