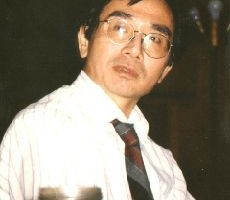【大紀元5月13日訊】一、個人主義:自由之魂
在中國,提到胡適,就必然想到自由主義;而提到自由主義,也必然會想到胡適。毋庸置疑,胡適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樞人物。
胡適的自由主義的倫理基地是個人主義。其思想基礎早在“五四”運動以前就已經奠定。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所受教育以及關於知識分子應當保持中立和獨立的一貫認識都在推動他走上自由主義者的道路。特別是他所接受和倡導的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思想直接導致自由主義。
胡適倡導個人主義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義》一文。這篇文章在五四運動以前對於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產生較大的影響。他在文章中倡導的個人主義在當時確定“最新鮮又最需要的一針注射”(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提倡自由獨立的人格和為我主義的個人主義。他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使之得不到自由發展,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和人格,應當成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張。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一是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到底不能發展個人的人格。”[1]一個自治的社會,一個共和的國家,都應當使個人有自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若不允許個人有自由獨立的人格,“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2]胡適在提倡個人主義的同時,反對狹隘的國家主義。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這是胡適對易卜生個人主義思想的徹底性的認識。易卜生曾經表示,國家的觀念終將消滅,人類觀念終將興起。胡適以此推斷易卜生晚年一定進入“世界主義”的境界。這說明易卜生的人類主義或世界主義思想對胡適是有影響的。
國家主義是個人主義的對立物,也是自由主義的對立物。胡適宣揚個人主義也是為了鏟除國家主義。個人在鑄成自由獨立的人格以後就會產生同國家的惡勢力相抗爭的勇氣。
胡適希望青少年朋友都能像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和斯鐸曼醫生那樣,努力鑄造自己的個性和人格,“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3]中國要擺脫愚昧落後的狀況,需要的不是國家主義,而是個人主義。“歐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面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獨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然而中國的統治者總是把國家主義強制灌輸給國人,以國家利益為借口壓迫個人自由。如此惡習,一代甚於一代。你要個人的自由,會有人說先要爭取國家的自由;你要個人的人權,偏有人講國家主權比你個人的人權更重要。國家主義者千方百計地為壓迫自由人權的行為辯護。胡適直接對此種國家主義進行挑戰。“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打著國家的幌子肆意剝奪公民個人的自由,這是國家主義者和一切奴役主義者的一貫作法。根據他們的邏輯,你若爭個人自由,便會危害國家利益,他們所謂國家利益說到底,就是他們依靠專制主義手段欺壓人民所獲取的既得利益。國家主義所要造就的是完全喪失自由獨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適號召個人要真實的為我,鑄成自由獨立的人格,這是從根底上破壞國家主義和其它一切集體主義和奴役主義的理論。人在形成自由獨立的人格後,自然不會滿足於現狀。自然敢於說老實話,敢於攻擊社會國家的腐敗情形。
簡言之,胡適的自由主義是反國家主義、反集體主義的,個人主義是其本體論核心。這是抓住了自由主義精髓的。
二、清醒獨立堅守不渝
五四當時及以後,在學術界,文化界,思想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爭論,胡適都參與其中,甚至差不多經常都是主角。譬如,關於整理國故,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論爭,關於東西文化的論爭,關於人權問題的論爭,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爭等。五四時期,影響中國文化的思想家和學者,作為領袖人物,人們一般容易提到三位:胡適、陳獨秀和魯迅。論及所受外來影響,魯迅和陳獨秀主要受日本的影響,胡適受美國影響。有人常說,受日本影響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響的思想家比較淺,比較明白。但是這一印象有其盲點。我自己更看重思想的內涵、傾向及生命力。
論及胡適在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影響,顯然,他這種所謂”淺”,並不是沒有內涵,而是把一種久經考驗的思想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才能。從長遠的影響來看,從正確性看,從與人性的黏結程度看,胡適在歷史上,就對中國思想的影響而言,要超越上面提的那兩位。陳獨秀先生走過的曲折道路就不必提了。若論及胡魯二位,這裡特別想指出,胡適是比較有建設性的,其思想相當健康。而魯迅,基本上只有否定性,只是挖中國社會的黑暗面。而魯迅在晚年思想逐漸左傾化,這一點實際上和中國後來的政治社會的悲劇發展有一定的關系。魯迅誠然比較深刻,他對中國社會的黑暗面,極其痛恨,但是由於過於偏激,且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以後,恐怕對中國的知識界的影響,就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時候,甚至是負面的,這使他在晚年一度走入歧途。魯迅在近代中國的否定性思潮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但這種否定思潮後來流於一種虛無主義了。胡適給中國指出的路,像民主與科學,是經得起考驗的,這方面他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若僅有破壞而無建設來平衡,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一片廢墟。簡單說,魯迅的思想很難作為一個建設社會的主流思想,或者說作為一個建設法治社會的主體思想。而胡適的思想則可以說和整個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適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關於人權,關於法治,關於民主,關於自由,他一生都堅守不渝。
開初胡適是想完全作一個學人。他從海外歸國之後,曾有一句話:從今二十年內不談政治。他的想法是現在有些東西還沒有弄清楚,需要研究清楚後再說話。但是後來卻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很多的中國的政治社會事件中去了。那恐怕在當時中國國情下是很難避免的。列強在中國的橫行,特別是三十年代日本逼著中國沒有辦法冷靜下來,中國就走上一條靠發動群眾來進行抗日的風潮。而共產黨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爭取跟日本人打戰,抗日也確實是一個正大光明的題目,胡適當然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他希望能夠效法列寧,接受類似當時德國《布雷斯特條約》這樣要求,然後一步一步建設自己,最後再站起來抗擊。這是兩種不同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在抗戰激昂時代,沒人會聽的進去的。他變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像丁文江,像蔣廷黻都主張新式獨裁,但他認為獨裁不是辦法。獨裁只能飲鴆止渴,會使中國現代化往回倒退。這就是當時一場著名的論戰。民主與獨裁之爭。其實蔣廷黻跟丁文江這些人也是受了現代教育,他們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們覺得中國當時必須要獨裁才能應付危局。然而歷史表明,恐怕胡適是想得更深遠一些。
三、反極權的政治自由主義
胡適作為中國自由主義承前啟後的核心人物,他早期關注的重點,如前所述,主要是自由主義的本體哲學,即它的倫理基地: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及其方法論——實驗主義、懷疑主義、重估價值——等等。簡言之,其中心是強調個性獨立、實驗精神和負責任的態度。在他的後半生,則主要關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其中心傾斜到了政治自由的問題。
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系統發揮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1941年胡適在美國發表《民主與極權的沖突》英文演講,提出民主與極權的兩大本質區別:漸進的與革命的,以個人為本位的與以整體為本位的。1948年9月他又發表了題為《自由主義》的文章,很明顯,此時,他思考的焦點已經轉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上來了。他說:“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中國式的)內心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壓迫的權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縛的權利。”這就是政治自由。 他感慨的是在近代歷史上,“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列舉了各種近代民主制度的創設均與東方人無緣,指出“世界只有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漸發展出好幾種民主政治的方式與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國,也可以用在大國。(1)代議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為正式起始。(2)成文憲,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近代的是美國憲法(一七八七)。(3)無記名投票(政府預備選舉票,票上印各黨候選人的姓名,選民秘密填記)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ustralia(澳洲南部)最早采用的。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胡適指明:“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改革。”他提到”容忍”時,特別指出“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向來政治斗爭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被壓的人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卻漸漸養成了一種容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這就與魯迅先生的“決不寬恕一人”形成了顯著的對比。
蘇聯的社會主義試驗曾經被認為代表了人類未來,當時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胡適本人也曾去蘇聯考察過。胡適的一些朋友包括研究國際法的專家周硬生先生,對蘇聯這個樣板都抱有熱切的希望。但胡適並不如此,他特意撰寫了《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方向》、《關於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致周硬生先生的一封信》兩文來闡述自己對蘇聯的不同看法,對蘇聯的非民主制度提出批評。他預測到“戰後的蘇聯可能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余英時先生指出:胡適“在1947年的中國公開宣稱以蘇聯為首的集團是歷史上‘一個小小的逆流’,更是一個膽大包天的舉動,如果沒有絕對的自信是不可能說這句話的。但是1989年東歐國家的全面崩潰、蘇聯的遽速變革……竟證實了他在42年前的觀察,胡適似乎成為一個‘偉大的先知’了。”這表現了胡適的遠見及其信念穿透歷史的卓越力量。
四、胡適的人權理論與實踐
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權。而在20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曾經有過一次關於人權的激烈論戰。這次論戰,是由胡適於1929年發表於《新月》雜志上《人權與約法》一文引起的。隨後他又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通過這些著作與活動,順理成章地,胡適成為論戰中捍衛人權的中心人物。
這場討論的參與者對人權的概念、性質、范疇以及人權與法治、人權與憲政等問題作了廣泛深入的探討。這場人權討論肇因於對國民黨政權違反人權行為的抗爭,但其意義遠遠超出這一具體的維權活動,實際上演變成為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人權啟蒙運動。在此以前,中國知識界和文化界中系統了解人權者甚少,即使知道一些也比較浮泛,國民普遍缺乏人權觀念。通過這場討論,胡適、梁實秋、特別是羅隆基,以通俗的文章與演講將人權知識推向社會,對於增強國人的人權意識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月派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遂成為人權意識的代表。不幸的是,此後的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淹沒了這一重大課題。直至1949年中國人的人權遭到全面褫奪若干年後的1980年代,人們才從塵封多年的歷史檔案中窺見到當年的人權先驅們的卓越努力及其成就。
胡適的人權思想概括起來不外乎兩點:一曰伸張人權;二曰主張法治。正如其《人權與約法》一文標題所表明,以法治保人權可以說是胡適人權思想的全部主張。人權與法治,這是中國在走向政治文明的過程中屢次被失落的主題,也可以說它仍將是21世紀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問題。胡適的文章一下子就抓住百年主題,這是胡適對中國問題長期思索的結晶。
中國傳統中缺乏權利意識,因此,無論滿清皇朝還是民國肇始,在社會上,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異端”或不同於多數人的“少數”,是談不到任何權利的。以皇權至高無上為理由或以多數人的專政為借口,凡是被認定為鎮壓對象的“逆賊”、“反革命分子”、“敵人”、“反動分子”等,其人權公然可以被肆意踐踏。不給反對派以人權,這在中國社會似乎已是天經地義之事。這種野蠻意識長期流行通暢無阻,正是中國社會踐踏人權的真正深層原因。在20 世紀的諸多中國思想家中,首先是胡適犀利地指出了這一點。在該問題上,胡適的主張同當時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基本主張是,無論一個人的身份如何、政治主張如何、宗教信仰如何,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平民百姓,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共黨嫌疑’,無論是守法公民還是在押囚犯,只要是人,就應享有基本人權,不容褫奪。就應享有人的尊嚴,不容侮辱。而當時的國民黨和後來的共產黨,雖然雙方激烈對抗攻擊,但卻享有共同的特點:否定有普遍的人權概念,肆意踐踏對方的基本人權。只要是敵對者、失敗者,就必然喪失人權保障。身體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剝奪,財產可以任意宰制。只要是發表異端見解的書報,就是‘反動刊物’,統統禁止。 當然,共產黨更是變本加厲,連人權這一概念都成為禁忌,在中共統治下,一般人,甚至中共的自己人,都朝不保夕,時時生活在恐懼之中,遑論敵對分子和思想異端者了。毛澤東時代,那是一個中國人徹徹底底被剝奪了人權的時代。
當年,由於胡適成為人權保障的中流砥柱,導致廣大反響。他對於孫中山學說中的獨裁主義成份,胡適最早產生疑問。胡適以勇敢挑戰的姿態指出:“我們要問,憲法與訓政有什麼不能相容之點,……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11]胡適批評孫中山晚年“對於一般民眾參政的能力,很有點懷疑。”[12]實際上孫中山晚年不僅懷疑民眾的參政能力,而且以民權幌子否定人權,以集體主義否定個人主義,從思想深處轉向獨裁主義。在憲政法治外空談民權,離個人人權而言民權。這種所謂民權主義同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是根本對立的。加上國民黨政府利用孫中山學說公然推行“上帝可以否定,但孫中山不許批評”的文化專制主義,致使胡適不得不對孫中山的學說本身提出挑戰。
除了對國民黨政策和孫中山學說不滿外,直接引起胡適大聲疾呼人權和法治的導火線是當時發生的幾件事情。
一是所謂“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報注銷消息,說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主任和宣傳部部長陳德征提出一個“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該提案提醒人們警惕“反革命”活動,並將“一切反對三民主義的人”視為“反革命分子”。為了鎮壓“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證據。“凡經省黨部及特別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它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陳德征的這一提案為國民黨法西斯專政大開方便之門。只要黨說誰是反革命分子,誰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對於此類案子,不須審問,只憑黨組織一紙證明,便須定罪處刑。“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的這一提案激怒了胡適。他看到提案後忍不住給當時任司法院長的王寵惠寫信,問他對此提案有何感想。在這封公開信裡,胡適對國民黨破壞法律程序和根本否認法治的現象提出了抗義。他責問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紀哪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的嗎?”胡適將此信稿送國聞通訊社發表。但幾天後得知信稿已被檢查新聞的官員扣去,未能刊出。這就更加激怒了胡適。他憤怒地表示:“這封信是我親自負責署名的,不知道一個公民為什麼不可以負責發表對於國家問題的討論”。
一是安徽大學學長被禁案。該學長只因語言頂撞了蔣介石,便被拘禁多天。其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而不能去法院控告任國民黨政府主席的蔣介石。
二是唐山商人楊潤普被軍隊拷打案。楊被當地駐軍拘去拷打,遍體鱗傷,商會代表集體求情也無效。此事還是在國民黨政府公布人權保障令後十一天後發生的。這兩件事表明,上至國民政府主席下至地方駐軍軍管,隨意侵害人權,何嘗受到法律制裁。
面對國民黨政府無法無天肆意踐踏人權的做法,胡適滿腔悲憤地痛吁:“人權在哪裡?法治在哪裡?”通過對上述國民黨政府侵害人權事件的揭露和分析,胡適指出人權的保障與實行法治是分不開的。
因此胡適本人亦遭到迫害。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曾以顛覆罪要求正式逮捕胡適。但由於胡適享有很高的社會威望,遂而免遭逮捕。然而其中國公學校長一職因此被罷免,《新月》雜志也遭查禁。有鑒於此,他成了中國人權的象征性人物,更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核心人物。
五、胡適與台灣民主化
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是產生了實際政治後果的,這就是台灣的民主化。
當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一份自由主義色彩鮮明的雜志《自由中國》雜志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號創刊,雷震先生為主編。當時,胡適雖然人在美國,但他是該刊的發行人和精神領袖。他一直和《自由中國》保持著密切聯系,常常對他的編輯方針提出建議,並且在雜志遭到困難的時候,利用自己的影響與上層關系,設法為之緩頰。從五七年開始雜志就推出15篇系列社論,總題是中國的問題,以”反對黨問題”作為總結,並作為中國問題的樞紐。《自由中國》鮮明地提出,反對黨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就是胡適挑出來的。
胡適自美國返台以後,在《自由中國》的歡迎宴會上發表演說,主張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以取得政權為目標的在野黨。隨後《自由中國》馬上發表了”積極開展新黨運動”的社論。這是胡適對中國的民主包括台灣的民主的轉化的重大貢獻。胡適去世之後,台灣的反對黨運動經歷了曲折艱難的歷程,終於在1986年反對黨正式合法化。這實際上是胡適開啟的道路的延續和發展,這一歷史流程與胡適早年的精神啟蒙是割不斷的。
當年,中國共產黨有意把胡適丑化成似乎像蔣介石的奴才。事實上,他跟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是實質性的,對蔣介石的批評是非常嚴峻的,而且是當眾批評。一九五八年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蔣介石前來恭賀他。他卻一再說總統錯了,當時氣得蔣介石臉都變色了。他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學人,從來沒有向政治權威低過頭。譬如,《自由中國》主編雷震於一九六0年八月宣布要在九月底之前成立中國民主黨,九月四日雷震就被逮捕,並被判處十年徒刑。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立即在九月四日當天,向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此舉甚不明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派運動,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恐將貽笑世界”。這些事實都說明胡適是做了事的,而不是像一些傳言所說的那樣害怕了退縮了。
台灣之所以能夠走向民主化,跟胡適為代表的這樣一群知識分子的風格有相當的關系。在海峽對岸,由於中共建政之初就在知識界開展了大規模的批胡適運動,因此關於他的觀念及行為,大陸民眾甚至學界都很隔膜。所以有關胡適思想與人格的研究,不單是為胡適進行個人申冤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攸關中國未來的前途。對中國人來說,特別是中國知識界來說,胡適先生的命運,他在中國的地位,都是值得反復深思的。
胡適的基本形像,如果從人品學品兩個方面說,他基本上是現代自由主義、理性精神、平實見解和寬容胸襟的代表。這樣一種基本象征,對中國,不管是學術文化界包括對政治社會生活恐怕都是相當重要的。自由主義跟其它意識形態根本不一樣的,在於它基本上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不是一套嚴格的形上學的理念,而且以自由主義為根基確立的憲政體系,是對其他任何意識形態都開放的。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自由主義具有對意識形態的超越性。這個在中國現代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中國提倡自由主義,是努力要讓它變成一個普遍的態度,就是說個人的自由應該受到保障,但我也不被允許侵犯別人的自由,整個社會用法治來保障這種自由,杜絕人權侵犯。而這正是胡適當年身體力行的。所以,簡言之,當代中國國民人格建設的任務,在某種意義上,就就是胡適精神的普遍化。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