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秋,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引人瞩目的大事:一件是美国为主英国为辅的美英联军打打着‘自由‧解放’的旗帜,攻打伊拉克推翻胡森政权之后,仍然受到意外的恐怖袭击,引起反战人士的责难,使美国不得不提出一项新的‘决议案’,要求联合国给予必要的支持﹔另一件是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二十三条立法’,引发了五十万居民‘七一’大游行示威抗议,迫使特区政府首长不得不宣布﹕无限期延后该项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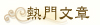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8 人和地的悲哀五十多年来,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最惨重的两大失败是:一、与人斗;二、与地斗。两斗俱伤的结果可以归纳为一个字:穷。与人斗和与地斗,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它的遗祸,如同近来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瘟疫,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一旦发作就很难收拾。因此,要想消弥‘积重’过多的祸害,决非易事。
 2005年2月25日 10:15 PM
2005年2月25日 10:15 PM 7 饿罪难挨一九五九年二月,钢铁师‘班师’回营。不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好歹也还是炼出了钢铁,至于炼出多少,领导人语焉不详,大众又无法过问,好在有毛主席‘成积九个指头,缺点一个指头’的最终定论,就不必计较了。一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电称:一九五八年全国钢产量‘跃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了一番。不管如何,这个数字起码符合‘大跃进’精神,皆大欢喜。我私下想,这一千多万吨钢,不知包不包括钢铁师三团小平炉炼出的那块低炭钢﹖那是技术员小祁鉴定的,锻成一把斧头一把镰刀之后,由我亲自送到省政府大院‘钢铁师成果展览会’上。
 2005年2月24日 9:44 PM
2005年2月24日 9:44 PM 6钢铁师记实今年的国庆节庆祝大会及大游行,特别热闹,花样也特别多。因为是‘大跃进’年,各行各业都要 以‘大跃进的姿态’,‘放卫星的成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献礼。
 2005年2月23日 11:27 PM
2005年2月23日 11:27 PM 5 自留地之争两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国北方平原上,演出过一幕惊心动魄的活剧。一群亡命的贵族重胄,在黄土平原上仆仆奔驰。他们虽然仗剑驾车,但看得出来,一个个衣冠不整,疲惫不堪,饥肠辘辘,难以继续赶路。他们饿狼一般的眼睛,四处搜索,只见荒凉的田垄间,麦苗稀疏,颗粒难觅,哪里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这时,他们发现一个衣衫褴缕的农夫,在田间正低头弯腰除草,动作迟缓无力。流亡者中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走下车来,用尽可能客气的口吻向农夫请求:‘请你给我们弄些吃的东西吧!我们几天没吃过饭,都快走不动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才好。’半天才直起腰来的农夫,看了看这一群路过的客人,叹了一口气,又弯腰从脚下捧起一大块泥土,送到年轻人面前,无可奈何的说:‘没有别的了,只有这个给你吧!’
 2005年2月22日 7:22 PM
2005年2月22日 7:22 PM 4 八月,多事之秋 历史会记住这个时刻。一九五八年八月,是中国现代史上、也许还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在黄帝的故里河南诞生了。在岭南,第一个人民公社急急忙忙投胎,选择在紫气横来、水稻卫星升空的连县。说来凑巧,我的女儿也在连县一家医院里呱呱坠地了。八月二十三日,中国的万门火炮,对准自己的国土家园金门,轮番轰击。同时向世界宣称﹕万炮轰击美帝头子艾森豪威尔!
 2005年2月21日 10:10 PM
2005年2月21日 10:10 PM 3 疯狂的夏天夏收夏种,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繁忙,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弄明白的。我的想象力只局限于上草村,每一个劳动力平均要负担十二亩水稻的收割和插秧,附加犁耙田及施肥。将近一半的田间劳动,要靠每个劳动力的肩膀(挑担运输)才能完成。所以,比平时要多出力,多出汗,甚至加倍的出力出汗,是可以预料的。
 2005年2月20日 9:36 PM
2005年2月20日 9:36 PM 2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上草村只是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在这个生产队落户,有点像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带着自己的户口和粮食定额到这里来,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参加评工记分,一样领取工分票。不同的一点是我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工资关系转到县委组织部,按当地的级别工资标准,每人比原来的工资额都少了一级。
 2005年2月19日 4:49 PM
2005年2月19日 4:49 PM 小 引一九五六年初冬,南岭葱茏。 我在深山里跋涉了七个小时,还不见有一户人家。这时,西山日落,彤云满天,回首来时山路,苍茫无际。正进退两难,忽见树林深处闪出一条人影。等这人走近了,才看清他的模样。只见他一身粗布黑头巾,黑短褂,黑裤衩,头插一根野鸡翎,腰插一把开山刀,脚踏一双十耳草鞋。他肩上扛着一株枯干的大松树,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我让在路边,向他打听我要去的那个瑶排。他两道目光闪电一般在我脸上一扫,扬手朝前方一指,脚步如飞,转眼间消失在浓重的暮霭里。
 2005年2月13日 4:50 PM
2005年2月13日 4:50 PM 特务长杨标真冤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我眼前出现一幅如此不可思议的情景﹕两条细麻绳﹐死死拴住特务长杨标两个大拇指﹐通过小滑轮用力一拉﹐杨标本能地踮起脚跟﹐就在脚尖离地的一刻﹐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杀猪一般地嘶叫起来……。
 2005年2月12日 4:31 PM
2005年2月12日 4:31 PM 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有一篇《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是毛泽东早年从事“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纪实文字。五十年代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北土改运动的某些真实面貌。还有作家丁玲写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获史达林文艺奖的小说,内容和艺术风格都跳不出《暴风骤雨》的格局。此外,再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翻天覆地、生灵涂炭的土改灾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海外某些早已脱离“共产体制”的知识人,偶尔提到当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动沿用当年的套话:什么“土地回家”,“农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记述的,仅限个人所见所闻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2005年2月11日 11:33 AM
2005年2月11日 11:33 AM 陶铸治粤,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至一九六六年窜升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谓官运亨通,风光了得。不料三年后,即被打成“叛徒”、“保皇党”,死于非命。
 2005年2月8日 11:06 AM
2005年2月8日 11:06 AM 鲤 湖 镇 一 役一阵激烈的枪声,震得寒星摇摇欲坠。 鲤湖镇周围十几里数十个村寨、近二十万民众,都从睡梦中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胆子大一点的人,轻轻开门走出来,黑夜里互相轻声打听,又都茫无头绪。小北风刮得很紧,不明来历的枪战,一阵紧似一阵,似乎还夹杂着一两声沉闷的手榴弹爆炸声,更平添几多不安和恐惧。有的缩头蹑足,返身入屋,闭门不出。有的披上一件旧棉袄,摸索着走出村口,试图辨别枪声的方位,希望得到一点什么消息。
 2005年2月7日 2:01 PM
2005年2月7日 2:01 PM 我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学唱国歌。老师把简谱和歌词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字体端正美观,便有一种引吭高歌的欲望;老师拿教杖指着,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学们跟着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里一高兴,课堂上高声唱,下课独自哼唱,放学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纪念周会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较清亮圆润,赢得老师同学赞许的目光,心里未免有些翘翘然。凡上音乐课,我特别起劲,特别投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