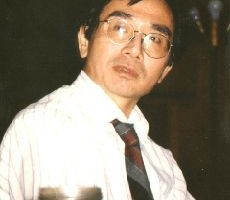【大紀元5月27日訊】
一、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自由派社會活動家。早年的傅斯年領導過1919年五四運動。他是當年5 月4 日遊行的總指揮。次日即出國留學,1926年秋返國。
傅斯年一生,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長和臺灣大學校長。其巔峰時期則是1949至1950年任臺灣大學校長期間,他勵精圖治,一個二三流的大學在其引領下,成為一個學術自由人才輩出制度健全的亞洲一流大學。
作為中國自由派知識群體的一員,傅斯年為人們所記住的,主要不是對自由主義理論的闡發,而是他貫徹自由理念的那些特立獨行的實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作為知識人清醒地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的行為方式。二是在大學校園裏極力伸張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三是作為中國言論重鎮,批評和挑戰政治權力的道德勇氣。
我們首先看他與政治權力的關係:
傅斯年雖然與當時中國的執政黨國民黨有很多淵源,但他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還鼓動他的老師胡適採取跟國民黨保持距離的態度。傅斯年與蔣介石有私交,蔣介石曾寫信給傅斯年,希望傅斯年幫忙請胡適入閣從政,而傅斯年卻在寫給老師胡適的信中說,蔣介石想借重你胡適先生的權威,大糞堆上插朵花,牛糞上插朵花,這朵花就是胡適,要借重你的聲望來給國民黨美化天下。所以,傅斯年說,胡老師,你可不能幹。他說,蔣介石這個人,表面誠懇,其內心是上海派,上海的流氓嘛,我跟蔣介石八九年的經歷,我太瞭解蔣介石了。
1946年蔣介石曾任命傅斯年為國府委員,他堅辭不就,並說自己乃一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並說:“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稗益,若在社會,或可以為一介之用。”書生本色,昂然而顯。
1947年1 月15日,蔣介石請傅斯年吃飯。席間蔣介石提出要當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傅斯年極力反對,說“北大亦不易辦,校長實不易找人,北大關係北方學界前途甚大。他(指蔣——編者注)說可以兼著。我說不方便,且不合大學組織法。他說不要緊(蔣的法治觀念甚微)。”後來胡適也沒有答應。這件事也體現了傅、胡二人要維護大學獨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傅斯年自己也有機會入閣,但他始終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個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才能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他曾寫信給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傅斯年在蔣介石統治的歲月裏,代表那種無黨無派的真正自由主義路線的人。他們要發揮知識份子對權力的批評制衡作用,不被國民黨同化。鑒於一般人都被政權吃掉了,或者沒有地位了。而胡適、傅斯年他們還有那麼一點點地位,所以他們孤軍作戰的情勢和勇氣就顯得特別矚目,賦有某種悲劇感,這也象徵了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者整體上的悲劇命運。
二、
在履踐自由主義理念方面,傅斯年最主要貢獻是在教育學術領域,是在大學校園裏極力伸張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維護學術自由、教育特別是大學獨立;二是力促大學以學術為重心,維持高度的學術水準。
臺灣大學——現在國際上的學術排名超越中國大陸的北大清華——正是傅斯年實踐自己自由主義教育理念及其制度設計的主要基地。台大,凝聚了傅校長的非凡的夢想和心血。有學者評論所說:“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面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傅斯年尖銳地指出:“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於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
1949年國民政府遷移臺灣後,國民黨從反面總結在大倫失敗的教訓,強化了鎮壓異議的恐怖氣氛,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遭遇更為嚴酷的政治環境。當局推行聯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要連坐。
傅斯年面對這種高壓,仗義而起:一面不准軍警隨意入校捕人,一面對當局聲明,台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聯保制度在台大無法推行。在當時的恐怖氣氛下,這樣做是需要極大的道義勇氣和崇高的擔當精神的。
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革除權貴子弟降格入學的陋習。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即便因此而得罪權門也在所不惜。
傅斯年在去世前不久致友人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不無欣慰地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雖然不是沒有麻煩。”在當時的情勢下,這一成就更加值得大書特書,勢將載入史冊。
學術自由是大學不可或缺的條件;但僅止於此是不夠的。傅斯年關注大學的另一焦點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學術水準。為此,他提出了台大辦學的基本宗旨:
1.辦學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義為主宰。他說: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強之目前功利為主宰”,而且“直到民國初年,大學只是一個大的學堂。”“今之大學制度仍不能發展學術,而足以誤青年、病國家。”如此狀況,必須改弦更張。他強調通才教育,高深學術。
2.嚴格挑選校長和教授,不能讓政客和不學無術之輩混跡其間。“做校長的必須教員出身,否則無直接的經驗、切近的意識,其議論必成空談,其行為當每近于政客。”。而“大學以教授之勝任與否為興亡所系,故大學教育之資格及保障皆須明白規定,嚴切執行”。
3.嚴格區分大學和中學的教學方法。“大學教育是則是培養一人入於學術的法門中的。”“大學生之訓練正是研究室之入門手續也。”不能將“大學化為中學”!
傅斯年的這些辦學方針與蔡元培、胡適一脈相通。這是一縷自由主義的教育脈絡,它影響了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學教育,從而使大學在當年中國社會的混亂局面中,相對獨立,相對乾淨,與國際社會主流教育界的差距在日益縮小。然而,自從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的大學盲目追隨蘇聯,強行實施所謂“院系調整”,把原有的已經建成體系的中國教育降格為黨的“馴服工具製造廠”,以培養“革命的螺絲釘”或“技術文盲”一類的“專家”、“工程師”相標榜,毀了幾代中國青年,至今後遺症仍然嚴重。以此對照傅斯年當年對中國教育界的告誡及其深謀遠慮,人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超絕卓識和博大胸襟。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