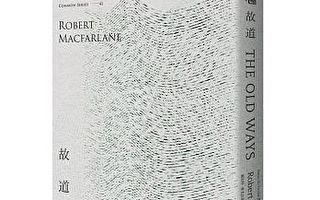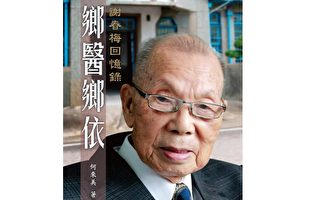“夜莺计划”拯救了无数人,但挽不回生命。那些来不及解释的歉疚,来不及道出的爱,与那个永远不愿掀开的秘密――尘封在阁楼置物箱的那张身份证,让这一切重新翻涌了起来。
*1
*一九九五年四月九日,奥瑞冈州海滨
如果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曾学到什么,那就是:爱,让我们明白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战争,让我们体会自己是怎样的人。
现在的年轻人想要知道关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他们以为谈谈说说,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那个世代比较静默。我们了解遗忘是多么重要、重新出发是多么美好。
但近来我发现自己一直想着战争、我的过去、一个个我已遗落的人。
遗落。
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我忘了心爱的人们在哪里;说不定我把他们留置在他们不该在的地方,然后掉头离去,困惑得甚至不知如何追溯来时的脚步。
他们没有遗落。他们也没有置身更加美好的处所。他们已经逝去。随着人生渐趋落幕,我已领悟哀伤有如懊恼与悔恨,进驻于我们的DNA之中,永远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自从先生过世、获知诊断结果之后,这几个月来,我老了不少。我的皮肤皱纹累累,看起来像是一张人们试图压平、重复使用的蜡纸。我的眼睛经常不管用——黑暗之中、车前灯一闪、或是下雨之时,我的眼前就一片模糊。
视力变得靠不住,实在令人不安。说不定这就是为什么我发觉自己一直回顾过去。往事之中怀带着我现今再也无法瞧见的明晰。
我试着想像我逝去之时终将得到安宁,我也将与每一个我曾爱过、我已遗落的人相会。最起码我会得到谅解。
但我应该知道不可能,不是吗?
***
我那栋名为“峰园”——百余年前由一位林业大亨兴建的屋宅已上市求售,我也已准备搬家,因为我儿子认为我应该这么做。
他试图照顾我,也想让我看看在这段最难过的日子里,他是多么爱我,所以我耐着性子,任由他管控。我哪在乎我在何处离世?而这正是重点。
我住在哪里已经不重要。我在奥瑞冈州海滨住了将近五十年,这会儿我把过去的岁月装箱打包,我想带走的东西并不多,但我挂念一事。
我伸手抓住悬吊而下操控阁楼阶梯的把手,阶梯从天花板伸展而下,好像一位绅士伸出他的手。
我走上阁楼,阶梯不太牢靠,脚一踩就摇摇晃晃。阁楼带着霉味,一个灯泡在头顶上晃来晃去,我拉一下灯绳。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困在一艘老旧的汽船里。墙上铺着宽长的木板,木板之间的蛛网密布,团团蛛网悬挂在空中,发出银闪闪的光芒。天花板相当高耸,极为倾斜,我站在阁楼正中央才可以挺直身子。
我看到那张孙儿们小时候使用的摇椅,还有一张旧婴儿床和一个看来破烂、弹簧底座已经生锈的摇摆木马,我也看到那张我女儿在病中整修的椅子。
一个个箱子沿着墙壁叠放,上面标注着“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锅碗餐具”、“运动用品”,箱箱皆是我已很少使用、却割舍不下的物品。
对我而言,坦承自己不再装饰圣诞树形同撒手放弃,而我始终不善于放手。我要找的东西塞在角落:一个贴满行旅贴纸的扁平置物箱。
我使劲把置物箱拖到阁楼中央悬挂在头顶上的灯泡下方。我在箱旁跪下,但双膝一阵刺痛,所以我靠着箱子,慢慢坐下。
三十年来,我首次打开箱盖。最上层的置物盘堆满小宝宝的纪念品。小鞋子,小手的陶印,画满细长小人和笑脸太阳的蜡笔画、成绩单、舞蹈彩排的照片。
我抬起置物盘,放到箱外。
箱子下层的纪念品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几本皮面精装的日记簿,封面已经褪色;一叠以蓝色缎带系绑的陈旧明信片;一个一角压扁的硬纸盒;一套朱利安‧罗西诺所着的诗集小册;一个装了数百张黑白照片的鞋盒。
最上面是一张发黄褪色的纸片。
我双手颤抖,拿起纸片。那是一张战时的身份证。我看着证件上那张小小的半身照,照片上是个年轻女子。茱丽叶‧吉威斯。
“妈妈?”
我听到我儿子踏上嘎嘎作响的木头阶梯,脚步声与我的心跳声一唱一和。他刚才有没有大声叫我?
“妈妈?你不应该上来这里。天啊!这些阶梯不稳。”
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跌一跤就……”
我摸摸他的裤管,轻轻摇头。我无法仰头一望。
“别说了。”我只说得出这一句。
他跪立,然后坐下。我闻得到他的刮胡水,淡淡的,略带辛香,我也闻得到一丝烟味,他先前偷偷在外面抽了一支烟,他多年之前戒掉这个习惯,但获知我的诊断之后故态复萌。我无需表明我的责难:他是个医生。他应该很清楚。
我直觉地想要把身份证丢进箱里,用力阖上箱盖,再度把它藏起。我已经藏了它一辈子。
如今我已来日不多。虽然不至于很快就撒手西归,但也拖不了多久。我不得不回头检视我的一生。
“妈,你哭了。”
“是吗?”
我想要告诉他真相,但我不行。我说不出口,想了真是难为情。到了这个年纪,我应该什么都不怕 ――尤其是我自己的过去。
我只说:“我想要带走这个置物箱。”
“箱子太大。我会把你要的东西重新打包,装进比较小的盒子里。”
他试着管控我,我笑笑回应:“我爱你,而且我生病了,所以我任由你指使,但我还没翘辫子。我要带着这个箱子过去。”
“你真的需要箱子里的东西吗?那些只是我们的手工艺品和其它废物。”
如果我老早告诉他真相,如果我多跳几次舞、多喝醉几次、多唱几首歌,说不定他会看到真正的我,而不是一个平凡、可靠的母亲。
他挚爱的那个我并不完整。我始终以为我想要被爱、被仰慕。如今我想想,说不定我想要被了解。
“当做是我最后的请求吧!”
我看得出他想要叫我别这么说,但他生怕自己不禁哽咽。他清清嗓子。
“你前两次都挺过来了,这次也可以战胜病魔。”
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我身体孱弱,情况不稳定,除非藉由药物之助,否则睡不好,也吃不下。
“当然没问题。”
“我只想确保你平安无事。”
我微笑。美国人可真是单纯。
我曾经跟他一样乐观,认定世间安全稳当。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谁是茱丽叶‧吉威斯?”朱利安说。
一听到他说出那个名字,我有点震惊。
我闭上眼睛,在弥漫着霉味和前尘往事的黑暗中,我想起过往,思绪有如一条直线,划穿时间与空间。我违背了自己的心意――或说我顺服了自己的心意,谁搞得清楚?――想起了往事。◇(待续)
——节录自《夜莺》/ 新经典文化出版公司
(点阅【夜莺】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