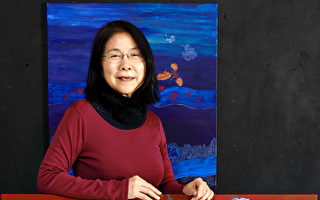【大纪元2023年12月15日讯】
【背景说明
本文初稿曾在1999年台湾经济学会年会中发表,后经匿名审查后刊登于学会该年论文集。本文与谢宗林先生合撰,主要是谢先生主笔,然主要的观点正可呼应本书第十二章的内容,本文对科技的解析值得大家思之再三。】
一、前言
国内外讨论如何提升一国产业科技实力的研究报告不在少数,但很少有明白交待其所采用的科技概念的。尽管如此,由于它们大多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中讨论问题,其字里行间和论述脉络隐约透露新古典经济学的科技概念倾向;因此,我们研判该科技概念已经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本文虽然也是讨论有关科技发展的问题,但所采用的科技概念和新古典经济学有极大的差异。由于概念上的差异,对于问题的认识和政策的建议就有显着的影响。因此,我们将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科技概念作为讨论的起点,首先详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科技概念,指出一些重要的事实反证,接着再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科技概念,以及我们对产业科技发展问题的认识,最后再就技术研究与移转课题,以政府采购补偿性交易措施为例说明之。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科技概念
从西方现代知识论(epistemology)的标准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科技概念不仅隐晦而且贫乏。此一学术传统有关科技的理念完全隐藏在抽象的“生产函数”定义之中。所谓生产函数是指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品(产出)之间的实物数量关系。对应于任何假定的投入组合,我们原则上可以从给定的生产函数检索出一个确切的最大可能产出数。相关的论述显示,新古典经济学者认为,此一确切的最大可能产出数,不是反映真实存在于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而是反映“厂商”本身的知识[1]。对于此种知识的性质,新古典经济学的文献罕有直接的论述,以致有些钻研产业技术发展史的学者说,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生产知识被包裹在“黑盒子”里[2];因此,我们只能旁敲侧击新古典经济学倾向的科技概念。
生产函数所代表的知识显然不是纯知识或科学知识(pure or scientific knowledge),而是有目的取向的行动知识或技术(purposive action knowledge or technology)[3]。有些新古典经济学者以整套生产蓝图(a book of blueprints)为例,开导初学者认识生产函数所蕴含的技术概念。他们似乎认为产业技术大多可以、而且已经用语言或其它符号表达出来[4];并且只要懂得所用的语言与符号,一旦生产蓝图在握,任何人都原则上可以立即运用其所代表的知识,进行自己认为有利的生产活动。
“生产蓝图套”指涉的形象,也颇契合生产函数定义所隐含的一个特色: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技术知识,和“厂商”在任何时点的实际生产要素投入、乃至实际生产组织与活动,系两种分属不同层次、截然分离的概念。新古典经济学将技术知识整个委附在(抽象的)“厂商”身上,而“厂商”则通常被看成是某一个企业家(entrepreneur)。它所谓的技术知识是独立于具体的生产设备、独立于受雇职工的人力资本,并且独立于实际的生产活动之外的。这种知识可以说是飘浮在空气中的一种能力(a floating intelligence or capacity),它随时能够像玩弄积木那样组合生产要素以获得想要的产出或结果。换言之,真诚的新古典经济学者“要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如此这般的汽车厂商:它虽没有任何汽车生产设备,没有雇用任何汽车工人,也没有生产任何汽车,然而却拥有生产汽车的能力,随时能够生产市场想买的汽车。”[5] Nelson and Winter (1982)对此直呼不可思议。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分别“厂商”的生产技术和实际的生产活动原本是无可厚非的;这种概念上的分别,表示新古典经济学忠于西方知识论的一个基本传统—知识不存在于客体,而是存在于主体的知者身上。从常识的观点来看,前述抽象的汽车“厂商”之所以匪夷所思,关键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将技术知识“整个”委附在被拟人化的“厂商”身上,从而把事实存在、而且极为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工与专业化现象—复杂分散的知识能力无法被任何个人或委员会集中掌握和统一规划运用,以及其所衍生出来复杂的知识协调问题,一股脑的扫进“生产函数”的黑盒子里。
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将“厂商”内部知识分工、专业化、复杂化,和协调的问题扫进黑箱,对于“厂商”的技术知识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也欠缺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在新古典经济学者公认最为严谨、最为深奥、因此“科学”地位也最为崇高的市场均衡模型中,“厂商”的技术知识是给定不变的(given and immutable);“厂商”之间只有市场价格媒介虚拟的(virtual)讯息接触,没有真实的(real)技术资讯交流与学习。单从此类模型的推演,我们无从猜测它们是否假定“厂商”之间技术资讯交流的成本非常高,以致没有技术交流;抑是“厂商”之间没有技术差异,毋需相互学习,所以没有技术交流[6]。标准的市场均衡模型在技术交流问题上保持沉默与模糊的立场,反映新古典经济学者习惯以“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预设架构讨论技术创新与扩散的问题,亦即,新古典经济学自始预判技术创新与扩散过程不受市场诱因的制约,当然无法在它设想的任何市场模型里加以讨论[7]。新古典经济学者大多认为,技术创新主要源自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旦基础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人们一起对自然界就会有新的认识,而这种一般性的科学新知自然而然会被应用到许多个别的产业,带来新产品和新制程技术,从而全面提升经济生产力和人民福祉。由于假定产业技术进步密切仰赖最新发现的科学新知,而一般性的科学新知(乃至比较特殊性的应用科技知识)不仅很难,而且也不应该由原始发现者(或应用科技的发明家)享有独占专用的权利,让他能够从竞争的生产与交易过程获得足够的报酬,所以大家应该运用政府强制的力量,补贴、甚至组织科技研发工作。新古典经济学呈现的科技创新概念也许可以称为直线性的技术创新模型(a 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8]。它认为技术创新的单向因果源头(科学新知)位于市场(生产与交易)过程之外;在整个市场模型的层面而言,生产技术基本上是一个外生变数(exogenous variable);无论就全体或个别“厂商”而言,科学知识都是一项无限耐用、且不可分割的生产要素投入;一旦有了科学新知,“厂商”的技术水准便可以自动提升,但“厂商”却无法个别自市场购得此一生产要素;因此,技术进步多半有赖英明的政府刻意、且系统化的协助。
我们认为,直线性的技术创新概念不仅(1)夸大科学新知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忽视技术创新过程的自发性与原创性(autonomy and originality);而且也(2)夸大技术创新与个别特定的(severally specific)生产(乃至销售)过程的可分割性(separateness)。换言之,我们认为,至少就现代制造业生产技术创新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夸大政府以行政裁量手段(或所谓政策措施)协助产业技术发展的效能与正当性。[9]让我们接着就前述命题稍作说明。
三、科学与工艺技术
就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远比直线性模型所呈现的复杂许多。古希腊文明未曾发展出任何系统化的自然科学,罗马帝国和中国亦然,尽管这些文明都有璀璨的工艺成就[10]。专就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而言,在19世纪中叶以前,自然科学对工艺技术也未曾有过重要的贡献。18世纪的工业革命是在没有科学奥援的情况下完成的。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除了摩斯电报机之外,没有任何一样重要的工业生产设备或产品,与前此50年取得的科学成就有关[11]。19世纪中叶以后,虽然有愈来愈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有关,但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与时间落差,事实上因研究领域(subject matter)与历史情境的不同而各异,无法一概而论[12]。科技研发虽然同样涉及物体,但追求的价值不同,因而科技之间若即若离的现象并不难理解。
科学家(scientist)追求自然界潜藏的系统化真理,其主要旨趣在于比别人独到深入,而且精确了解永恒的物体性质,而技术发明家(technologist)的主要旨趣则在于展现巧思,安排一些已知的事物(包括经验的与科学的法则,以及特定的情境事实),以取得他人尚未料想到的利益。技术发明家热情专注的对象不是自然界永恒的规律,而是如何让已知的事物按照比原来便宜的新方式运作,以达到某一个预定的目的,并且带来较大的利润。在寻找新的问题,在搜集线索,以及在思量种种可能的答案和展望时,技术发明家必须注意许许多多不停流转的情境利弊因素。他必须对人们的种种需求感觉敏锐,必须能够评估人们愿意花费多少代价来满足那些需求。对于走马灯似的情境,技术发明家必须热情关切,而科学家则否,后者的心思专注于自然界内在的永恒规律[13]。换言之,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知识,是以真假来衡量的,原则上无关现实的目的;而技术发明虽然也是一种知识(确切的说,是有目的取向的行动知识),其衡量标准却是:针对预定的现实目的,它有用的程度多大,亦即,它所指导的行动其成功概率几何。
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的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两者的工作方式与态度各异。对此,英国昆虫学家V. B. Wigglesworth(1899 – ?)在论及科学家参与解决二次大战期间的实际问题时,曾有颇为精辟的观察,值得引述。他说:“在过去他们所习惯的纯科学工作领域里,如果他们无法解决问题A,他们也许便转而尝试解决问题B;而正觉得问题B解决无望时,他们也许突然发现了问题C的线索。然而他们现在却不准规避,必须仅针对问题A,提出某一解决之道。此外,还有许多他们未曾想过的麻烦限制,让他们觉得徒然增添实际工作的难度:有些解决之道不能用,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另外有些解决之道不能用,因为所需的材料太贵了;再有些解决之道也不能用,因为它们也许会搞出人命或危害健康。总而言之,他们发现应用生物学不是‘让智力较差的人去搞的生物学’,而是一门全然不同的领域,需要全然不同的工作态度与心思。”[14]
鉴于在许多领域,科学的研究落后工艺技术的发展,有些科技史学者乃认为科学与技术为一互动性的过程。例如,Mowery and Rosenberg(1989 pp.33~34)指出,“到了20世纪,工艺知识领先科学发现的情形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当今许多科学的研究工作,旨在整理技术发明家早就发展出来的知识和实用的方法,使之系统化,展现其内在逻辑。工艺技术对科学发展有重大的形塑作用,因为它领先取得了某些知识,从而对科学家提供了一些‘有待解释的’资料,吸引科学家尝试解释或以更深层的法则综合表达那些经验资料。”因此他们认为,“若想深入了解以往科学如何影响与形塑工艺技术,必须注意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也必须牢记,过去的经验显示,迅速扩张的工业社会的工艺需求,往往是从非常简单的、而不是从尖端的科学得到满足的。自19世纪末以来,科学研究的方向……愈来愈受命于工业成长的需要。”[15] 前面第一段引文似乎搞混了科学与工艺的知识性质;而第二段引文虽然不无见地,但不无夸大现实需要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近代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愈来愈受命于工业和国家经济或军事发展的需要,也许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科学发现(scientific discovery)愈来愈反映现实的社会需要。[16]恰好相反,科学史的考察清楚说明,任何对科学本身不感兴趣的人,是不可能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的;同样的道理,任何对科学发现本身的价值无动于衷的社会,是不可能成功促进科学发展的[17]。换言之,现实的需要是不可能触发重大的科学发现的,而专注于现实需要(例如,“船坚炮利”)的社会是不可能会有好的科学发展成绩的。由于科学与工艺是两个原则上截然不同的领域,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往往不易共事。例如,欧本海默(J. R. Oppenheimer)谈到二次大战主持原子弹发展计划的亲身经验时曾说:“科学家对于发展工作的现实顾虑无不感到忿怒,而关心发展的人则无不认为科学家懒惰、没用、也不认真工作。所以实验室要不很快变成全是科学家,就全是关心发展的人。”[18]
虽然科学与工艺是两个原则上截然不同的领域,但此一原则界定并不否认有一些研究领域具有两者的某些性质,因此可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有些仍具经济价值、但比较古老的工艺(例如,纺织与冶金)主要是技术家从“经验试误”(trial and error)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科学未曾提供显着的帮助。另有一些重要的现代工艺则与其形成对比,例如电子和大部分的化学品工业技术,是技术发明家将科学新知应用到现实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如果某一项技术只是科学的应用,那么它对科学就不会有丝毫的贡献。相反的,从经验试误发展出来的技术,正因为它本身是非科学的(unscientific)[19],反而可以提供科学研究的问题与线索。
对应前述的观察,我们或许可以界定两个介于科学与工艺技术之间的研究领域:系统性的技术(systematic technologies)和技术性认可的科学(technically justified sciences)。像电子工程学和气体力学这些近代所谓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s),虽然可以仿照纯科学的方式加以培育,但实在应该归类为系统性的技术。虽然也被名为科学,但它们实为技术的性质相当明显,因为如果经济环境发生激烈变化,导致它们丧失经济价值,它们就会被冷落,乃至被完全遗忘。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纯科学,原本也许不是科学家热情研究的领域,但因为可以提供大量非常有用的技术发明资料,所以被认为特别值得加以培育。例如,关于煤、金属、羊毛、棉花,等等物质的科学研究,或可归类为技术性认可的科学。
前述那两个介于纯科学与纯技术之间的领域,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许会合而为一。例如,胰岛素的发现开启人体内分泌科学研究的新页,本身即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然而,它同时也发明了一个可以操作来治疗糖尿病的技术。大部分的药理学(pharmacology)也具有与此相同的特性。有些自然界固有的变化过程因为会产生重要的自然结果而深具科学意义;如果这些结果也是人们所欲求的目的,而我们又凑巧能够照自己的意思操作或启动那些变化过程,那么就会有这里所讲的科学与技术合一现象。但这种特殊的合一现象,原则上并不妨碍科技应该被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活动领域:工艺知识离不开实用目的,而科学知识则无关任何实用目的。[20]
上文提到Mowery and Rosenberg(1989)说“当今许多科学的研究工作,旨在整理技术发明家早就发展出来的知识和实用的方法,使之系统化,展现其内在逻辑。工艺技术对科学发展有重大的形塑作用,因为它领先取得了某些知识,从而对科学家提供了一些‘有待解释的’资料,吸引科学家尝试解释或以更深层的法则综合表达那些经验资料。”当中所谓的科学研究,指的似乎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与冶金工艺相关的科学研究。在同一篇文章里,他们指出“十九世纪后半叶冶金技术科学(the science of metallurgy)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先前冶金技术的许多创新。因为了解柏赛麦及其后之炼钢法生产出来的钢品特性,牵涉到重大的商业利益,所以才有此一科学的发展。在分析各种炼钢法和各种矿源投入的产品性质方面,科学研究的成绩特别可观。诸如钢品老化现象或钢品脆度和燃料之间的关系,不仅科学家有研究兴趣,而且也是钢品生产者和使用者极为关切的问题”[21]。他们此处所谓的科学和我们所谓技术性认可的科学意义应该是一样的。果然,则他们所谓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能说是“旨在整理技术发明家早就发展出来的知识和实用的方法,使之系统化,展现其内在逻辑”—这句话比较像是在形容我们前面所谓系统性的技术;然则说系统性的技术研究能够“以更深层的法则综合表达”原有的工艺知识,也不是完全妥当—因为工艺知识多半含有非常重要、但无法表明或言传的成分。他们之所以搞混技术性认可的科学和系统性的技术,似乎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工艺是行动知识的特质,而误以为任何工艺知识最后都可以被科学或其它系统性的法则取代。
前文提到工艺知识是有目的取向的行动知识,这是说它教导人们按照某一套(或多或少可以标明的)规则(rules)行动,利用某些工具或材料(implements),以取得特定的现实利益(material advantages)。此处所谓的“规则”指的是人为的操作规则(artificial-operational principles),包括一般所谓产品设计(product design)与制程设计(production engineering)所体现的原则。此处所谓工具与材料不是依其物理或化学性质来归类或认定,而是依其是否有助于行动目的,依其是否能够满足操作规则所要求的功能来归类或认定。例如,假设我们想把钉子敲入木板,则对应的操作规则将教导我们如何运用榔头敲钉子,而被我们当做“榔头”用的工具,除了普通所谓榔头之外,可能还包括枪柄、鞋跟、厚实的字典等等,它们并无一定的物理或化学性质。又例如,任何机械专利事实上都是在保护某个操作规则。机械专利都会陈述机械的操作规则,亦即,陈述其各个特殊部分扮演什么特别功能,以及所有的功能怎样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运作的整体,以达到该专利机械的设定功用。发明者也通常希望他的专利所涵盖的范围愈广愈好,所以都会尽可能抽象的陈述他所发明的操作规则,除非必要,否则尽可能避免提到任何实际建构专利机械的材料特性或尺寸。如此得到专利保护的机械概念所指涉的物体,其实际构成的材质与形状大小可以是五花八门的。[22]
由于任何操作规则有其相应的目的(即前此所谓特定的现实利益),而就那目的来说,操作规则的价值在于它是满足该目的的一个“理性”的方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将操作规则视为一个“理想的”操作标准。例如,手表的操作规则是手表是否正常满足目的要求的标准。换言之,任何机械正常如何运作的概念都隐含一个反面的判定:未能依其概念运作的机械都不是正常的。当锅炉爆了,机轴裂了,或火车出轨了,我们说这些东西没有依照原来设定的操作规则在运作。然而,除了让我们能够说那些东西坏了,操作规则却不能够让我们对坏掉的东西说或做些什么其他的。曾经受过物理与化学训练的工程师,也许能够解释依照正常操作规则建构的机械偶尔失灵的原因[23]。他也许观察到某些零件变形导致机械损坏,或者腐蚀作用使机械失效。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也许能够找出,决定机械零件是否发挥原设定功能的物质条件。这种科学知识也许可以用来改进机械免于失常,但绝不可能涵盖或取代定义机械是否失常的操作规则。事实上,不问任何现实目的的纯科学家,单凭其科学知识是无法分辨一台机械和一堆废铁的。[24]
以上主要就技术性认可的科学无法涵盖工艺知识加以说明,未明白提到系统性的技术。尽管如此,由于系统性的技术虽然有人称为科学,但实为技术,有其特定的现实目的,所以当然也不可能被化约成可以表明的科学原则系统。接着,我们要说明,撇开工艺知识的目的性不谈,即使是经过系统化努力的工艺知识,也不完全是可以表明或言传的。
四、工艺知识与技巧
上文曾提到Nelson and Winter(1982)根据一般事实认识的观点,指责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厂商”概念不可思议。当时我们曾指出,其不可思议的关键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将技术知识‘整个’委附在被拟人化的‘厂商’身上,从而把事实存在、而且极为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工与专业化现象—复杂分散的知识能力,无法被任何个人或委员会集中掌握和统一规划运用,以及其所衍生出来复杂的知识协调问题,一股脑的扫进‘生产函数’的黑盒子里。”现代社会或厂商内部生产所运用的行动知识之所以无法被任何个人或单位集中掌握,至为重要的关键因素则在于:形形色色的行动知识是分散在许许多多的个人身上,不是存在于货栈或百货公司的橱窗里,而个人身上的行动知识当中,有相当重要的成分却是无法定义或标明的,因此是不可言传的;在某种适当的互动架构与环境下,这些许许多多个人“知道做但不知道说”的知识能力,也许尚有发挥的机会,但因为它们是无法言明传输的,所以绝对无法被集中掌握和统一规划运用。这种个人不可言传的知识能力,是个人以经验试误的方式在各种社会与企业传统中学习得来的,因此是一种介于人类天生本能与理智中间,而且是因人而异的能力[25]。同样的道理,技术发明家在传统的经验试误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工艺,不用说有许多尚未得到科学的研究分析,以“使之系统化,展现其内在逻辑”;即使花了大把银子进行科学或系统性分析,所获得的操作法典或手册,往往不足以全盘解释工艺之所以成功的因素,遑论依赖那些操作法典或手册,他人就能够实际重演那些工艺。简言之,我们认为现代工艺也具有所谓传统技巧当中无法认定的成分。
大约300年前,意大利有一位识字无几的木匠,名为史特拉底瓦里(Stradivarius,1644 – 1737)。他例行生活制作的小提琴,至今仍有数把流传,被公认为琴中极品。台湾台南奇美博物馆(原名艺术资料馆)由于收藏了其一而名闻国际。历年来,不断有人应用显微、化学、数学、电子等等现代尖端科技,尝试制作可以媲美史特拉底瓦里的小提琴,却都没成功[26]。现代人之所以无法复制史琴,可不完全是因为现在再也找不到他所使用的材料,而是主要因为不知道如何重复他的制作技巧,且让我们进一步仔细剖析所谓技巧究竟是什么东西。
一个很会游泳的人,我们说他游泳“技巧”很好。从他在游泳池里一再游来游去,一般人大概都能看出他的动作遵循某一套规则(或者说,他的肌肉运作呈现某一套操作规则)。熟悉浮体力学的人也许还会说,会游泳的人之所以不会沉下去的道理。他的呼吸方式和不会游泳的人不一样—吐气时,他不会尽吐胸中之气,吸气时,他则比平常人吸入更多的空气;如此呼吸可以保持较大的浮力。不用说一般泳者,即使是游泳教练,也不一定说得出此一让泳者保持浮力的呼吸之道[27]。同样的道理,假设使史特拉底瓦里再生,他也许说不出自己何以能成功制作名琴的操作规则[28]。游泳的例子说明技巧普遍具有知道做(know-how)出操作规则,但不知道说(know-that)出此操作规则的特性。
下面这个例子则说明,以科学方法分析技巧的成分,所得到的行动准则(maxims or rules of art)不能取代技巧,亦即,行动准则不是技巧的全部,知道一些行动准则不等于知道如何展现技巧。许多人会骑脚踏车,但包括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和脚踏车制造者在内,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脚踏车骑士为何能够保持平衡的道理。根据简单的力学分析,骑士遵守如下所述的规则。当他开始向右倾斜时,他将脚踏车的把手向右转动,让脚踏车前进的轨迹向右弯曲。于是产生一股离心力,将骑士向左推,抵消把他向右下方拉的重力。脚踏车把手向右转的动作,暂时让骑士向左倾斜,于是他接着将把手向左转动;如此这般操控把手,使脚踏车沿着一序列适度弯来弯去的轨迹前进,也让自己平稳坐在脚踏车上。简单的分析告诉我们,对应于一定的倾斜度,适当的前进弯度和脚踏车前进速度的平方成反比。
然而知道这个保持平衡的规则,是否就等于会骑脚踏车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不要说骑士显然无法做到按照倾斜度相对于前进速度平方的比例,来调整前进弯度;即使他真能照着做,他也必然摔下来;因为实际骑车的动作还必须将许多没有纳入规则陈述(不管是一般性或是特别情境)的因素也一并纳入考量。概括的说,任何技巧都是一个整体性的动作;有系统的观察与分析整体动作所获致的一些规则(rules of art),其本质好比是处世格言(maxims);“正确”应用规则虽然是行动成功的部分因素,亦即,规则虽然有指导“正确”行动的用处;但是,如果完全严格遵照规则来行动,则不一定成功,或许失败成分居多;就好像完全严格遵照格言处世,则人生必然处处荒谬。事实上,如果不是已经多少知道如何实际操作技巧(或做人),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人所陈述的技巧规则(或处世格言),遑论应用那些规则成功展现技巧(或做人)。[29]
由于技巧的奥秘多半无法全部认定,因此技巧多半只能模仿而无法言传。例如,前文附注(28)提到日本松下(Matsushita)电气公司1984 -1987年间开发Home Bakery的故事。开发人员跟随在大师傅身旁,全心全意认同大师傅的目的或工作价值观,模仿大师傅的每一个动作,在不知不觉当中学得搓揉面糊技巧的规则,包括连大师傅自己也从来不知道说的,当然也从来没察觉到的关键性规则。由于技巧无法言传或言教,只能经由学徒模仿师傅的身教而得到留传,加以个人生活接触范围有限,所以技巧通常具有地方性,一些特定的技巧通常不是到处可见。再者,也由于技巧的奥秘多半无法全部认定,因此模仿学习虽然有个已经存在的对象,不是毫无章法,但仍然是一个无法全部认定的摸索试误过程,从而既是一个学徒个人发现,也是学徒个人创新结合的过程;例如,跟随同一个师傅的各个学徒,学得的技巧各有其个人独特的色彩或风格。一般所谓传统的东西,包括法律和政治传统,也都含有此处所谓技巧的成分,都具有地方性色彩,而继续存在的传统也通常是缓缓变动的传统。[30]
就所谓传统手工艺技术而言,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它具有此处所谓技巧的特性。至于以传统技巧的概念来理解现代工业技术,一般人乍听之下也许觉得难以接受。第一个反对的理由也许是:传统技巧欠缺现代工业产品的划一性。第二个反对的理由也许是:在现代工业生产过程当中,传统手工技巧要不是多半被机械取代了,就是被生产装配线支解成为简单的动作[31];而设计机械或生产线所需的技术知识,则已经被系统化写成书本或文章,变成一般化的资讯了;因此,从前是学徒跟随师傅几无章法的学习传统技巧,而现代工业技术则到学校里有系统的学习技术的科学逻辑。第一个反对的理由很容易排解:传统工艺产品具有工艺家个人风格,并不表示个别工艺家的产品不具有划一性;而现代汽车工业产品具有划一性,也不表示所有汽车公司的产品都一样。
第二个理由基本上是新古典经济学者典型的生产技术概念。它所谓的技术知识是独立于具体的生产设备、独立于受雇职工的人力资本,以及独立于实际的生产活动之外的;“生产函数”上的任一点,都代表一座按钮工厂(turn-key plant),只要一按下电纽,工厂就启动,按照固定的速度喂进原料和简单的人工动作,产品就依固定的速度不断流出。此一工业生产概念也是所谓“科学管理学派”追求的理想:它主张若要提高生产效率,则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人性因素都应该去除,人应该被转化为对一定刺激呈现一定反应的机器。然而事实却不然,而且被彻底严格“科学管理”的企业理想不仅无法实现,执著于“科学管理”的企业也不具市场竞争力。[32]即使像纺织和炼钢这些经过长期系统化努力的现代工业技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无法标明的技巧仍然是决定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关键因素[33]。而且虽然书本上的规则陈列与逻辑演练并非毫无益处,但实际有效应用那些得到陈述的操作规则,仍然有待经验试误的磨练所取得的技巧;虽然这种技巧不是指尖上的技巧,然而若非这种应用技巧也像传统手工艺技巧那样无法全部标明,否则科技落后国家也不致经年累月苦于所谓的技术移转问题了。
在进一步说明技术移转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处理第三个可能反对将现代工业技术视为传统技巧的理由。有人也许觉得前此的论述,只是说明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仍然需要许多具有手工艺技术的工人,而这并不等于说个别企业的生产技术,就整体而言,具有传统技巧的特性。之所以有此疑问,很可能是因为现在还有许多人以“科学管理”的预设概念在思考现代企业的问题。“科学管理学派”有很奇怪的“科学”(science)与“理性”(rationality)概念。它不仅认为科学的内含是纯粹客观的东西,都是可以事实或逻辑证立并且表明的,完全没有个人特殊的判断或无法言传的信仰因素[34];而且它还认为只有利用被它称为科学的东西,来指导与规划设计一切行动,我们才真正是理性的,也才会成功。[35]因此,它才企图以客观系统化的动作规则取代职工的个人经验与技巧。这种将员工物化的概念,看不见员工个人的经验与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知识来源,误以为光凭企业管理阶层应用“科学”“理性的”规划设计与严格操纵,就可以保证企业成功;即使生产过程中,个人技巧事实上仍然存在,那也被看成是一种无助于生产效率的意外不幸或干扰因素,而且也只表示生产过程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理性”规划设计与严格操纵。以这样的概念来经营家庭小型工业,虽然难成大器,也许还无伤大雅。但,我们可以决然断言,它绝对不可能用来成功经营现代所谓知识或研发密集的企业。事实上,它不可能理解这种企业;因为后者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适当的组织架构,除了可以让许许多多员工自主发挥其个人身上难以言宣的行动知识,以形成某种合于组织生产目的的复杂秩序之外[36],还能够不断的进行自发学习与创新技术。前述复杂的生产秩序或许多少还能被“理性”规划设计,但自发学习与创新则决然不能。自发学习与创新虽然不是没有目的的摸索,但它显然不是一个可以事先被“理性”规划设计与严格操纵的过程;它也绝对不是一个在已知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演的过程,而是一个涉及逻辑跳跃的过程—创新的程度与逻辑跳跃的幅度成正比。[37]Nonaka and Takeuchi(1995)说的好:“技术创新的精髓在于按照某一特定的价值理想或想像的远景再造整个世界。创新技术的意义,就等于是整个企业的再造。它是员工个人与企业不断自新前进的过程。它不单是研发、策略规划、或市场行销部门等等少数几个专家的责任,而是企业上下一体的责任。”[38]此种企业整体活动的操作规则若是可以被完全标明,或者不能被标明的部分不重要,大概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企业管理和创新理论不断出现,而落后国家的技术升级就只会是个非关实现能力的简单意愿问题。由于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就操作规则而言,现代知识或研发密集企业的整体活动过程,和传统手工艺技巧或游泳或骑车一样,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键性成分。进而言之,我们认为,现代知识或研发密集企业所操作的生产技术,是特定企业在特定的企业传统氛围中摸索学习和创造出来的特定传统技巧,不是一般化、可以普遍应用的知识。而且正如任何活的传统(例如,语言)一样,有市场价值的企业生产技术也必定不断求新求变,以适应外在的环境。
二十世纪著名的数学与哲学家怀海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论及十九世纪欧洲文明的发展时,曾说“十九世纪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新特色,是它的工业技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些没有关联的伟大发明。(从技术创新与扩散的速度来看),我们很难不觉得,除了发明之外,还有其他较不为人所知的新东西。……十九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于是一个崭新的方法进入人类的生活。若想了解我们这个年代,我们也许可以忽略所有的变化细节,诸如铁路、电报、收音机、纺织机、化学合成染料等等。我们必须把焦点对准这个发明的方法本身;它才是真正的新奇,它粉碎了旧文明大部分的基础。”[39]十九世纪迄今,全世界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上赶上了欧美工业先进国家。根据这个事实来研判,怀德海所谓发明的方法,似乎不仅仅包含他自己点出的科技研发职业化与科技人员训练系统化,而是多半还包含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键性部分,因此特别不容易学会。[40] Polanyi (1958)有一段相关的观察,在此特别值得引述。他说:“在全世界数以百计新成立的大学里,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科学内容虽然能够被成功传授,但无法认定的科学研究技巧却大多还没有渗透到这些大学里。一些于四百多年前发展出现代科学方法的欧洲国家,现在尽管变穷了,但和海外许多科学研究经费较为充裕的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多、也较显着的科学新发现。若不是年轻的科学家有到欧洲当学徒的机会,以及若非有些欧洲的科学家移居海外,一些海外的研究中心在科学研发上是极无可能取得寸进之功的。”[41]我们觉得引文当中的“科学”很可以换成“现代工业技术”来读,而“国家”在此则可以当成“企业”(特别是所谓知识或技术密集“企业”)来看。
五、技术研发与移转
就比较综合的层面而言,现代经济学界有关技术研发与移转的文献,特别是在所谓“国家技术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这个标题之下的文献,主要是想在某种程度内有系统地认定怀德海所谓“发明的方法”的操作规则。就正面的目的而言,迄目前为止的文献是令人失望的。例如,Nelson and Rosenberg(1993)指出,就研发组织或相关制度与技术创新表现之间的关系而言,由于经济学界迄今仍没有任何清晰连贯、而且多少通过验证的分析架构,学者每每随意各自不同地选择少数几个变数加以观察而不顾及其它,以致相关的文献充斥许多真假难辨的因果论述[42]。有些学者甚至没有仔细观察评估多少实际资料,就率尔人云亦云,以致积非成是。例如Lynn(1985)抱怨说:“一些在专家意见交换的场合被暂时提出来讨论的假设性解释,竟然被当真引用纳入花俏的理论分析当中。专家学者们一再互相重复,于是一些刻板印象愈来愈似乎是真的”[43]。尽管如此,从反面的角度来看,那些文献也并非毫无意义—它们都在反证“现代知识或研发密集企业的整体活动过程,和传统手工艺技巧或游泳或骑车一样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键性成分”。此外,虽然他们无法标明认定整个技术创新过程的操作规则,但他们一些零星(然而却)实在的观察,却可以确切地告诉我们,技术与其创新过程不是什么。这种反面的观察,应该也有助于我们更接近了解技术及其创新过程。因此,值得在此摘要叙述,做为下文讨论“补偿性交易措施”(offsets)的参考资料。
(1) 现代工业技术大多不是一般化的知识,而是许许多多个别企业特用的知识。换言之,即使是在同一产业,甲企业的技术大多异于乙企业的技术,其技术之特殊差异化一如其产品特殊差异化。在大多数技术先进国家,被视为研发(R&D)支出的金额当中,至少有60%是发展(D)支出,亦即,大多是用来改进或发展特定产品或特定制造过程。在企业的层次,不包括正常生产设备投资在内,技术创新的费用分配情形大约是:研究10~20%;发展30~40%;生产工程设计30~40%;上市推销10~20%。这样的经费分配隐含10~30%的企业研发所需要素投入来自于外界(主要是大学与政府实验室),而其余则由企业自筹。实证研究显示,有很高比例(40~60%)的企业生产技术是企业自己创新研发的,来自其他企业的技术只居于次要的地位。之所以有如此几乎是常态的现象,不完全是因为创新技术的企业不愿意对外提供新技术。许多实证研究显示,即使没有智慧财产权的障碍,技术移转仍有其他重要难题。例如,企业如果自己没有既熟悉内部生产条件、又能够独立研究技术瓶颈问题的科技专家做为“看门人”,则即使是发表在公众期刊上的公开资讯,对企业的问题也丝毫无用。而且,即使在同一企业内,不同工厂之间的技术移转也需要接受技术的工厂花费钜大的学习成本。[44]换言之,“技术移转”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名词,换成“技术学习”也许比较适当。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技术移转”一词太过消极,让人以为受者不必有什么动作。然而实际上,除非受者有积极的态度,花费人力物力,否则无法发挥新技术的成本或品质效益。再者,订契约“购买”技术的说法也不怎么精确。取得操作新技术的能力不像取得网球拍,只要到店里花钱买来就算了。它倒比较像是“学习”打网球;参加网球训练班有助于得到打网球的技巧,但学会打网球的责任绝大部分是在学生自己的身上。[45]
(2) 现代工业技术创新过程和实际生产(乃至销售与售后服务)过程有显着的重叠,亦即,技术创新过程多半伴随密集不断的实际生产调整与学习。这种调整与学习的成果大多附着在特定的员工身上,无法有效标明成为系统化的操作规则,不可能和不在技术研发现场的外人全部分享。换言之,现代工业技术的操作规则无法全部标明,而其标明的部分也不是局外人看了就可以理解的。
(3) 综合前述诸点,我们也许可以确定的说,有市场竞争价值的技术,主要是生产特殊差异化产品的特定技术,主要是特定企业内部逐步试误摸索累积得来的特定技术。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设计能力,也是企业成功吸收外来特定技术的重要必备条件。吸收外来技术的过程,一定也是调整或增补该技术,以适应新操作环境的过程。因此,新创技术的移转(或更好说是学习)或扩散,也是某种技术创新的过程。简言之,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是决定吸收外来技术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46]
(4) 独立于生产事业的技术研发机构,对于产业技术升级虽然有用,但事实证明只能扮演次要与间接的角色。之所以如此,主要也是前述技术特性与技术移转的问题使然。独立的研发机构开发出来的技术,多半要不是不契合产业的要求,就是很难移转给产业使用。据报导[47],台湾工研院史钦泰院长于1998年五月间指出,“过去外界在讨论企业研发面临的困境时,大家常常为没有成果所苦恼,而眼前的问题却是如何妥善运用(国内研发单位取得的)研发专利。根据统计,真正能被使用的,比例仅及一成。”企业需要的是相当“特定的”技术(譬如,“特定”到和企业本身的条件以及外在环境契合的程度),不是独立研发单位以整个产业不分畛域为设想对象而端出来的技术。从使用者角度看来,如果不合己用,再怎么先进的技术也还不够成熟到可以采用。在印度,类似的问题似乎更严重。[48]
(5)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往的技术移转政策主要是,鼓励跨国企业参与直接投资提供技术,或办理“整厂”技术输入。由于这两种方式皆未能激励本国企业积极提升技术水准,目前许多开发中国家乃转而一方面要求跨国企业在当地设立研发单位或代为训练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开发中国家也设法要求供应进口技术的跨国企业,尽量把技术“拆散”(unpack the imported technology),将部分设计与发展的工作交给本国企业或独立的研发单位来做。相对的,日本从前在发展本国技术能力时却不是如此。日本从前拒绝外人直接投资,其提升本国技术能力的方法主要是所谓“逆向工程”,本国企业几乎百分之百必须自己承担模仿学习与改进技术的责任。[49]比较国际间发展技术能力的经验,我们似乎可以说,尽管外力的协助(如果真的是免费的)当然是多多益善;但,若想提升本国技术能力,不仅最好不要有遇到困难就想仰赖他人解决的念头,而且更应该体认到,自己尝试解决困难,即使失败,所学到的一定比抄袭别人现成的成功还要多。
(6) 最后要摘要记述的是前提事实的政策涵义。对于为什么某些国家在某些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比其他国家发展或学习得更快,大多数学者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然而根据许多技术发展经验的国际比较研究,大家对于以下三点似乎颇为笃定:一是就制造业技术而言,政府和学术机构虽然能够从旁协助,但绝无可能取代企业本身的研发努力;二是教育与训练体系品质的良窳,影响本国企业所能吸收到的科技人力,攸关本国的技术能力表现,应该是任何政府投注的主要对象;三是总体经济与贸易政策必须刺激,甚至强迫本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50]第一和第二点的理性(rationale),上文若不是已有交代,就是显而易见。关于第三点的理性,我们在此要提醒读者注意思考上文附注(40)当中所引怀海德的那一句话。关起门来在国内市场仰赖政府青睐眷顾与享受特权的企业,终会丧失许多荣耀生命、但不可捉摸的特质,由而“懒洋洋、纵容自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人生乐趣,以致于堕落沉沦”。相对于“显而易见的人生乐趣”,致力于现代科技发现与创新显然需要一股“傻劲”,因其预期的满足可能非常遥远、不可测也。而当我们说日本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很有“敬业”精神时,我们说的正是他们的“傻劲”。没有日本人普遍的“傻劲”或“敬业”精神,要想成功发展科技真是戛戛乎其难也。
六、补偿性交易措施与技术能力升级
补偿性交易措施是晚近产业技术方面的热门课题,但在全部有关产业技术的经济学文献当中,补偿性交易措施文献所占的份量极少。另外,这方面的文献多半只是叙述某些补偿性交易的型态,搜集此类交易量实际的成长趋势(特别偏重军事采购相关的补偿性交易资料),然后详细讨论一、两个实际发生的交易个案;其主要的旨趣似乎只在于提醒经济学者注意,有些实际交易个案不符合教科书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简单概念[51]。极少看到有文章评估补偿性交易的边际成本(例如,附带补偿性条件的采购成本,究竟比无此类条件的采购成本高出几何)或其边际效益(例如,产生多少技术移转效果或就业机会);换言之,很少有文章企图模仿前提“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文献,尝试不管是定量或定性的因果关系论述[52]。尽管如此,对于定性评估补偿性交易的技术移转效果,此类文献提供的一些实际资料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在此摘要叙述。
首先以军备采购为例,说明此处采用的一些补偿性交易型态(或方式)之定义。原则上,军备采购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型态。一个极端的型态是由本国企业全权负责设计与生产(indigenous projects)。另一个极端则是购买国外企业(或政府)设计与生产出来所谓“现成的”(off-the-shelf)设备。从采购者的角度来看,第一个极端的采购形态所带动的本国企业研发与生产活动量最多,而第二个极端所带动的本国企业活动量则最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采购形态,例如,合作研发与生产(co-production)、专利授权生产(licensed production),以及附带补偿性交易条件(offsets)的国外采购,所带动的本国企业活动量大小则介于两者之间。所谓合作研发与生产(简称合作生产),顾名思义指的当然是“买卖双方合作生产某产品,其中也包括技术移转、人才培训等”;专利授权生产,“即卖方授权买方生产某种产品”;而国外采购可能附带的补偿性利益,则有“技术移转、联合投资(joint ventures)、教育训练与人才培训、共同研究与发展(R&D)、贸易拓展(即直接从本国购买现成的产品与零组件)、直接投资(即在本国投资建立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或其他(例如、协助发展旅游事业)”[53]等等国外军备供应商向本国企业提供的赚钱机会。
前述诸多五花八门的补偿性利益,如果和购入之设备有直接的关系(例如,“贸易拓展”项下涉及的产品或零组件是国外设备供应商生产该设备所需之部分产品或零组件;又例如,“技术移转”项下涉及的技术是生产或维修购入之设备所需之知识),一般称之为直接的补偿性利益(direct offsets);至于和购入之设备没有直接关系的利益(例如,国外供应F-16战机附带提供在本国合资设立轻油裂解工厂的机会,或者承诺购买本国五星级旅馆度假券等等),则称为间接的补偿性利益(indirect offsets)。一般文献中,补偿性利益(offsets)一词,除了指涉前述直接与间接的补偿性利益(所谓“狭义的”补偿性利益)之外,也概括指涉前述所谓合作研发与生产和授权生产(所谓“广义的”补偿性利益)。
对于不熟悉补偿性交易文献者来说,前述的定义也许会产生一些困扰。且让我们从技术能力与发展的角度,点出合作生产、专利授权生产,以及(狭义) 补偿性交易的异同。以合作生产、专利授权生产、或(狭义)补偿性交易条件等三种方式采购军事设备,显然都涉及买方的企业和卖方或多或少分享采购案所带动的研发与生产工作(work-sharing)。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前述三种工作分享的方式有时候很难严明区分。例如,比较F-16战机的国外供应商“专利授权”买方企业“生产”战机配备的驾驶座椅,和该F-16供应商向买方企业购买该类驾驶座椅以冲销补偿性交易承诺额度;前者为“专利授权生产”(co-production),而后者为(狭义)“直接的补偿性交易”(direct offsets),但在这两种采购方式之下,买方企业似乎都以同一模式分享了采购案的供应工作,亦即,都一样承担了生产驾驶座椅的工作。然而读者却必须注意,该两种工作分享方式在这个例子里有如下之关键性差异:依补偿性交易条件供应驾驶座的买方企业,应该已经拥有生产该驾驶座的技术,所以补偿性交易不一定涉及技术移转或学习的成分,而专利授权生产则显然要求卖方向买方企业提供特定的生产技术[54]。这一点特别值得详述。
尽管在(狭义)补偿性交易条件的协议中,偏好取得新生产技术的买方通常会给予一些技术移转项目较大的补偿金额冲销权数,以鼓励卖方提供技术给买方的企业;但无论从技术移转(或学习)的主控权或买卖双方的技术差距来看,(狭义)补偿性交易可能带来的技术能力发展利益,均远逊于合作生产和专利授权生产。就二次大战之后,西欧诸国军备采购方式的沿革而言,在广义的补偿性交易方式当中,起初各国最常采用的方式是授权生产,接着有合作生产方式之兴起,而(狭义)补偿性交易则是1970年代以后才发展出来的[55]。军备采购(或其他复杂系统之采购)所涉及的国外授权生产,其意义不仅在于买方企业因此能够供应本国(或第三国)一部分特定的采购需要,更在于买方除了原来必须具备相当成熟的技术能力之外,还必须花大钱维持一整条特定军备的新生产线。同样的道理,要以合作研发和生产的方式采购军备(例如,1975年General Dynamics和欧联合作生产998架F-16战机的计划,其中650架供应美国,348架供应欧联;依合作生产契约,欧联预估可以得到279架产值的工作机会)[56],买方除了原来必须具备(相对于卖方而言)相当成熟的技术能力之外,还必须肯花大钱特别装置部分新生产线。换言之,以授权生产或合作生产的方式采购军备,买方虽然一方面比较能够按照自己的目标引进或发展生产技术,比较不用担心购入的设备往后的维修问题,而采购支出对国内经济也有较直接与较大的激励作用;但另一方面,买方的采购花费则必然比买国外现成的设备高出许多;因为买方不仅采购时要花钱买技术,采购之后还要继续花钱维持买来的技术。由于美国生产的军备性能愈来愈高,美欧之间的技术差距愈来愈大,而欧洲诸国则失业问题严重、政府预算受限,既无力也不愿意花大钱扩建自己的军备生产线与维持自主的军备技术能力,所以逐渐才有(狭义)补偿性交易条件出现,以部分取代原来西欧诸国偏好的授权生产与合作生产模式。它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买方国内的工作机会,而不在于引进或发展特定的新生产技术。政府采购附带的补偿性交易条件,通常要求国外供应商(及其国外下包厂商)向买方的本国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增加购买一定额度的特定商品与服务。即使买方在(狭义)补偿性交易协议中,以较高的额度冲销权数鼓励卖方移转技术给买方本国的企业,但由于究竟要移转何种技术的主控权完全属于卖方,再者因为技术移转和学习的成本随着双方技术差距而增加,所以卖方迫于(狭义)补偿性交易协议而提供的技术,往往若不是买方不觉得有价值的,就是买方自力足以发展的。[57]其实,根据前文关于技术研发与移转的论述,(狭义)补偿性交易协议比较欠缺技术移转效果乃意料中事:学习新技术本质上是个别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学习者需要有旺盛的企图心。因此,真正有心取得新技术的企业,首先考虑的取得方式很可能是类似“逆向工程”的自力发展,再来考虑专利授权生产(licensed production)或合作生产(co-production),至于透过补偿性交易协议而来的善意施舍,则是可有可无,不能倚赖。
此一猜测和中华经济研究院1993年的厂商意见调查结果颇为一致。该次厂商问卷调查,探询各种政府措施对提升产业技术的重要性程度。根据该问卷调查,国内厂商平均认为比较有用的政府措施依序为:(1) 科技人才的培训与延揽(平均分数2.145),(2) 研究开发与投资的租税减免(2.119), (3) 政府对国内产品之采购(1.820),(4) 融资与低利贷款(1.755),(5) 创新技术之研发补助金(1.586),(6) 国外技术引进与移转的辅导(1.508),(7) 全面提升产品品质与验证的辅导(1.261),(8) 政府对国外产品采购签订工业合作互惠协定(0.767),(9) 建立行销据点及通路的辅导(0.663),(10) 自创品牌的辅导(0.598),(11) 对智慧财产权的法律保障(0.546),(12) 建立中心卫星工厂制度(0.221),和(13) 高科技工业园区之设置(0.182)[58]。“政府对国外产品采购签订工业合作互惠协定”排名第八,其重要性积分(0.767)和排名第七者(1.261)有显着落差,显示(狭义)补偿性交易利益实际可能带来的技术发展效果相当有限。
国外的经验也显示,由于有价值的技术多半是未标明的知识[59],所以涉及技术移转的(狭义)补偿性交易协议特别不容易管理与落实执行,技术移转的效果当然不佳。另一方面,补偿性交易利益并非免费的午餐,亦即,如果买方要求的补偿性利益愈多,则采购成本愈高。因此,世界各国目前有关补偿性交易利益的协商哲学,一方面倾向于简化补偿性交易协议的项目范围,尽可能在协议中标明买方想取得的特定技术或想分享的工作,以减轻管理补偿性交易的行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倾向于放弃依采购个案分别协商补偿性交易利益,而改以通案授予投标资格为条件,寻求和国外特定著名企业建立长期技术策略联盟的关系,集中引进国内企业认为有利可图的生产技术[60]。
七、结语
一般人以“技术”(technology)此一单数名词名之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异质的开放集合(open set),包含不确定数目、各有其特定目的与特定操作环境的行动知识。而行动知识一定是“参与”某一个人或某一企业组织“生命”的操作规则,不是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就行动知识的意义而言,技术不会自动扩散,也不能被移转,只能被学习。“学习技术”表示某人(或某企业)憧憬他人(或他企业)某一外显的生命表现,希望自己也能够有类似的表现。成功习得某一技术,绝不表示学习者能够复制他人(或他企业)的操作规则,亦即,绝不表示让学习者有类似表现的操作规则等于他人的操作规则。因此,学习技术成功,也表示学习者本人创新技术成功。成功没有理论,也没有公式(即,没有足资依循的理论或公式以保证成功);成功隐含逻辑跳跃,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学习者本人如果没有旺盛的企图心,想改变自己的生命,如果只是营营苟苟于一些显而易见的满足,则学习绝不可能成功。换言之,学习技术是有世俗代价的。学习的代价由政府来承担(例如,政府运用补偿性利益补贴个别企业学习国外的技术),当然可以减轻学习者面临的世俗压力,然而其降低学习成功不确性的效果极为有限。此外,政府也必须考虑,技术不会自动扩散,而且技术也不是通用的东西,亦即,技术本身没有外部性或外溢效果。除非是生产真正的共用财(例如知识)所需的技术,否则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架构下,政府补贴学习技术很少有正当性可言。
进而言之,有市场竞争价值的技术,主要是生产特殊差异化产品的特定技术,主要是特定企业内部逐步试误摸索累积得来的特定技术。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设计能力,也是企业成功吸收外来特定技术的重要必备条件。吸收外来技术的过程,一定也是调整或增补该技术,以适应新操作环境的过程。因此,新创技术的移转(或更好说是学习)或扩散,也是某种技术创新的过程。简言之,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是决定吸收外来技术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再者,考察二次大战之后,西欧诸国军备采购方式的沿革而言,在广义的补偿性交易方式当中,起初各国最常采用的方式是授权生产,接着有合作生产方式之兴起,而(狭义)补偿性交易则是1970年代以后才发展出来的。后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买方国内的工作机会,而不在于引进或发展特定的新生产技术。政府采购附带的补偿性交易条件,通常要求国外供应商(及其国外下包厂商)向买方的本国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增加购买一定额度的特定商品与服务。即使买方在(狭义)补偿性交易协议中,以较高的额度冲销权数鼓励卖方移转技术给买方本国的企业,但由于究竟要移转何种技术的主控权完全属于卖方,再者因为技术移转和学习的成本随着双方技术差距而增加,所以卖方迫于(狭义)补偿性交易协议而提供的技术,往往若不是买方不觉得有价值的,就是买方自力足以发展的。其实,根据上文关于技术研发与移转的论述,(狭义)补偿性交易协议比较欠缺技术移转效果乃意料中事:学习新技术本质上是个别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学习者需要有旺盛的企图心。因此,真正有心取得新技术的企业,首先考虑的取得方式很可能是类似“逆向工程”的自力发展,再来考虑专利授权生产或合作生产,至于透过补偿性交易协议而来的善意施舍,则是可有可无,最好不要倚赖。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1.孙克难(1997),〈政府采购政策与产业发展〉,中华经济研究院,工业局委托研究报告。
2.邹继础(1996),〈经济成长:理论与台湾经验之省思〉,载于于宗先、吴惠林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之演变》,第二篇,中华经济研究院。
3.杨小凯(1999),〈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香港《信报财经月刊》,7月,268期,页3~12。
英文部分:
1. David C., Mowery, and Rosenberg, Nathan (1989), 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 Freeman, Christopher (1988), “Japan: a New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 in Giovanni Dosi & et. al.(1988, eds.),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St. Martin Press, New York.
3. Hall, Peter and Markowski, Stefan (1994), “On the Normality and Abnormality of Offsets Obligations” , in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1994, Vol.5.
4. Hayek, F. A. (1974), ‘Nobel Memorial Lecture: 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 collected in F. A. Hayek(1978),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Kagami, M. and Humphrey, J. eds. (1998), Learning,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Adjustment,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okyo, Japan.
7. Lynn, Leonard H.(1985), “Technology Transfer to Japan: What We Know, What We Need to Know, and What We Know That May Not be So” in Nathan Rosenberg and Claudio Frischtak eds. (1985),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Concepts, Measures, and Comparis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8. Markowski, Stephan and Hall, Peter (1996), “The Defence Offsets Policy in Australia” in Martin, Stephen ed. (1996), in The Economics of Offsets, Hardwood Academic Press, Amsterdam.
9. Martin, Stephen ed (1996) in The Economics of Offsets, Hardwood Academic Press, Amsterdam.
10. Nelson, Richard R. and Rosenberg, Nathan (1993),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Systems”, in Richard N. Nelson (1993, 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Nelson, Richard R. and Winter, Sidney 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US.
12. Nelson, Richard R. (1990), “ On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Their Acquisition ” in Robert E. Evans and Gustav Ranis eds. (1990),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sso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Westview Press, Boulder, AZ.
13. —(1990), “Capitalism as an Engine of Progress”, in Research Policy, 19(1990), pp.193-214.
14. Nonaka, Ikujiro and Takeuchi, Hirotaka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Pavitt, Keith (1985), “Technology Transfer among The Industrially Advanced Countries: An Overview”, in Rosenberg and Frischtak(19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16. Polanyi, Michael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 Rosenberg, Nathan (1982), Inside the Black Box :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18. –(199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for the Asian NICs: Lessons from Economic History”, in Robert E. Evans and Gustav Ranis(1990, eds.), op. cit..
19. Whitehead, Alfred N. (1925),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注释
[1] Richard R. Nelson and Sidney G. Winter(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p.60。
[2] Nathan Rosenberg(1982), Inside the Black Box :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p. vii.。
[3] 参见前注1所引文献p.60。此处采用Michael Polanyi(1958),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pp.174 – 184关于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区分。
[4] 参见前注1所引文献p.63。在成长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晚近虽然有“内生”成长模型的出现,将人力资本、学习因素等纳入,但本质上还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生产函数“黑盒子”的根本理念,即使最近华裔新秀经济学家杨小凯与J. Sachs共创新兴古典成长模型,试图将古典学者的理论以数理方式处理,骨子里还是流着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同的血液,说得白话一些,这些模型里都没有活生生的“行为人”,只有划一的机器人。因此,我们以新古典经济学涵括之。
[5] 参见前注所引文献p.61。
[6] 新古典的市场模型容不下技术创新与扩散的问题,并不表示该问题不能在某些非新古典的市场模型里被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熊彼得的《经济发展理论》便是两个著名的例子。
[7] 参见Nathan Rosenber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for the Asian Nic’s: Lessons from Economic History’, in R. E. Evenson and G. Ranis (1990 e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sso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8] 请参阅Richard R. Nelson(1990),‘Capitalism as an Engine of Progress’, in Research Policy 19(1990)pp. 193 – 214, esp. pp. 210 – 212。
[9] Michael Polanyi, op. cit., p.181。
[10] Michael Polanyi, op. cit., p.182。
[11] David C.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1989), 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pp.1 – 34, esp. p. 23 -4。
[12] Michael Polanyi, op. cit., p.178。
[13] Michael Polanyi, op. cit., p.178, fn.1。
[14] David C.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op. cit. pp. 33 – 34。
[15] 关于事实为何如此演变,有兴趣的读者或可参阅Michael Polanyi, op. cit.当中有关Laplacean Research Program, Utilitarianism, Marxism的论述。
[16] “科学发展源自社会现实需要”是新马克思科学史观的特色主张。参见Michael Polanyi, op. cit., p.238。
[17] Michael Polanyi, op. cit., p. 220 ‘No important discovery can be made in science by anyone who does not believe that science is important in itself, and likewise no society which has no sense for scientific values can cultivate science successfully’.
[18] 引自Michael Polanyi, op. cit., p. 178。
[19] 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前科学的”(pre-scientific)。
[20] 以上三段文字主要摘译自Michael Polanyi, op. cit., p.179。
[21] Mowery and Rosenberg, op. cit., pp. 31 – 32。
[22] 摘译自Michael Polanyi, op. cit., pp.328 – 9。
[23] 由于我们允许操作规则偶尔不能达到相应的目的,前文所谓操作规则是一个“理性”的方法云云,当中的“理性”应该解读为Herbert A. Simon所谓的“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一般而言,任何工艺技术成功运作皆需适当的环境条件,因此对于环境条件的理解不足,常是技术运作失灵的主要原因。
[24] Michael Polanyi, op. cit., p. 329。
[25] Friedrich A. Hayek(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pp.22 – 23, and 75 – 79。
[26] Michael Polanyi, op. cit., p.53。
[27] 英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与哲学家Michael Polanyi,有一位成名的科学家朋友,年轻时为了生活,曾经干过游泳教练的工作。这位朋友说,他当时因找不出为什么自己会游泳的道理而颇觉困窘—无论他在水中怎么动,他总是会浮起来。参见 Michael Polanyi, op. cit., p.49。
[28] Ikujiro Nonaka and Hirotaka Takeuchi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pp.63 -64以及pp.96 – 113, 有一则关于日本松下(Matsushita)电气公司1984 -1987年间开发家用自动烤面包机(Home Bakery)的故事,其过程和今人尝试复制史特拉底瓦里琴相似,只是结局比较幸运,因为Home Bakery所欲模拟的技巧当时并未失传。开发Home Bakery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大师傅搓揉面糊的过程机械化。起初,松下电气的开发人员利用X光照射大师傅和机器搓揉出来的面糊,尝试比较其异同,却得不出任何要领。后来,开发人员亲自跟随大师傅从头开始学习搓揉面糊,终于发现大师傅搓揉面糊不仅有拉扯的动作(stretching),还有大师傅自己也从来不知道说的,当然自己也从来没察觉到的扭捻的动作(twisting),而后者正是决定烤出来的面包是否可口的关键因素。
[29] 以上两段文字主要参考Michael Polanyi, op cit., pp.31 and 49-50。
[30] 参见Michael Polanyi, op cit., pp. 53-54。
[31] 或者说,实际生产过程中所需的知识要不是已经物化存在于硬件的自动机械装置里,就是存在于软件的装配线管理当中。
[32]参见 Ikujiro Nonaka and Hirotaka Takeuchi, op.cit., p. 35-36。
[33] Mitsuhiro Kagami (1998)指出,日本金属加工产业的竞争力,多半来自于强调基本手工技巧的训练与经验的传承,而不是来自于先进的NC车床投资。相对的,亚洲开发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发展精密的金属加工产业,则是因为欠缺传统金属加工技巧。参见 ‘New Strategies for Asia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roblems Facin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Backward Linkage’, in M. Kagami and J. Humphrey (1998, eds.), Learning,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Adjustment,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okyo, Japan。
[34] Michael Polanyi, op. cit .,以及 Karl R. Popper(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对这个所谓客观的科学概念有精辟的批判。
[35] Friedrich A. Hayek, op. cit. 对于这种被称为笛卡儿理性的概念(Cartesian Rationality)有精辟的批判。
[36] 关于有组织的复杂现像,请参阅F. A. Hayek(1974), ‘Nobel Memorial Lecture: 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 collected in F. A. Hayek(1978),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37] 参见Michael Polanyi, op. cit., p.177。
[38] Ikujiro Nonaka and Hirotaka Takeuchi, op. cit., p.10。
[39] Alfred N. Whitehead(1925),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96。
[40] Alfred N. Whitehead, op. cit., pp. 96 – 97没有清楚交代,他所谓发明的方法是否为一个“可以完全标明的”例行规则(a completely specified routine),尽管他似乎承认,照此规则作为所得到的技术创新效果,在数量上不是确定的(quantitatively indefinite)。在别的地方,A. N. Whitehead(1929), Adventures of Ideas, pp. 87 – 109, 他似乎影射多数东方文明之所以未能持续发展科技知识,一个主要因素是其统治精英未能以相互劝服(persuasion)(或谓“以理相向”)取代暴力(force)统治的传统行为倾向(或谓“以力相向”);比较粗俗明白的说,就是其统治精英奉“官大学问大”为至理,从而不讲求多数人可以接受且恒常的道理。他说,“享受权力对许多不可捉摸的生命性质,产生致命的摧毁作用。统治阶级因此而懒洋洋,纵容自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人生乐趣,以致于堕落沉沦。”(‘The enjoyment of power is fatal to the subtleties of life. Ruling classes degenerate by reason of their lazy indulgence in obvious gratifications’ in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 106)。读者应该能理解,商业买卖之精神在于相互劝服。因此,尊重商业自由是现代科技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又,相对于“显而易见的人生乐趣”,例如,口腹与狎妓而言,致力于现代科技发现与创新显然需要一股“傻劲”,因其预期的满足可能非常遥远、不可测也。(请参阅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p. 96 – 97。)就同一意义而言,当我们说日本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很有“敬业”精神时,我们说的正是他们的“傻劲”。
[41] Michael Polanyi, op. cit., p. 53。
[42] Richard R. Nelson and Nathan Rosenberg(1993),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Systems’, in Richard N. Nelson (1993, 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4。
[43] Leonard H. Lynn, ‘Technology Transfer to Japan: What We Know, What We Need to Know, and What We Know That May Not be So’ in Nathan Rosenberg and Claudio Frischtak (1985, ed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Concepts, Measures, and Comparisons, pp. 270 – 1.
[44] Keith Pavitt(1985), ‘Technology Transfer among The Industrially Advanced Countries: An Overview’, in Rosenberg and Frischtak, op. cit.
[45] Richard R. Nelson(1990), ‘On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Their Acquisition’ in Robert E. Evans and Gustav Ranis(1990, e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sso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46] Keith Pavitt, ibid., p.4。在机械论者(即单向因果论)的眼里,此一命题涉及循环论证(circular reasoning),因此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从现代所谓复杂理论的观点来看,此一表面看似循环论证的命题只是隐含,吸收外来技术(或技术创新)除了涉及行为人个人主观的价值之外,还涉及逻辑跳跃。由于存在此一关键因素,吸收外来技术(或技术创新)的现象不能以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来解释。前文提到“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文献令人失望,我们可以断言,之所以如此,厥为大多数学者囿于机械论使然。关于复杂理论,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读者,可以从F. A. Hayek(1988), op. cit., Appendix B下手。关于逻辑跳跃,则可以参考Michael Polanyi(1958)有关heuristics的章节。
[47] 《工商时报》,1998年5月6日记者张世忠报导。
[48] 参见Nathan Rosenberg(199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for the Asian NICs: Lessons from Economic History’, in Robert E. Evans and Gustav Ranis(1990, eds.), op. cit.
[49] Christopher Freeman(1988), ‘Japan: a New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Giovanni Dosi and et. al.(1988, eds.),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50] Richard R. Nelson and Nathan Rosenberg(1993), op. cit., p. 20。
[51] 例如,Peter Hall and Stefan Markowski (1994), “On the Normality and Abnormality of Offsets Obligations” , in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1994, Vol.5, pp. 173-188;特别提醒狃于教科书之交易概念的经济学者,不应该依先入为主的概念将补偿性交易视为“不正常”的交易。
[52] Stephen Martin(1996), “Countertrade and Offsets : An Overview of the Theory and Evidence” , Stephen Martin(1996,ed) in The Economics of Offsets, p.41.
[53] 孙克难(1997),〈政府采购政策与产业发展〉,中华经济研究院,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研究报告《我国迈向先进国家的产业政策之研究-总结报告》, p.297。
[54] Stephen Martin(1996), op. cit., p.3。
[55] ibid., p.32。
[56] ibid., p.2。
[57] Stephan Markowski and Peter Hall (1996), “The Defence Offsets Policy in Australia” in Stephen Martin (1996, ed.), op. cit., pp. 49-74, esp. p.67.
[58] 引自孙克难(1997), op. cit., p.303.
[59] 孙克难(1997), op. cit., p.311, 指出台北捷运局未能从外商习得一些核心技术,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技术“外显程度”很低。技术“外显程度低”,指的正是此处所谓“未标明的知识”。
[60] Stephen Martin (1996), op. cit., p.408-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