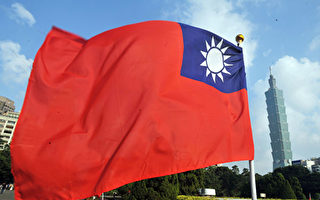【大纪元7月5日讯】语言本是交流与沟通,是如中文“人”的字型结构一般表达相互性,“经”与“传”的传播凭靠的就是语言,源远流长,人之理在这源流里蔓延,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乃至各方各面都在此得以建构。而当人类进入现代意识间,自海德格尔以下,语言更是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因了语言而“在”。但是倘若语言面对当下已不具有了扬善之功,而只有呈恶之能,怎么办?
进一步说是,当语言所欲表达的已 不在是思辨和善意,甚至语词本身丧失了中性立场,而且表达主体沦为了如“国家机器”般的操作,语言已是不可言说;不可言说之语言就丧失了“在”之可能。我这里所指是不在乎语言是本国还是他国,是中文还是英文、抑或法文、德文,这里欲呈明的对立性是“恶”与“善”。欲求的是人之相“持”还是“人”之毁灭。
浅显的例子,有人已指出“技术”本是中性的,任何科研的发明和仪器的制造本身意愿是要造福人类,而倘若这样的发明如军事武器一般沦落到魔鬼的手上,毁灭方才有发生的可能。记得还是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一位朋友的孩子对自己的小学老师放下教鞭走向战场激动不已的表达:老师从此以后有枪了,像我的水枪,砰,朋友倒下,哈哈大笑,我再将你扶起。小孩的意识里没有血的概念,没有真正枪杀的语汇,有的是嬉戏;小孩以嬉戏来表达真实的血流成河的战争。而成人往往在巨大的灾难前丧失了表达的可能,常称其状态为“无言”。
小孩的可以言说与成人的无言叹息形成对比,迫使进入知识的思考。倘若小孩因了对战争的无知而拥有了语言,而成人却因了知识的掌握丧失了语言,那么什么是知识?在休谟的《人性论》里,知识是人对真理的参与和共有。这样的人之主体行为在现实中是否有发生的可能?学过外文的人都知一句常用语是“Repeat after me! ”“跟我说”是学习语言的一种途径,可这种鹦鹉学舌本身不具有“对真理的参与和共有”可能性,也就是说人在学习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存在丧失言说本真的可能。海德格尔在强调语言之在时是强调个体在语言中的行为,可是今日的现实,语言还有无可能发生在个体的行为中?
我是在阅读了皮埃尔.布迪厄《国家精英》英译本前言后产生一种深深的忧郁,因为布迪厄在分析国家权力时,将其看成为“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其挟制符号的运用和传播,在如此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黑暗里,国家机制下的平民个体有无可能存留一丝丝自尊的可能?甚至提出言说自尊几乎是奢侈。布氏使用的概念是“国家魔术”,其分析:“国家暴力,并不仅仅(甚至主要)施加在士兵、疯子、病人和罪犯身上,每每在我们用学校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来认识并建设社会时,它也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降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国家不仅‘在那儿’,在那些官僚机构、权威和仪式中,它也‘在这儿’,深刻地烙在我们身上,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所共享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中,不是军队、庇护所、医院,也不是监狱,而是学校,成了国家的最潜在的线管和仆人。”而在此我要问的是:个体倘若除了“温顺地屈服于一个连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枷锁”之外,还有无他路可行?
悲哀的是,唯有可能是沉默与无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知”的内在性和确然性意味着“自己同自己相处的这种最深奥的孤独,在其中一切外在的东西和限制都消失了,它彻头彻尾地隐遁在自身之中”。似乎要强调的是客观对于主体的重要,但是倘若现实当下那个本来属于客观的无形而膨大的权力技术操作已完全剥夺了人主体仅有的存在和尊严时,普遍性已成为权力之“恶” 的伪装且可优先与独霸万方时,选择遁入内心,让善之知只有在沉默中畅言,岂不是被戕害之主体寻求尊严的唯一可能。
在这样的思考过程里,偶然观看了一个60年代的影片《隐私》,故事叙述一个出色女演员突然不会说话了,而且同时终止交往行为。在治疗过程中与一护士单独相处,影片描写两个女人本是医治与被医治、看护与被看护的关系;但由于病人本身的沉默,而导致护士不断地言说。在医院机制下,医生与护士的言说是代表权力的,所以无须你听与不听,更无须回应;因为权力的言说目的仅指向“服从”而不是“沟通”。可是,当两个女人相处,护士渐渐在自然及人情的关系里,渐渐淡化了权力本身。这个情节很好地帮助了我理解(俄)别尔嘉耶夫的《当代世界的精神状态》一文,医院作为组织形态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采取的是一种监控状态,而自然、大地、海边、花园恢复的是人生存的有机形态,所以影片采取许多海景、蘑菇、石头等空镜头来表达权力者与管制者起初走向的融合。于是,护士将本来身份为病人者当成了倾听对象,开始叙述其从未言说过的隐私。当言说触及隐私时,语言已从组织形态走向了个体形态,而在海德格尔对语言的分析里,就有“倾听”与“呼唤”的相对结构,于是护士开始呼唤这个拒绝说话的病人言说,请求哪怕只说一分钟、哪怕只说一个词。在影片呈现拒绝言说与语言疯狂的结构里,失语患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回驳上面所言老黑对“主体完全走向内向而导致绝对随意”的担忧;其实失语者始终在以理智克制性承受护士的语言暴力。而护士在诉求遭遇回绝后,直接将两人关系摧毁破裂,重新恢复监视与被监视的权力关系。而在权力关系下的结果指向只有两种,影片以复调形式呈现:一是回到医院空间,在权力的胁迫下,个体丧失了所有生存能力,终于实现了权力要求的“Repeat after me!”而另一种就是、也是所有权力不能实现其征服所愿几乎雷同的结果即“谋害”。影片没有很清楚呈现为什么这个出色以表演语言为生的演员要跌进失语状态,而是以护士的性与堕胎来隐喻表达,似乎剧作者与导演力求探讨的是二女人的女性质数的重合与分离,即朋友与敌人的交互关系;但我更愿意理解的是权力、权力监控以及权力失控疯狂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呈现里是超越性别的。也就是说在权力不能如意实现其意图时很容易走向失控性灾难,这在历史上有许多明证;而更加造成当下恐惧现状的发生还在于,权力的正面与背面的交叉,当隐私在不觉中被触及时很有可能导致恐怖发生。因此我更注重影片的其他细节,当护士给病人孩子的照片时,在医院里,这个母亲撕毁了;可是在其书中却夹着一张估计是二战时期,大兵举枪胁迫一个幼小孩童的照片,这个撕毁自己孩子照片的女人不时看着那个在冰冷铁枪的压迫下举起双手投降的孩子,是怜悯是惊恐?还是那幼小孩童在杀伤性武器下的颤栗导致了一个母亲拒绝自己的孩子?战争残酷中的孩子不是我前面提到美国朋友玩水枪的孩子。影片还有一个细节是失语者在医院电视里看到一个斗争冲突中的自焚画面,她情不自禁地用手掩住嘴,这个动作常常发生在人惊恐下怕发生时。那么对于一个本身失语的患者,其摀住嘴的动作担心什么呢?
回到文章起意,失语在于善在恶的现实下被遮蔽、隐遁,而走向内在自身。这是在权力的技术运作里人之个体可以寻求“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的唯一途径?以拒绝来追求安宁与充实?我不知这是不是就是答案,但却仍欲追问:在无孔不入的权力胁迫下,平民能有何作为?当我书写这些文字时,该感恩的是女性写作历史所呈现的意志给予的鼓励,让绝望的色彩不是那样灰暗;一如苏珊.古芭在读解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的受难者所言:“妇女在人生中体验文化文本的方式是任文字刻在自己的身上”。毕竟我们曾有过如奥维德《变形记》中的烈女先辈,在遭强暴践踏、甚至被割去舌头的艰难下,仍顽强地用紫褐色血液织就进雪白的绢丝,来向世间呈明自己受难的事实真相。就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林昭的血书。而我更希望的是,在面对黑沉沉的权魔笼罩下,可以有文字将被权力伤害的体验、还有自己本拥有的美好与期待深深刻进灵魂,毕竟在那最后的一天,每一个人可以携带的、面呈天国的不是肉体而是魂灵!
2005-7-2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