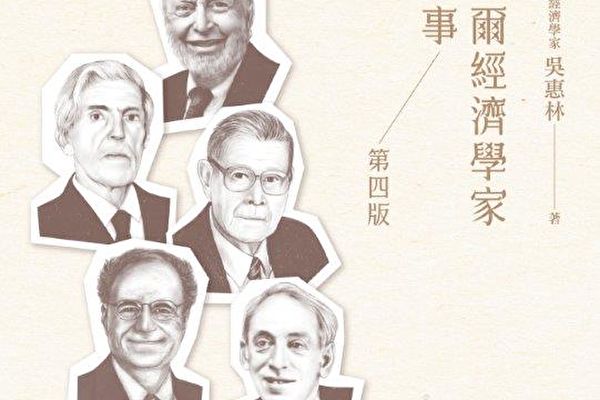【大紀元2020年03月13日訊】對於臺灣民眾來說,十月曾經是「光輝燦爛」的,因為節日慶典特別多,充塞著喜氣洋洋的氣氛。對於全球人民而言,十月的共同盼望則是耀眼奪目的「諾貝爾獎」得主揭曉,這是自一九o一年以來就有的慣例,而諾貝爾獎則是依據阿佛烈.諾貝爾(Alfred Nobel, 1833-1896)的遺囑設定的獎項,由於金額龐大以及評審過程的嚴謹,此桂冠一直是最被世人看重、最崇高的榮譽。
諾貝爾獎的由來
諾貝爾為何要出資設立此獎?據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鉅著《石油世紀》(The Prize)中記載,諾貝爾家族是石油大亨,發明火藥的阿佛烈.諾貝爾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在化學和財務上都天賦異稟,利用硝化甘油在十九世紀建立了一個從巴黎操控全局的火藥帝國,沒想到卻被野心家用作殺人利器,而且火藥也使戰爭更為殘酷,死傷者更眾,因而發明火藥的諾貝爾備受譴責。
就在一八八八年,阿佛烈的二哥路德威(Ludwig Nobel, 1831-1888)在法國度假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有些歐洲報紙把諾貝爾兄弟搞混,誤將路德威當成阿佛烈,於是阿佛烈讀到自己的訃聞,也發現報紙把他稱作「火藥大王」,蓋棺論定他是憑發現新殺人方法以致富的「死亡販子」(或謂劊子手)。阿佛烈目睹此景頗感悲痛,也因而慚愧、省思,於改寫遺囑,捐贈一大筆款項成立「諾貝爾獎」。
依諾貝爾遺囑所設立的獎項,原先只有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等五種,諾貝爾希望獎勵的是特殊「成就」,並非傑出的個人。因此,在自然科學方面,諾貝爾獎是針對重大「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給獎。
經濟學獎的出現
經由簡單的敘述之後,我們已經知道諾貝爾獎的設立,是諾貝爾為了贖其發明火藥,以致成為可怕的殺人利器之罪而撥款成立,但獲頒諾貝爾獎者無疑被世人極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羨慕稀鬆平常,而歷年來的得獎者也大都認為得獎是其一生至高榮譽。既然諾貝爾的遺囑裡只設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現今每年頒發的經濟學獎當然是後人新設的。
原來它是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三百周年,在一九六八年出資創設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簡稱「諾貝爾經濟學獎」,於一九六九年開始頒發。此一新設的獎項,基本上給獎標準是比照原先的五種。依瑞典中央銀行的規定,該獎項每年頒發一位在經濟學上有傑出貢獻,且其重要性一如諾貝爾在遺囑中所言的人士。不過,有許多次,當年的得獎者不只一位,而儘管諾貝爾原先希望獎勵特殊的成就,而不是傑出的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成就是附著在人身上,終究似乎反客為主,世人反而較在乎得獎人。
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本人所設立,但其被世人重視的程度一如原始的五種獎項,尤其在經濟學界更被視為最高榮譽。可是自該獎誕生以來,「異聲」似乎未曾間斷,最大的反對聲浪是認為,經濟學獎不應與其他獎項一起頒發,因其非諾貝爾本意,意義顯然不同。這種反對意見並無實質內涵,只具「形式」意義而已。比較有力的反對意見,乃認為經濟學並非「科學」,連經濟學界都有人這麼主張。有趣的是,這種主張最具代表的人物卻是一九七四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瑞典的左派經濟學家繆爾達(Gunnar Myrdal, 1898-1987)。
繆爾達在接受了諾貝爾獎之後,愈想愈不妥,於是撰寫一系列的文章譴責此一獎項,也對自己曾經受獎表示遺憾(只不知他是否將高額獎金退還給主辦單位)。他表示,經濟學並不是一門和物理學、化學或醫學有著相同意義的科學。關於這一點,相信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同意的,其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一九七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 A.Samuelson, 1915-2009)稱為經濟學界鰻魚的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的反駁最具代表性。
經濟學是否為科學
弗利曼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應美國德州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講述其走上經濟學術的心路歷程,在表明其懷疑「諾貝爾獎是否有什麼正面效果」時,特別就繆爾達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攻擊提出駁斥。弗利曼說經濟學家既是社會的一員,也是科學家,他們並沒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純科學工作上,但物理學家或化學家也是一樣。
基本上,經濟學所具有的科學成分,和物理學、化學或其他自然科學的科學成分,在性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雖然物理學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實驗室操作,而經濟學家則不能,但是光憑這一點,仍不足以否認經濟學的科學性。舉例來說,大氣科學是一門公認的科學,但幾乎是不可能進行控制的實驗,在許多其他的科學領域也都有類似的限制。經濟學家固然不太可能執行控制的實驗(然而仍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經在做了),但是未控制的經驗,經常會產生近似控制實驗的資料。
弗利曼舉統一前的東、西德為例,比較不同的經濟制度,指出其係控制實驗的優良例子。這兩個國家以前是同一個國家,人民背景、文化、遺傳基因皆相同,但卻因為意外的戰爭而分裂為兩部分。在柏林圍牆的一邊,是相對自由的經濟體制,而另一邊則是集體主義的社會。類似這樣的控制實驗,也見諸於共產中國與臺灣,或回歸前的香港,以及南、北韓之間的對照。
弗利曼進一步認為,所謂的控制實驗,也並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兩種不同的狀況之間,可能存在著無數的差異,想要將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相信在所謂的控制實驗與未控制實驗之間,原理上存有任何差異;同樣地,不論是在物理學或經濟學的領域,進行科學工作的可能性,也應該是不分軒輊的。我們有必要清楚區分一個人在科學研究領域所做的事,和他身為一個公民所做的事。這樣的觀念,在物理領域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經濟學。
弗利曼再以星戰計畫這個熱門的爭辯議題為例,指出有些物理學家聲明反對星戰計畫,但卻有另一批物理學家支持這項計畫。很明顯地,這些不同的聲明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已獲大家認同的科學知識,絕大部分反而是這些物理學家的個人價值觀,以及對政治事件的判斷等等。要評量他們在科學上的能力或貢獻,憑藉的不該是這些聲明,而應該是他們在科學上的工作。弗利曼強調,這種做法也適用於經濟學。
其實,弗利曼認定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科學」,早在一九七四年左右,一篇〈芝加哥學派〉文章已強調,而且將之列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第一種特色。弗利曼說,經濟學作為一種實證科學,是經由應用、檢定、改進這三個過程,不斷地循環而成,是典型的實證科學。弗利曼之所以強調這一個特點,尚有兩個重要理由:一是此係芝加哥學派與奧國學派的重大差別所在;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經濟學能夠成為實證科學,乃使其在社會科學中享有后冠,也才使經濟學在一九六九年開始,被列為諾貝爾獎的頒授對象,因為唯有能夠實證,才可拿出證據來贊同或反對某些政策,也才使經濟學與現實生活有著密切關係。
講到這裡,我的腦海裡自然地浮現芝加哥學派的另一位二十世紀重要人物,他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去世的史蒂格勒(G. J. Stigler, 1911-1991)教授,他也是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推手
如果說經濟學家被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所青睞,緣於經濟學是門實證科學的話,那麼,史蒂格勒教授在一九六四年第七十七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的會長演說詞──〈經濟學家和國家〉(The Economist and the State)就貢獻非凡了。
該篇演說對於經濟學家未能就政府的公共政策做有用的實證研究,極表不滿和不解。當時,史蒂格勒說:「兩百多年來,國家的經濟角色一直受到學者的注意,但卻未引起他們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決心。我相信,在歐陸和英美的文獻中,終年不斷的辯論總脫離不了抽象的談論範圍。經濟學家既不想棄問題於不顧,也不想真正加以探究。」接著,他提出數個疑問:「為什麼坊間有關如何評估資產的文獻汗牛充棟,卻沒人就管制團體對價格和費率的影響做出評估?為什麼指責侵犯個人自由的言論聲浪震天,卻沒人積極探討各項福利措施對所得分配之影響?為什麼我們一直甘於讓政策問題留白?」在提出這些疑問之後,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要求:「我們需要一套有關政府行動的正式理論,或是一系列關於政府和私人控制經濟活動之比較利益的實證研究。」
史蒂格勒特別重視政府的公共政策,乃因公共政策的影響層面最深、最廣,而想要政府能夠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證據顯示公共政策的影響效果,在「拿出證據」之後才能大聲說話,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權、利益團體的左右。因此,實證研究顯得特別重要,而在當時,許多數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經出現,史蒂格勒興奮地比喻說:「數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炮代替了傳統的弓箭。」他更進一步地指稱:「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所謂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傑逢斯(W. S. Jevons, 1833-1882)或凱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理論革命,比起勢力愈來愈強大的數量化牽連之廣,只能算是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黃金時代的門檻,不!我們已經一腳踏進門內了。」由於有此體認,史蒂格勒在該演說的末了說:「我對於我們這一門學問的光明遠景感到無限欣慰。……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學,證明我們的數量研究,無論在影響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嘗試的勇氣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日漸擴展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將無可避免地、無可抗拒地進入公共政策的領域,並且,我們將發展出一套制定明智政策所不可或缺的知識體系。之後,我相當確信,我們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和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其實,在史蒂格勒此篇大力呼籲重視實證工作的重要著作之前,他便已經以身作則率先從事有關〈電力管制和證券市場管制〉的先鋒式實證研究,也由於親身體驗到「拿出證據來」的重要性,才有感而發地發表該篇大作。事隔五年之後的一九六九年,諾貝爾獎首次頒給經濟學家,而得獎的就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專家」──弗瑞希(R. Frisch, 1895-1973)和丁伯根(J.Tinbergen, 1903-1994)。由這個事實,也可印證實證經濟學是何等被看重了。即使到晚近,年輕一代的芝加哥學派健將、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黑克曼(J.Heckman, 1944-)更是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可能會有所進展」。
實證經濟學是爭論關鍵
因此,儘管芝加哥學派始祖奈特(F. Knight, 1885-1972)不認同將經濟學發展為一門實證科學,弗利曼卻將實證經濟學列為芝加哥學派的第一項特色,並特別強調它,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關於經濟學是不是科學的議題,已故的蔣碩傑(1918-1993)院士在《諾貝爾經濟獎論文集》的序文〈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結晶〉中,也持非常肯定的看法,強調「經濟學究竟是一門歷史較短的科學,而且是非常難得實證的科學。」也提到自然科學家譏評經濟學不科學並不公允,他進一步認為,經濟學是人類智慧的高度結晶,值得最聰明的人去研究它。由蔣先生的字裡行間,依稀嗅出其對諾貝爾獎頒予經濟學以拉拔經濟學家的地位,持高度肯定。
由上文所提,中外諸大師的說詞,已可駁倒繆爾達等認為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調,因而以經濟學非科學,並不夠格加入諾貝爾獎行列的說法不能服人,而且也不是關鍵所在。事實上,正因為經濟學在薩繆爾遜等人的帶動下,不斷引入自然科學的分析法,以及在凱因斯的帶領下,經濟學家成為影響國計民生公共政策的重要參與者,本來就已具相當重要性的經濟學家,再以如此崇高的諾貝爾獎桂冠加在頭上,是否會讓仍為凡人的經濟學家過分膨脹,以致提出錯誤的政策而荼害廣大民眾?就這一點應該才是思考諾貝爾經濟學獎價值的關鍵。說也真巧,與繆爾達同時獲得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就曾針對此關鍵點發表振聾發聵的演說。
海耶克的傳世諍言
如上所言,原本是希望獎勵特殊成就的諾貝爾獎,已反客為主成為褒揚得獎「人」,因此,對於有幸獲獎者,其身價「暴增」,世人也往往認為他們高人一等,甚至是無所不能,這在經濟學這門社會科學的得獎者身上更是明顯。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容易理解海耶克在諾貝爾獎受獎宴席上會這樣說:
「諾貝爾經濟學獎既已設立,被選為聯合得獎者之一的人,當然會深深感激;經濟學家當然也對瑞典中央銀行如此重視他們的學科,以致授予這項最高榮譽,同樣感激。但是,我必須承認,如果當初被問到是否要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我會斷然反對。第一個理由,我怕這樣的獎會像某些龐大的科學基金活動一樣,勢將助長時髦的學風。這個憂慮,現在由於我這樣一個不合時潮的經濟學者居然被選為得獎人而消失。可是,我的第二個憂慮,仍無法同樣的釋然於懷。
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種權威,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部門,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發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如果一個人的業績落伍了,同行的專家馬上就會輕視他。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
在經濟學方面有了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成為全能者,而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他素未專研的問題表示意見,而認為這是他的社會責任。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學家的成就,使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獎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謙遜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力以外對於公共事務表示意見。
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受獎者謹記住我們經濟學的大師之一──馬夏爾(A.Marshall, 1842-1924)的一句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眾人大捧特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
在這段話中,海耶克的兩點憂慮,一是擔心諾貝爾獎將助長時髦學風;二是經濟學者影響層面甚廣,誰都不應有資格獲得「權威」的標籤,否則由於得獎之後所引發的膨脹,勢將有害於社會。海耶克本人因其在不合時潮時獲獎,故免去了第一點憂慮,但由歷年來得獎者的研究領域來看,卻仍然存在,尤其曾有幾年相繼密集地頒給熱門時髦的財務金融學者,更可證實海耶克的憂慮。當然,我們並非否定該學門的價值,只是質疑諾貝爾獎錦上添花,甚至推波助瀾的必要性。
至於第二點憂慮,一直以來都存在,因為絕大多數的得獎者都只是在各自專業領域內學有專精,較偏於「技術」和「工具」層面的專家,的確令人擔心由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存在,使經濟學脫離「人文」層面愈來愈遠。而且正如上文所提蔣碩傑院士所言,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的結晶,是關係著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科學,但若誤用而導致實施錯誤經濟政策,則遺害將既深且遠,共產世界的慘痛經驗固不必談,就是自由世界裡也例證斑斑,最明顯的是,著重短期而賦予政府龐大「權力」的凱因斯理論。可是,為何迄今該理論仍然甚為風行?主因之一是,太多人早年身受其教,已在腦中根深柢固,縱使有心去除,當事人也已無力,再加上諾貝爾獎對經濟實證科學的肯定,更使對新一代的教育無法還原經濟學本質,甚至陷於如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 Buchanan, 1919-2013)嚴厲批評的「現代經濟學缺乏一個紮紮實實的哲學基礎,因而無法使經濟理論與我們的人生發生適切關聯」。
真正的經濟學家
有趣的是,主張經濟學是實證科學者認為唯有抽離主觀因素,將實證知識資源由臆測中分離出來,才能免於流為空談或政治的偏誤,也才能與實際人生聯結。而持反對經濟學實證科學論點,主張回歸人文精神者也同樣強調經濟學應切合實際人生。為何目標相同,但觀點卻南轅北轍?由已故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1907-1995)先生對經濟學家的分類,可得知梗概。
夏先生依循海耶克的分法加上第三類,而將通常被稱為經濟學家的一群人,就其思想言論的底蘊分成三類:一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二是經濟工程師;三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他說這三種人都同樣在使用經濟學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們發表的文章都討論經濟問題,很自然地把他們統稱為經濟學家,但實則有顯著區別。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顧名思義大多是受僱於某人或某一集團,而為某人或某一集團的經濟利益辯護,或者只為捍衛他自身的利益。
經濟工程師是怎樣的人?工程師而冠以「經濟」二字,我們可想到:他的專業是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他無視於,至少輕視公共經濟事務是千千萬萬的行為人,形形種種的主觀意志表象。個人的主觀意志,畢竟不同於既定的、客觀的存在,而可以規格化的物料。工程師的專業是利用工程學的知識,就這些物料預先做成一個模型(或出於自己的創意或遵照業主的願望),然後按這個模型來建造一座壯觀的廟堂,或一套精密的機器,或一條高速公路。由於所
建造的東西不同,而有建築工程師、機械工程師、土木工程師這些不同的稱謂。稱謂儘管不同,他們同樣地都是利用一些無生命、無意志的物料,製作預先設計好的東西,至於被冠以「經濟」二字的經濟工程師,則是搬弄一些經濟學名詞,而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人的行為所形成之公共經濟事務。
至於真正的經濟學家,起碼應有以下的認知:必須了解其所關心的「人」,與生物學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經濟學家雖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動物的慾望、衝動和本能的反應,但更重要的是,「人」還具有異於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大特徵。人的慾望會自我繁殖不斷增多,而其滿足卻要受到外在種種限制。於是在要求滿足的過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選擇。選擇,是出於不得已;選擇什麼,則又力求自由。這就是說:人,並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爭取自由的本能。
分工合作和諧互動
由於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徵,所以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漸漸學習了爭取個人自由的適當方法。這個方法是要不妨害別人也能爭取,否則終會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會在個別自覺的互動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同於出自本能的蜂蟻社會,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擴大,是由於人的自覺行為之互動。「互動」之「互」字,顯示出主詞的「人」是指多數,而且多到說不出他們是誰;並非少許幾個人,更不是像孟軻所稱為「獨夫」那樣的一個人。其互動也是在其獨特的環境,各憑獨特的零碎知識而行為,而互動,絕不是靠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設計、規劃、指揮,或命令而組織成的所謂「團隊」行為。
那麼,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正是有些人所說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嗎?事實上完全相反。因為團隊行為受制於這個團隊主宰者個人的知識,即令他有所謂「智囊團」的幫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數人。至於分散在社會上無數個人的知識,個別看來是零碎的、瑣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與任何專家系統智識同日而語,但是,那些分散在社會的知識總和,卻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知識所能攝取其萬一。即便在將來更高科技時代的電腦,也不能納入那些知識的總和。所以非團隊行為不僅未造成混亂,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會所賴以達成、擴大的基礎。如果引用亞當.史密斯(A. Smith, 1723-1790)的話,這是「無形之手」的作用;引用海耶克的話,則是「長成的社會秩序」。
重視「無形之手」,並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長成的社會秩序」,並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會秩序」。以「重視」、「尊重」這樣的字眼,是要強調有形之手不應牽制或阻礙「無形之手」的運作,只能為其除去障礙,使其運作順暢無阻;是要強調法制的社會秩序不應干擾或擾亂「長成的社會秩序」,只要提供一個有利於後者,得以保持活力而無僵化之虞的架構。這些論點應用到經濟領域,便是自由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由市場是長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社會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對於市場的運作只可維護或給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擾或阻擾。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分類
在這三種分類下,夏道平先生曾就迄一九八八年二十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評論說,並非全都是真正的經濟學家,甚至就他們的思路來說,有的只可稱為頂尖級經濟工程師,當然這些得主應不至於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
個人認同夏道平先生的說法,也不否認這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是各專業領域的佼佼者,只是覺得諾貝爾獎的性質應該是非常特殊的,在經濟學層面更宜朝「思想」上具原創性貢獻者給獎,也並非每年都非頒發不可,否則會拉低此獎的價值,甚至與其他一般獎項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當可惜了。
話雖如此,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者在其從事的領域上都有突破性的貢獻,至少會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這些得獎者為何會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與他們的家庭、天賦資質、成長環境有所關係?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為者亦若是」?
約在一九八0年代中期,我對此課題就相當感興趣,於是嘗試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進行了解並為文介紹。先在報紙上發表,而後在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經濟前瞻》季刊(現為雙月刊)上,每年十月按時介紹,迄二0一四年退休之前從未間斷。曾有學校老師和上班族朋友建議可以結集出書,二00九年初有機會探詢出版社的意願,出版社催促我加緊腳步,於是上緊發條,將一九六九至八0年中十二屆的得獎者補上,這才發現並不輕鬆。雖然參考資料不少,但摘要濃縮再加上論評的工程浩大,迄年底才大功告成。
其間我曾自問:市面上已有一些介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中文書籍,為何還要再出版這類的書?一來有的過於學術、僵硬;二來有的不完整;三來既有的都缺論評。所以,夾敘夾評、通俗化的本書應還有其價值。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讀者在認識經濟大師之餘,能正確思考經濟學的本質,而且能夠不盲從、信服權威,並試著領略「經濟即生活」。此外,就這數十位名家中,上文所提夏道平先生的三種經濟學家分類,讀者能否將這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歸類、能否指出哪
幾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哪幾位是經濟工程師?而是否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呢?我希望讀者能在讀完本書之後,對這些問題形成個人批判性的看法。
本書最初在二00九年底出版,三年之後,又新增三屆得奬者,再將這三屆得獎者加入本書,於二0一三年三月出了第二版。二○一六年底,出版社通知存書不多,建議再將二0一四~二0一六年三年的獲獎人列入。由於三年來已沒寫了,乃提起精神蒐集資料趕工補齊,也趁機將以往得獎者的資料增補再重新出一版。在二0一七年十月出了第三版。迄今(二0二0年)又過了近三年,又新增三屆得獎者。再把二0一七~二0一九年三年的獲獎者納入成為第四版。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