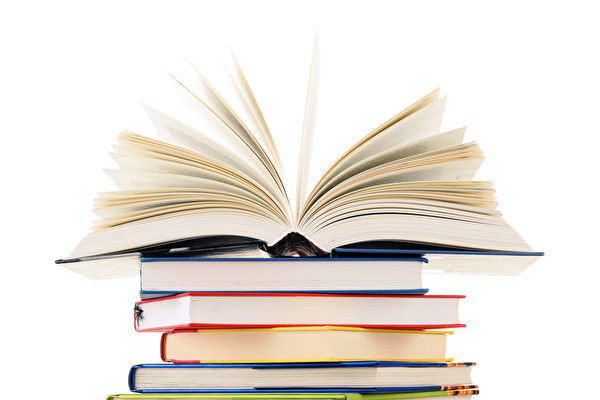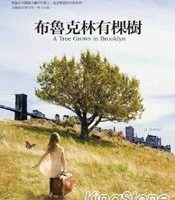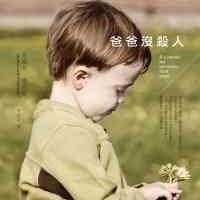【接续前文,书摘:过于喧嚣的孤独(1)】
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和书籍,而我生活在一个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居住在过去曾经是王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习惯,一种执著: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压进自己的头脑,这给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他们为了一包挤压严实的“思想”甘愿献出生命。
现在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来我按动这台机器的红色和绿色电钮,三十五年来我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为了买醉,我憎恶醉鬼,我喝酒是为了活跃思维,使我能更好地深入到一本书的心脏中去,因为我读书既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消磨时光,更不是为了催眠,我,一个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的人,我喝酒是为了让读到的书永远使我难以入眠,使我得了颤抖症,因为我同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高贵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如果我会写作,我要写一本论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书……珍贵的书籍经过我的手在我的压力机中毁灭,我无力阻挡这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巨流。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心肠的屠夫而已……
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把这些东西压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车开来把包运走,送到火车站,由火车运往造纸厂,在那里工人们剪断捆包的铁丝,把我的劳动果实倒入碱和酸的溶液中,其强度足以溶化那些总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脸刀。
然而,正如流经工厂区的浑浊河水中偶尔会有美丽的小鱼闪现一样,在这废纸的长河中,不时也会有珍贵书籍的书脊放出夺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发花,我朝别处望了片刻,然后才迅速把它捞出来,先在围裙上抹抹,翻开书页闻闻它的香味,这才像读荷马预言似的读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之后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里,同我发现的其他珍贵书籍放在一起,小箱子里铺了许多圣像画,是不知什么人连同一些祈祷书误扔进地下室的。
后来,这成了我的弥撒,我的宗教仪式,这些书我不仅每一本都仔细阅读,而且读过之后还在我打的每个包里放进一册,因为每个包我都要给它装饰打扮一番,必须让它带着我的个性,我的花押。
要让每个包都具有特色可是件煞费脑筋的事情,为此我每天在地下室得多干两个小时,提早一个钟点上班,有时连星期六也得赔上,把永远堆积如山的废纸送进机器,打包。
上月,有人送来三千六百公斤绘画大师的复制品,扔进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伦勃朗、哈尔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欧洲其他绘画巨匠的作品,我于是在每个包的四周里上一幅名画的复制品,到了傍晚,当这些包整齐地堆放在升降梯旁边等待运走时,它们身上里着的美丽画幅使我怎么也看不够。瞧!这张《夜巡》,这幅萨斯基亚像,这幅《草地上的早餐》,这张《缢死者之家》,这张《格尔尼卡》。
另外,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还藏着一本名著,这个包里是翻开的《浮士德》,那包里是《唐‧卡洛斯》,这儿里在臭烘烘的纸张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许佩里翁》,那儿,装在旧水泥袋里的是《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
因而,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我知道,哪个包里躺着──犹如躺在坟墓里──歌德、席勒;哪个包里躺着荷尔德林;哪个包里是尼采。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既是艺术家又是观众,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惫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划了口子,累得要休克,为了缓解和减轻一些这巨大的体力消耗,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上胡森斯基酒店打啤酒的时候,一路上我有足够的时间琢磨、幻想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
我灌下那么多的啤酒,为的是更清晰地看到前景,因为我在每一个包里藏了一件珍贵的遗物,一口没有盖的儿童小棺材,撒满了枯萎的花朵、碎锡纸角、天使的头发,我给书籍铺了一张舒适的小床,它们像我一样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间地下室。
因此,我干活老是完不成任务,院子里的废纸堆得山一般高,都顶到天棚了,从洞口倒进我地下室的废纸也堆积如山,同院子里的那座山连接了起来。因此主任有时用铁钩扒开洞口,脸气得通红朝我叫嚷:
汉嘉,你在哪儿?◇#(节录完)
************
【作者简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
捷克作家,生于一九一四年,卒于一九九七年。被米兰·昆德拉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四十九岁才出第一本小说,拥有法学博士的学位。先后从事过仓库管理员、铁路工人、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站打包工等十多种不同的工作。多种工作经验为他的小说创作累积了丰富的素材。他的小说充满了浓厚的土味,被认为是最有捷克味的捷克作家。
——节录自《过于喧嚣的孤独》/大块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杨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