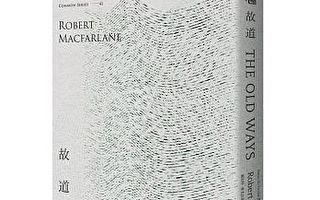十一月,紅十字會接手了審查和分派牧師到世貿災變現場服務的工作。所有感興趣的各教派神職人員,只要有意願繼續擔任志工的,都受邀聚集在紐約聖公會主教區辦公室。紅十字會規畫了好幾個工作區域,讓牧師們選擇自己感受召喚想前往服務的地點——家屬中心、聖保羅教堂、萬豪飯店、永久或臨時停屍間。
我心中毫不懷疑自己屬於哪裡。我見過的死者遺體比大部分人都來得多,我自忖,舉手表示想到災變現場停屍間服務。我萬萬沒想到,我即將祝福的都是些殘骸,而不是遺體。
從我第一次輪值開始,大型黑色屍袋幾乎都已改成了小型紅色塑膠袋,有時只裝了一顆牙齒或者一片人體組織。燃燒了一百天的瓦礫堆已逐漸變成一個越來越乾淨的坑穴,地獄之火的鼓吹者已被清乾淨,期盼轉換成了決心。
災變現場四周,商店櫥窗閃爍著節慶彩燈,提醒我們生活仍然照舊,即使被死亡浸透。黑暗寒凍的夜晚為那個美得令人心痛的九月天——以及在那之後像把匕首將我穿透的每一個碧藍天空——提供了慰藉。因此我歡迎雪白冬日的到來。感覺就好像天空排空了它的顏色,以便幫助我們重新來過。
我邊走邊縮緊下巴抵抗風寒。
「寒冷可以讓遺體保存得久一點。」我心想。
這陣子我滿腦子就只想著這些。所有一切都和災變現場、遺體、在這裡工作的男男女女脫不了關係。我看了人行道上匆匆來去的一家人不止一眼,心痛地想起我自己的孩子。一小時前我才和他們親吻道晚安,這時卻感覺他們彷彿在另一個世界。
「妳非去不可嗎,媽咪?」
我的八歲女兒在溫暖的被褥中問。我那六歲的兒子已經睡著了。
「每次妳出去我都好擔心,而且聖誕假期還沒過,萬一妳出事怎麼辦?」
她的眼睛打量著我的臉,露出一種認知到生命無常的早熟表情。
「我到底在做什麼?我到底想證明什麼?」
我常這麼問自己——直到我走進災變現場。這時我的矛盾和自責消失了。我無法想像自己是唯一有這感覺的人。
我女兒不可思議地把死亡看得很平常,不單是因為九一一,也因為在我們家這話題常被拿出來討論。從小在一個擔任安寧病房牧師的母親身邊成長,她參加過的守靈、見過的遺體,或許比我認識的任何成人都還要多。
然而她也了解,那些死亡大都是疾病造成的,通常是長期罹病而且以老人居多。她能夠走向陌生人的棺木,將她的小腦袋放在亡者胸前,用小天使般的美好信念說:
「沒事了,你和天使在一起了。」
她說這話時,聽起來莫名地真實。
如今她了解,死亡隨時都會降臨。可能發生在雙親出門上班,或者搭飛機旅行的時候。很可能來得毫無道理。
「答應我一定要回來。」
她雙手摟住我的脖子說。我也很掙扎。身為母親的我為了必須離開而為難、內疚,然而身為牧師的我卻迫切地想要上路。離開家門有時感覺就像撕下一片繃帶——道別拖得越久,心就越痛。
孩子們會沒事的,我告訴自己。他們會沒事的。這是事實,差不多和一首為我抒解離開他們的愧疚感的頌歌一樣真實。我試著不斷複誦它來讓自己相信。我丈夫在家陪他們,萬一他們半夜醒來,他可以安慰他們。我離開時沒有多回想他的模樣。他也一樣,只問我是不是又要到市中心去。我看不出他是否為我擔心、感覺被遺棄,或者和我的世貿災變現場生涯漸行漸遠。
我看到了一些我不知道該如何跟他分享的東西,一些我感覺他並不希望我拿出來分享的東西,漸漸地我也變得越來越退縮。一部分的我迫切想要擁有他的同理心和支持,能有機會述說我的種種經歷,然而另一部分的我也害怕,一旦說出口會被他不情願聆聽的態度所傷。
還有另一部分——或許我們兩個都有——則是,拒絕面對我在世貿災變現場的工作將會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為自己、為我們的關係,以及為孩子們。
我已經相當熟練,一到達災變現場就把這些念頭打包,裝進一只乾淨漂亮的箱子。我的孩子、我的婚姻、我在停屍間以外的生活,可以等以後再說。
也許我在哄騙自己:驅使我一次次到這兒來輪值的是服事神的心,而不是某種特殊的私心。也許兩者兼有吧!我只知道,接下來八小時我將實實在在活著,我將超越自己作為妻子、母親的角色,更趨近於一種讓人能回想起上帝的憐憫和存在的東西(儘管相當微弱)。
我將寒冷的空氣吸入肺裡,讓安檢站的警官掃描我的識別證然後放我通過。身穿迷彩軍裝的年輕士兵在災變現場邊界內站崗,不時將重心從冰凍的一隻腳轉移到另一腳。
我無法想像在這樣的大冷天裡站得筆直,就算穿著沉重的靴子也一樣。我總不忘向他們致謝,並且鼓勵他們在休息時間多利用聖保羅教堂提供的休憩設施。除了供應食物、熱咖啡和溫暖的休息空間,教堂也有按摩治療師、脊椎指壓師、浴室,還有寧靜。
他們總是微笑、禮貌點頭以對,男人外表下的男孩稚氣有如底層的閃電隱約可見,突然迸現,馬上又消失。
當我繼續往停屍間走,一股新伐木材的香氣讓我放慢腳步、昂起頭來。我深吸著,就像聞到蘋果派時本能地感到幸福。朝香味的來源轉身,我看見為公眾設置的一段通往觀察臺的長長斜坡已經搭建完成,預定三天後開放使用。這也是災變現場籌備中的四座觀察臺的第一座,以便讓一般市民能夠更清楚、沒有阻礙地觀看這場公共悲劇。
除了來看災變現場,他們同時也是見證者,能夠親睹這兒進行中的各種工作,以及整個城市展現尋找遺體、收復這塊土地的剛毅決心。我了解觀察臺的設置引起不少爭議。有些人表示擔心世貿災變現場將會變成觀光景點,但事實上,它已經是了。
這並不表示訪客都是抱著窺探或不敬的意圖而來,他們就只是很想看看。這跟想要參加守靈的衝動不同,不管是出於對遺屬的敬意,或者是為了相信死亡的真實性而必須去看看死者。
如果我沒有在這裡服務,我也會很想來的。我會被這個充滿傷痛的地方吸引,想要來表達敬意並且禱告。
我繼續往前走,離開空蕩的觀察臺——到了週日肯定會擠滿人群——到達充作停屍間的簡樸活動拖車。這裡絕不會開放訪客進入的。這裡是災變現場的聖器室。
在這個長方形房間的盡頭擺著兩張不鏽鋼接收桌。和我們一樣,它們耐心等候著下一批殘骸被送進來。幾名救護技術員坐在折疊椅上輕聲談話,一位看來相當年輕的紐約港務警局的官員倚在牆邊,一個坐在小桌子後方的警探伸展著筋骨。
我走進去時,他們全抬起頭來,揮手招呼或喃喃說聲哈囉。一本巨大的冊子攤在桌上,一頁接一頁登錄著無數生命的遺失部位:一隻腳、一隻手臂、一個乳房、一根骨頭,包括部位名稱、時間日期和地點。輪值的人換了,字跡也跟著改變。
很顯然地,被起出的殘骸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小。這讓我想到,這本詳列著尋獲殘骸的冊子已成為記錄九一一災後慘況的斷腸資料庫。
有好一會兒,我站在那裡瀏覽它的內頁。整齊的條目無止無盡地延伸下去。我強烈意識到我無法為這些七零八落的生靈做些什麼,但想到有人來為他們祈福,多少讓我感到寬慰。某個不知名的同事,某個虔誠的人,願意作為天使的化身,為一個生命作證。捧著這本冊子,我知道我同時也捧著我念誦過的禱詞。我正捧著我祝福過的那些遺體——我閉上眼睛片刻,讓呼吸緩和下來。
當我把冊子放回桌上,那名警探打了個哈欠,揉揉疲倦的眼睛。他告訴我這個晚上相當平靜,送來的殘骸非常少,也因此時間過得特別緩慢。起碼我們有個地方可以躲避寒凍。我看了一眼那位港務警局官員,認出他是我曾經在這裡見過的人——魯迪。一個大約二十八歲、長得高大威風的男子。肩膀寬闊,胸膛似乎就要從外套裡迸出來。
除了體格壯碩,魯迪有著親切迎人的臉龐和笑容;不像拖車裡的其他人,他完全沒有疲憊不堪的樣子。那種強烈對比實在驚人。我很好奇會不會是他的年輕或者光滑的橄欖色肌膚遮掩了他的疲態。我有股直覺,他的精力是源自某種更深層的——屬於內在性靈的東西。
第一次在停屍間見到他時,我指著他帽子上的字母,問他是不是賓州來的警官。
「噢,不是。」他大笑著說:「PAPD指的是港口事務警察局。」
我覺得好丟臉。在重建工作的前幾週,我越來越習慣在帽子、夾克上看見各式各樣的字母組合,因為有太多穿制服的人員從全國各地趕來幫忙。最常見的縮寫是FDNY(紐約消防局)和NYPD(紐約市警局),但還有好多其它的單位。
魯迪很有耐心地——而且自豪地——解釋,港務警局的人員是九一一攻擊事件發生後,第一批趕來支援的執法人員。當天他們折損了三十七個人,比任何警局都要來得多。這讓我想到他那厚實的肩上不知扛著多少重擔——哀傷的重擔、存活下去的重擔、追憶的重擔。
「嗨,魯迪。」我朝他走過去,說:「賓州還好吧?」
他暖暖笑著,伸出手來。
「嗨,真高興見到妳,牧師。」
從他的強大手勁,我感覺到他的活力——我不禁又想,我背後那本工作日誌中不知藏有多少正值青春的男女。這念頭沉重得讓人無法承受。我問他最近如何,他在現場投注的大量時間都是怎麼熬過的。我們一起靠在牆邊,不自覺地抵擋著緊壓在牆的另一側的傷痛風暴。
「我忘了上次有沒有告訴妳,」他輕聲說:「有天晚上我在這裡值班,有人說他們認為他們似乎找到了一名劫機者的遺骸。」
這話有如音爆轟一聲襲來。◇(未完,待續)
——節錄自《讓光照亮你的心》/聯經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李昀
點閱【書摘:讓光照亮你的心】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