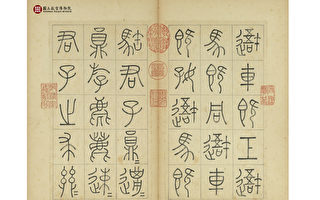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相约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聚会。兰亭四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一幅大自然的美景正合赏玩。于是曲水流觞,吟诗作对,说是为行修褉仪式而聚,其实俨然就是东晋名流雅士舞文弄墨、徜徉山水之间的最佳写照。
俯仰宇宙,品察自然万物,王羲之有感而发,写下《兰亭序》记载了这次集会,也道出人生无常的感悟。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大半部书法史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就在王羲之融情于景加上心书相契的情况下诞生。
《兰亭序》并非问世后就是书法史上的宠儿,甚至直到初唐之前都没有留下关于《兰亭序》的评论和记载。相传《兰亭序》传至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再传到其弟子辨才手中,由于当时皇帝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四处探求,最后终于从辨才手中得到《兰亭序》。
唐太宗得此墨宝后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临摹多张,还命冯承素等人以双钩法拓摹,再以这些摹本让朝臣临习。由于后来刻本众多,唐朝以后的书法名家如“宋四家”苏、黄、米、蔡、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等人都曾在《兰亭序》下过一番功夫。《兰亭序》的好不断为后代书家所发掘,人人临习,人人赞叹,《兰亭序》也就成为行书的代表作。时至今日,提及学行书,《兰亭序》依然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首选。
许多书法名作在不同朝代受到的评价都有所不同,或褒或贬,审美角度互异,品评内容自然不一。而能像《兰亭序》一样,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观念里都被奉为“神品”的情形,可谓少之又少。《兰亭序》通篇灵动活泼、畅快淋漓,但每一使转、提按,每一笔牵带,或连或断,都交待地清清楚楚,丝毫不失法度。变化多端的用笔化入结构章法,呈现出丰富多样的体态与疏密合宜的空间,“大小、长短、匾狭,均各还其态,率其自然”。妍美中带有遒劲,飘逸中又显圆融平和,令人“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兰亭序》的美确实是爱好书法的人所难以抗拒,“天下第一行书”的赞誉千年来不曾稍损。然而中国艺术向来重视心灵世界的探索,强调作品精神层面的意涵。从这个角度来看,《兰亭序》叹为观止的书艺就不只是精湛的技巧所能完全概括。放诸天地之间、悠游山川的旷达,率真自然、天人合一的晋人风韵,这是《兰亭序》所投射出来的独特的生命情调,是她之所以迷人的重要质素,也是吸引我们与之对话的关键所在。@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