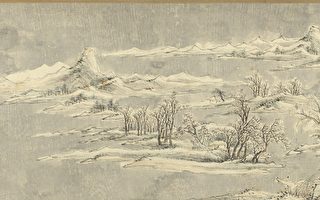清朝時,有一松江府華亭縣人叫汪瑾,年紀五十多歲了,窮愁潦倒,客居在京都,布衣不第。他已十分厭倦在外客遊,時當秋風吹起,他動了思念家鄉之情,便乘船南歸。
在等候放閘時,船停泊在武城縣舊縣城西邊。傍晚,汪瑾正感到寂寞冷清,驀然看見一個小僮僕,滿頭大汗地跑來,投上一張名帖給他說:「我家主人馮二官來謁見。」汪瑾看名帖上稱「鄉眷晚生馮勰」,卻素不相識。心想自己既老又貧,至親好友當面走過尚且不相認,哪裡又有硬來認親的人?他懷疑這是認錯了,遲疑不肯領受。僮僕說:「老翁您不是松江府姓汪的嗎?」汪瑾說:「是的。」僮僕說:「那就不錯了!」說著就跑走了。
不一會,馮勰來到,穿著華美的衣服,戴著新帽,年紀大約三十歲。行禮作揖,登上船來,執禮謙讓恭敬,送上四匹潞綢為進見禮,自稱:「我是山西人,將要到揚州去訪一老相識,他在上官橋巡檢司。仁兄要歸松江,我想乘搭你的便船,不知肯接受嗎?」汪瑾看他樸實忠厚,便答應了。馮勰拜謝,僮僕於是把行李搬進了船艙。
晚上兩人敘談起來。汪瑾說:「仁兄是山西人,我是南方人,為何稱『鄉眷』呢?」馮勰說:「我祖籍是松江府的,明亡清興後,改籍為汾陽,名片稱鄉眷,是表示不忘本的意思。」汪瑾說:「為何不仕宦求進,辜負這壯年的大好時光?」馮勰說:「這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可以強求。我為想入仕做官,先後花費了上萬金了,始終沒有成功。起初很憂鬱不快,後來也就不放在心上了。我轉念一想,自己才疏學淺,一無長處,何必無才忝居官位,尸位素餐呢?假如說因貧困而去做官,那麼我本來就是資財殷富之家。不管從哪一方面考慮,都一無足取,所以我甘心為一布衣平民。仁兄您生當盛世而卻不被用,這是命啊,對貧困又有什麼可抱怨的呢?」汪瑾十分佩服馮勰的話,滿肚子牢騷頓時減消。從此以後兩人朝夕相對暢談,相處十分歡洽。
善惡有報通陰陽兩界
一天,船停泊在淮安,正好逢到中秋節,汪瑾打了酒邀馮勰一塊賞月。酣飲之間,馮勰忽然握著酒杯嘆息說:「華亭的鶴叫聲,還能夠再聽到嗎?」汪瑾聽了也不在意,便問:「你的朋友當巡檢,料想官況也一定很清苦。你千里迢迢去訪他,不會徒勞往返空跑一趟吧?」
馮勰沒有回答。好久他才放下杯,悽慘地說:「十多天來,很感念仁兄待我情深意厚,好幾次想要竭誠相告,又恐你聽了害怕,因此隱瞞不說。如今蒙你詢問,實在難以再沉默了。上官橋巡檢姓陳,雖然說是朋友,實際卻是仇人啊。十三年前,我販賣千捆布到蘇州,路上經過荏平,與姓陳的一起住在同一個客棧。正逢下大雨,滯留在客店,姓陳的與同舍客人呼盧賭博了一天一夜,一敗塗地,囊中錢全部輸光,還欠人家一百多兩銀子,無法償還,遭到了同舍客人極大的窘辱。我可憐他,替他如數償還,事情才算了結。我又贈送他二十兩銀子路上用。那時候姓陳的千恩萬謝,說要知恩圖報,哪怕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願的。然後,他又同我商量:『家中尚有老父母,難以守志樂道,要想按官家之例出錢捐買一個小官職,苦的是囊中無錢。恩公仗義疏財,能不能再借給我五百兩銀子,利息任你定。假如有幸能得一官半職,絕不失信,有負恩公。』我正高興他能仁德愛人,便慨然答應了他。當時也怪我太粗心大意,竟沒有立下契券。過了五年,我又重來京城,聽到他已得到揚州的官缺,還沒有領到官憑,寓居在宣武門外。便連忙去拜訪他,下人卻推辭說他外出了,我再三再四去等候,才得一見。相見時,他又對我非常冷淡傲慢。」
汪瑾聽到這裡,不禁怒目切齒,說:「人心險惡難測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嗎?」馮勰說:「倒不是人心險惡難測,而是我們這種人心太老實口太直爽,以君子之心去對待小人,難道沒有聽說過中山狼的故事嗎?」
汪瑾說:「是的,確實如仁兄所說,真是受此輩小人的惡氣也太久了。對這種人,仁兄應當討還欠債,同他絕交算了。」馮勰說:「我也轉念一想,何不就這樣做呢?但是向他問起欠債,他不但不承認,而且反口出惡言。我十分憤怒,同他爭論起來。我所以這樣,倒不是痛惜失了一筆錢,而是痛恨這人太負心了啊!誰料到這姓陳的為人如鬼妖,比蛇蠍還毒,竟買通了管理街坊的小吏,把我送交官司。因為沒有契券作證明,官府不審察,糊亂判案,竟使我暴死他鄉,不得歸葬故土。我在陰間告狀,已准予追償這筆血債,幸得仁兄帶我進揚州,使我得以向那姓陳的發洩我的憤恨,我一定要以厚德答謝仁兄,以後哪敢忘了結草銜環之報呢?」
汪瑾聽了,毛骨悚然說:「那仁兄你是鬼嗎?」馮勰說,「是的,你在燈下月下驗一下就知道了。」汪瑾驗看了一下,果然見馮勰沒有影子,於是非常恐懼。木然坐在席上,面色如死灰。
馮勰安慰他說:「不要怕,我感激仁兄都來不及,哪裡會害仁兄呢?」好久,汪瑾才神色稍定,但還是戰戰兢兢同他相處,如有芒刺在背。等到達揚州,馮勰悵惘地說:「從此同你永別了。不過,我聽說起造寶塔,一定要造到尖頂。我知道仁兄同知府是故交,明天希望你去拜訪他,乘空為我一洗冤屈,不要讓那負心奴才再盜取清白之名來欺騙世人。」說完,再拜告別。
汪瑾也哀痛地送別他,指著小僮僕問:「這個小僮僕是人呢,還是鬼呢?」馮勰說:「我自身都是鬼了,哪裡還能把人來當作僕役呢?他也是我在陰間花五千錢買來的,也與仁兄同鄉,是南門外賣襪商人李四的兒子。」等到馮勰走了,汪瑾才放下心。
汪瑾生性謹慎,沉默寡言,始終沒有把這件事洩露於人,所以船上的人全都不知道。第二天,汪瑾去拜訪知府,留下來飲酒。正飲到親熱歡洽之處,忽然有人來報說,上官橋陳巡檢在夜裡得急病死了。知府驚愕地說:「一個精神好好的人,怎麼一下子就死啦?」汪瑾嘆息說:「冥冥之中,天理昭昭,難道是虛妄的嗎!」於是就向知府講述了自己的經歷,知府瞠目結舌了好久。
姓陳的死後無家歸葬,知府為他買了棺材衣衾,送到公墓埋葬了。清點姓陳的宦囊還有一千多兩銀子,知府痛恨姓陳的為人不良,便把它全部贈給汪瑾,說:「我這是替馮勰報姓陳的怨,報你的德。」汪瑾起初不肯接受,後聽知府說的很在理,才收下了。回家過上了小康日子。
他向鄉人打聽有認識李四的人,原來李四是回民,果然生過一子,但在兩年前,這個孩子年紀十五歲,生瘧疾死了。問他的形貌,也同馮勰的小童僕一模一樣。只是不知道在陰間是被何人所占有而賣給馮勰的。
資料來源:《夜譚隨錄》@*#
責任編輯:古容#
——看更多【古道人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