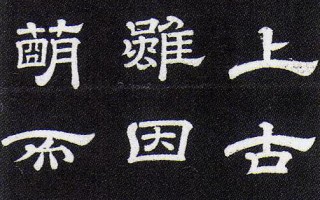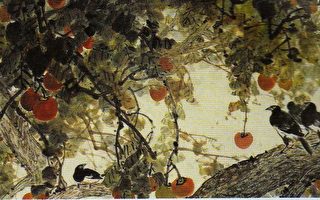一、「盧仝烹茶圖」的問題
臺北故宮博物院珍藏一幅歸在錢選名下的「盧仝烹茶圖」(下文簡稱「盧圖」),該圖為紙本,設色明亮,但清爽雅緻;無錢氏提款,只有「舜舉」一印。首經乾隆皇帝鑑定為錢氏真跡,並寫了一首長詩,裝裱在圖的上方。該圖以盧仝烹茶圖為題。考盧氏號玉川子,是唐朝與陸羽齊名的茶師,留有飲茶詩「走筆謝孟諫議守新茶」 。今畫中主人翁盧仝身著白袍、盤腿坐在花氈上;周邊是一片往上延伸的寬敞臺地。主人身旁置一茶壺與茶杯。其左為男僕,其右前方煎茶者正在煽火煮水。臺地頂端偏右有太湖石和芭蕉,右側留白。佈置優雅清澈,給人舒暢的感覺。就畫的品質而言,是今日歸錢選名下的精品。
然而,近年來有些學者提出質疑,甚至把它定為明末畫家丁雲鵬的手筆。主要的理由是:錢選雖然嗜酒但未聞其喜好喝茶,則會以烹茶為主題作畫;掛軸畫幅狹長,在南宋、元初很少見;無畫家款識,只有「舜舉」一印,此印是否有問題;該畫流傳歷史資料欠缺,畫身無乾隆以前的收藏印或提拔,而且著錄上也沒有此畫的資料;畫的風格與丁雲鵬的畫法一致 。可是類似的諸多論證在讀者之中都有不同的反應,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很有趣,也是給愛好藝術鑑賞者提供一個討論的機會,因此將個人的所知、所思集結成這篇短文供讀者參考。下文即就這幾點再做進一步的論證,而且將茶藝的時代性列入考察的項目之一。
二、錢選與「盧仝烹茶圖」
錢選(1235-約1302),浙江霅川人,字舜舉,號玉潭,又號巽舉、清癯老人、習嬾翁。南宋景定間進士,宋亡後隱居鄉間以詩酒為樂,是元初著名的畫家,因是南宋遺民,乃被歸為宋人。他的畫藝相當廣,舉凡山水、花鳥、動物無所不精,而最重要的特色不是只有寫形、出韻的工力,而且表現的超逸不俗的個性與文人畫風的時代精神。他的成就深深影響捯趙孟頫,再由趙氏傳播給元朝畫家,其後輾轉影響到明清的主流畫派。
「盧圖」到底與錢氏的風格有無緊密關係呢?上文提到的前四個論點,其實不能肯定這幅畫是後人的偽作。第一、錢選是否只喜歡喝酒而不喝茶呢?無人能證實,而不喜歡喝茶的人還是可以畫烹茶圖,因為那喝茶的人士廬泉不是畫家自己呀!就像不打坐的人也可以畫和尚打坐,不喝酒的人也可以演貴妃醉酒。第二、所謂「很少見」並不是沒有,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就有南宋馬遠的「華燈侍宴圖」,元初錢選的「荔枝圖」、管道昇的「竹石圖」、王淵的「秋山行旅圖」等等都是狹長立軸。至於第三、第四點只能提供研究者參考而已,因為這些現象在藝術史上的例子所見多是,故終結的重點還是在於畫的風格本身。
論風格,我們可以從構圖、筆觸、用色和整體表現來探索。而整體的表現更是關鍵性的議題,因為這往往是一件作品展現其時代性的面相。該圖的佈局採高視點,營造或享受李白所說的「登高壯觀天地間」那種氣勢。這種取景法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但也因時代而略有改變;顧愷之的畫讓人物漂浮在空中,觀者也同是在空中,故事觀者與畫中人物同飛。五代、北宋畫家喜歡把視點放在畫面的中段,畫出比較莊嚴的「巨碑式」山水,在南宋因為馬夏派畫比較小幅山水,所以把視點降低了。到了元初因為追求古意,再度把視點提升,他的方法並不是回復顧式的格法,而是把前景的地平線往上延伸,將聚焦放在畫面頂端的景物──如「盧圖」的太湖石和芭蕉。這也是畫中最精細的部分,顯示畫家由上往下看的視線之言連續性。意圖抹平畫面,讓畫面平淺而輕慢,也能更貼近觀者,給人一種親切感、輕鬆感。這種佈局方法,在趙孟頫的「鵲華秋色」,以及其後吳鎮、倪瓚的許多山水畫都有很精采的表現。
再就筆法而言,「盧圖」的畫法是以線描為主,只在關鍵處加一些輕淺的皴和淡墨渲染──具體的說,那是在臺地邊的一塊小崖壁和太湖石塊的凹凸處。因此畫面的視覺效果是簡樸、單純、開朗和清逸。再者,人物的姿態、視線、神情,以及背景的配置,都相當寧靜、自然、輕鬆,沒有造作的氣氛。這種風格特色也表現在錢選的其他作品中。
畫中人物的開臉的確比「貴妃上馬圖」要寫實,這可能令一些鑑賞家感到困惑,其實錢選的作畫如「秋瓜圖」、「桃枝松鼠圖」都傳達出精深的寫實功力。元初的幾名名家如錢選、龔開、趙孟頫都能以簡潔的筆墨,充分把握人像和物像的形式與結構,故那位烹茶侍者的老人臉應該不足為奇!這種「寫實」的手法沒有在「貴妃上馬圖」出現,可能因為後者是一幅仿古之作。最重要的是兩幅作品都呈現出清靜高雅的境界。
這種表現方式相當符合趙孟頫所說的「古意」。懂得閩南語的人應該都知道「古意」就是老實、單純、不耍技。因此「古意」第一個條件是人物或景物都要表現出一種簡樸、自然、超凡、輕鬆的氣氛,要配合這種境界,筆墨要溫柔、清潤,柔中寓氣,所以可以追朔到東晉的顧愷之。第一位把「古意」這個形容詞用在畫評上的是趙孟頫,但是可以說源於錢選,印為錢選幾乎是趙氏的老師。黃公望題錢選「浮玉山居」云:「趙公敏公嘗師之。」倪瓚題錢選「牡丹卷」云:「水精宮裏仙人筆,曾從溪翁(錢選)學畫花。」可見錢選的筆法、創作理念深植於趙氏的畫中。
元初的「古意」在自然主義的薰陶下,用筆也趨於自然,即配合物質面的基本形相,不是顧氏的漂浮式,也不是吳道子的銳利線條。所以今日歸在錢氏名下的人物畫中,《祡桑翁像》如果不是錢氏的仿古之作便是一件後人偽作。而《貴妃上馬圖》,所畫的雖然是唐朝的題材,卻是錢氏筆下的寧靜、清秀,不是唐人的豐盈氣魄。
三、「盧仝烹茶圖」與名畫的關係
「盧圖」會不會是明朝中葉吳派畫家的作品呢?我們都知吳派是江蘇的一群畫家凝聚出來的一種文人畫風格,其來源就是元四大家,而元四大家的風格又源於元初的錢、趙。因此吳派畫風與錢、趙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盧圖」被人懷疑是出自吳派畫家之手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整體而言,吳派畫無論人物或山水景物,其筆觸、線條的動性較強,因此都會凸出於畫面,也會跳出景物和人物的自然本體面,呈現出一種醒眼的、具有個性的書法性格,如沈周的古拙、文徵明的矯健、唐寅的曲折。即使人物畫專家的作品也沒有「盧圖」這麼安靜、純樸、冷逸。
「盧圖」與明末丁雲鵬的關係更是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其中牽涉到許多層面。就題材而言,丁氏畫了不少煮茶圖和漉酒圖,而且看來與「盧圖」有些相似之處。他的「玉山烹茶圖」似乎是參照「盧圖」改造而成的:圖中玉川即盧仝,亦是白袍,但他是半盤腿坐在鋪有地氈的石臺上。他的正右方是烹茶者,左前方是男僕。背景亦有芭蕉和太湖石,但加上芭蕉花和竹林。儘管有些相似,但是由於個性有異、時代不同,表現的方法和產生的視覺效果完全兩樣。我曾開玩笑說:「藝術家是聰明的小偷,他們偷了別人的技法和題材,放在自己的畫裏,可是一般人看不出來。」很顯然,丁氏看到「盧圖」為其所吸引,於是將它改造,加入自己的風格和時代性。因此我們不能因為「盧圖」與丁氏的畫有一點兒像就斷定它是丁氏手筆。否則清初四王仿了那多宋、元畫家的筆法,那些被仿的宋、元名畫都成了四王的作品了!
丁氏圖中人物除了扭曲的姿態之外,更有趣的是他們的腳特別短,尤其是那個男僕,簡直像個怪矮人。背景的太湖石和芭蕉,覆蓋了畫面中段的大部分空間。並加上幾朵鮮紅的芭蕉花白和幾枝綠竹。密集的翠綠色蕉葉、鮮紅的芭蕉花、扭曲的太湖石,還有石上那閃爍的「白眼群」,實在太熱鬧了,一點「古意」也沒有!至於芭蕉葉的一些細節與錢氏的芭蕉葉有點像,這可能是丁氏看過錢選的畫,而模仿的,就如他在「應真雲圖卷」中採用一個從拓本得來的羅漢像一樣,雖略有形似,但無神似。
在丁氏的作品中,強烈的對比性處處可見;丁氏筆下的人物時在有太多的誇張與戲劇畫的現像,這不只在那強力扭曲的姿態,也表現在那強力扭轉的衣折。至於樹木、石頭、花草也是靜不下來的,當然更談不上自然了,這種重大的差異不是一兩處,丁氏的畫作,無論是以人物或山水為主題,都離不開詭異、矯飾的作風。就是那幅以山水為主題的「盧山高」,其複雜、熱鬧以及造作之戲劇性,遠超過王蒙的山水。試看其畫中的臺地,與「盧圖」中的臺地放在一起,豈非天壤之別!丁氏的臺地很像人工開鑿後再用米黃色的混泥土構築出來的,也像幾片用鐵打造出來的盾牌,一點也沒有「盧圖」或錢氏其他畫作的自然氣息。
在佈局方面,丁氏畫作也是非常戲劇化。如果將「盧圖」與「玉山烹茶圖」、「煮茶圖」、「漉酒圖」等丁氏作品並列觀之,其人物的經營、位置、都可以看出其中的巨大差別:請看「盧圖」中三個人物兩近一遠,但安排的開闊寬敞而平衡,令人一見而開心。丁氏「玉山烹茶圖」將三位人物幾乎排在一條左上右下的斜線上,而且顯得擁擠熱鬧。「煮茶圖」也是擁擠異常,更有甚者是那位主人公看起來相當霸道。「漉酒圖」把三個人僅僅為在一個小盆子旁邊,主人左袖衣折曲轉蛇行往下流竄,相當詭異。
就整體佈局而言,丁雲鵬的畫比「盧圖」複雜多了,因為他採用的是移動式的視點,所以沒有聚焦,如他的「盧山高」,從下到上幾乎是同一層面,但是在這單一的層面上出現復雜的凹凸變化。這種現象也表現在他的人物畫上,譬如「漉酒圖」最底下的石塊、野草和桌上物,幾乎都是非常細緻,同樣細緻復雜的現象也表現在中段的人物和上段的花草、樹、石。儘管這樣的佈局也是讓景物貼近觀者,可是其視覺效果與「盧圖」完全不同,因為丁氏之作是讓景物衝向觀者,同時在其中開一些「小窗」讓視線延伸出去,產生強烈跳躍式視覺效果。
四、茶具與烹茶
探討「盧圖」的斷代問題,我門還可以從茶具和烹茶方式切入。古時的茶具除了壺、杯(盞)之外,還要有取水用的瓢、甌,磨茶用的碾、臼(槽)、椎(杵),以及煎茶、煮茶、泡茶用的銚(或鐺、鍋)、勺、卮漏等等。唐朝以來茶藝不斷精緻化,從採茶、製茶、煎茶、泡茶到飲茶都成了一種藝術。蘇軾「試院煎茶詩」有很精彩的敘述(註 3 ) :
蟹眼已過魚眼生(由採茶到曬茶)
颼颼欲作松風嗚
葉茸出磨細珠落(由曬茶到碾茶)
眩轉燒甌飛雪輕
銀瓶瀉湯跨第二(由煎茶、選水、取水、煮水到泡茶)
未識古人煎水意
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
貴從活火發新泉
又不見今時洛公煎茶學西蜀
寶州花瓷坪紅玉(古人泡茶很講究水質和煮水具,所以蘇軾特別弦調要「從活火發新泉」 ,又要用「花瓷紅玉」的茶具)
我今貧病常苦飢
分無玉口捧峨眉(抱怨自己貧病沒有花瓷紅玉可用)
且學公家作茗飲
磚爐石銚行相隨(只能學一般人,帶磚爐、石銚同行)
不用撐暘拄腹文字五千卷
但願一甌常及睡足口高時(不用萬卷書了,只要睡足時有一甌茶便心滿意足矣! )
「盧圖」中的茶具畫得很清楚:在盧仝右手邊有一個赭色茶壺、一個赭色的杯座上放一個白色的小茶杯、後方有一個白色的甌放置在赭色的三足座上,甌蓋己經打開。在茶師前面是一個三足的鼎形爐,爐上放一個赭色的鐺(古代一種有腳的鍋,用於烹茶)。據說在唐朝法門寺地宮中鈴現有類似的茶具,但是本人尚無緣一見。「盧圖」的爐旁有個赭色的茶壺,壺口設計相當特殊──口上加一個杯子,杯上有個蓋子。考唐宋時代,茶藝是先將茶葉曬乾,製成茶餅,泡前磨成粉末,可以直接將細粉放入壺中或杯中泡 • 但也可以在壺口加上卮漏(瀘器),在泡茶時先將茶未放入卮漏,再倒入開水,細末衝入壺中,粗片則留在卮漏中。「盧圖」這個茶壺可能加卮漏。
另外,元朝畫家趙原也有一幅烹茶圖,題為「陸羽烹茶圖卷」,但因是小寫意畫,人物和茶具都很簡率。比較明確的茶具是一個圓形三足座上放著一個甌形爐 • 爐上置一個小鍋,茶師的身旁隱約可看到一個小茶壺。主人翁陸羽半盤腿坐在廳內看茶師烹茶。畫上的題詩云:「呼童剪茗滌枯腸。軟塵落碾龍團綠,活水翻鐺蟹眼黃。耳底雷鳴輕著韻,鼻端風過細聞香。一甌洗得雙瞳豁,飽翫苕溪雲水鄉。」(註 4 )詩中提到的茶具有碾和鐺。足以證明圖中的陸羽還是用茶末。那麼「盧圖」若非見證宋、元人還用碾過的茶末沏茶,就是這位畫家在作畫前已經細心研究過唐人烹茶的方式了。
現在來看看明末畫中的茶具吧。明末最喜歡畫煮茶這個主題的是丁雲鵬。他的「廬山高」所畫的茶具最清楚,也最接近「盧圖」。畫中主人在臺地的遠方與友人對話,旁邊站著一個僮僕。臺地近處是煮茶者蹲在鼎形鑪的前方扇火(圖4)。有趣的是爐上放的是一個頂端高凸的茶壺,也說是把一個像「盧圖」中的泡茶器直接放到火爐上了。爐邊放一個碟狀器,應該是裝茶的容器。他為什麼會把茶壺直接放在爐上煮茶,而不是用鐺煮水呢?而壺上高凸的杯有何作用?會不會是一個卮漏,待水煮開之後,將茶葉放入卮漏,待茶濃之後再將茶水倒入主人身旁的小茶壺或茶杯?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丁氏的「玉川煮茶圖」。該圖也有鼎形爐,置於精雕的石臺上。爐的口呈三疊蓮瓣狀,上頭的水壺像是古時的銚(把手和短流的鍋),但作蓮篷狀,中軸部位高凸,因此其功能與「廬山高」的烹茶方式一致。主人後方的石臺上有個赭色的小茶壺 • 爐前女侍者手捧著一個盤,到底是水果或茶葉,無法論斷。但是從「煮茶」這個主題來說,茶葉的可能性比較高。雖然茶具與「盧圖」和「廬山高」類似,但有很明顯的奢華裝飾,符合明末的「矯飾作風」。
丁氏的「煮茶圖」也有同樣的設備。畫中主人坐在榻上,前方榻邊有個蓋上桌巾的小臺子,上面置一穹項式的火爐,頂上爐口放一個有卮漏、蓋和把手的多重水壺。侍者也是手捧著一個大盤子。在畫面的右下角另有一侍者正在整理一些茶具,已經取出的有一個小茶壺。
曬過的茶碾成茶末的泡茶方式,在日本延續至今,可是我們中國人今日已不再用茶末而只用茶葉。到底中國人何時改用茶葉泡茶呢?上述宋、明茶具的差異顯然可見,雖然我們無法從圖中肯定卮漏的存在,但是從茶藝史上我們知道明朝中葉之後人們開始用茶葉沏茶,而不用茶末。在繪畫上也有蹟可循,如上述趙原的題畫詩,證明元朝後期還是用茶末。明朝中葉的文徹明有「品茶圖」。圖中的茶具是一個大形的桶狀火爐,爐上有一個水壺,壺口凸出一個圓柱狀帶蓋的小杯,其功能與丁氏畫中的烹茶方式一致。再看與丁氏同時代的陳洪綬所作的「品茶圖軸」,用茶葉泡茶的習俗就更為明顯了。畫中主人與客人各持一杯,主人杯底有蓮花形「茶船」(杯托),客人則手持一個無茶船的杯,主人身邊有一個桶狀的爐子,上面放一個有長柄的蓋子,這蓋子翻過來可以變成煮水鍋。爐旁是一個無卮漏的茶壺(註 5 )。可見他們沏茶的方式與今日的習俗無異 ──直接把茶葉放入壺裡。
五、結語
綜上所述「盧圖」雖然不一定是錢選的真蹟,但無論是從風格或從畫中茶具來看,都不會是明朝末期的作品。筆者在《元氣淋漓》(註 6 )與《明山淨水》 〈註 7 )二書將錢選的作風總結在「冷逸」這個觀念上,所以作品主要的是表現「清和、寧靜、高雅、自然、寬敞、輕鬆」,也就是當時所謂的「古意」。而將明末丁雲鵬、陳洪綬等人的畫風總結於「詭異」,以「爭奇競怪求新意」為其特色,有點像西洋畫史上 16 世紀的矯飾主義( Mannerism )或 18 世紀的洛可可 (Rococo)。
元初「古意」與明末「詭異」是兩種相對的美學觀。它們的出現與發展都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簡而官之,就中國繪畫發展史而言,元初的「古意」現象是一種古典風格的再生,它的成因除了對南宋馬夏派宮庭畫的反彈之外,更反映了 中國儒士面對蒙古帝國極權統治所採取的沉潛志向和柔靜歸真的心態,也是文人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的寒蟬效應。元朝中葉文人畫家如黃公望、倪瓚、吳鎮基本上還是保存這種心態,只是筆觸略為活躍自由。元末有一段極為短暫的解放,因而出現了王蒙的繁密牛毛皴。明初政治壓力再次衝擊畫壇,文人畫相當沉寂,到了明朝中葉蘇州文人在商業社會中獲得新的生命,也有了新的活力。到了明末,亂世再起,而且西洋文化、藝術的衝擊前所未有,在這樣的環境,晝家很難一直保持靜而不動,因此爭奇鬥異的現象是不可避免了!當時同屬這種詭異畫派的畫家還有李士達、吳彬、陳洪綬、崔子忠等人。到了清初寒蟬效應重現,也帶動了弓一種以四王吳惲為代表的「古意」在畫界繁衍,使明末的詭異畫風消失無蹤。
總之,古物的鑑定是一項非常繁複的工作,而且結果也是常有爭議,很難以一已之見說服眾人,因此我們對一幅傳世珍寶的重新定位,改變作品真偽的判斷要特別謹慎。譬如最近拜讀趙茂男先生的大作「<文賦>卷中宋高宋『紹興』 印的發現」一文,意圖將<文賦>的收藏年代從元朝提前到宋高宗時代,舉出的理由是:「王羲之 『 快雪時情帖 』 的卷尾之『紹興』印,印文與 『 文賦 』 卷的 『 紹寫 』 印正相同。」(註 8 )但事實並非如此,兩印的「紹」字左右兩旁之距離,前者較遠,後者較近。而且「紹」字的絲字旁上段,後者是兩個圈連在一起,而前者則是兩圈之問多一豎筆 • 再就「文賦」卷的書法風格而言,顯然與趙孟頫有關。就以「盧圖」來說,從乾隆到二十世紀中葉,書畫鑑賞家都視之為錢選精品,今日要重新定位得三思而後行,尤其要將它歸入丁雲鵬名下更是矛盾難諧!
註1:熊宜中,「啜墨看茶-送蘇軾茶藝美學初嘆」,《藝文薈粹》,創刊號,頁12-21。《蘇東坡全集》上,頁70。
註2:傅申,「傳錢選畫<盧仝烹茶圖>應是丁雲鵬所作」,《故宮文物》,311期,頁46-57。
註3:仝註1
註4:《藝苑掇英》,第43期,頁46。
註5:《藝苑掇英》,第60期,頁11。
註6:《元氣淋漓》,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頁 14-36。
註7:《明山淨水》,東大圖書公司, 2005年,頁 225-240。
註8;趙茂男,「 〈 文賦 〉 春中宋高宋 『 紹興 』 印的發現」,《故宮文物》, 315期,頁90-93。
文章圖片提供:藝文薈粹雜誌(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