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看見了那個值四十個蘇的錢,他的腳已把它半埋在土中了,它在石子上發出閃光。這一下好像是觸著電似的,「這是什麼東西?」他咬緊牙齒說。他向後退了三步,停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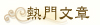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孩子停留在那叢荊棘旁邊,沒有看見冉阿讓,把他的一把錢拋起來,他相當靈巧,每次都個個接在手背上。可是這一次他那個值四十蘇的錢落了空,向那叢荊棘滾了去,滾到了冉阿讓的腳邊。冉阿讓一腳踏在上面。
門開了,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現在門邊。三個人拿著另一個人的衣領。那三個人是警察,另一個就是冉阿讓。一個警察隊長,彷彿是率領那群人的,起先立在門邊。他進來,行了個軍禮,向主教走去。
在開始行動的那一剎那間,由於幻想的擴大,他幾乎認為那個門臼活起來了,並且具有一種非常的活力,就像一頭狂叫的狗要向全家告警,要叫醒那些睡著的人。
他正陷入這種思想紊亂的時刻,在他的腦子裡有一種看不見的、來來去去的東西。他的舊恨和新愁在他的心裡翻來倒去,凌亂雜沓,漫無條理,既失去它們的形狀,也無限擴大了它們的範圍
當冉阿讓出獄時,他聽見有人在他耳邊說了這樣一句奇特的話「你自由了」,那一片刻竟好像是不真實的,聞所未聞的;一道從不曾有過的強烈的光,一道人生的真實的光突然射到他的心裡。
剛才他還在那船上,是船員中的一員,和其餘的人一道在甲板上忽來忽往,他有他的一份空氣和陽光,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現在,出了什麼事呢?他滑了一跤,掉了下去,這就完了。
對他來說,這個歷歷可見的自然界是若有若無的。我們幾乎可以說,對冉阿讓,無所謂太陽,無所謂春秋佳日,無所謂晴空,無所謂四月天的清涼曉色。我不知道是怎樣一種黯淡的光經常照著他的心。
靈魂能不能由於惡劣命運的影響徹底轉成惡劣的呢?人心難道也能像矮屋下的背脊一樣,因痛苦壓迫過甚而蜷屈萎縮變為畸形醜態,造成各種不可救藥的殘廢嗎?
社會必須正視這些事,因為這些事是它自己製造出來的。我們已經說過,冉阿讓只是個無知識的人,並不是個愚蠢的人,他心裡生來就燃著性靈的光。愁苦(愁苦也有它的光)更增加了他心裡的那一點微光。
冉阿讓在監牢裡住了幾年之後,自己也忘了那些東西。在他的心上,從前有過一條傷口,後來只剩下一條傷痕,如是而已。關於他姐姐的消息,他在土倫從始至終只聽見人家稍稍談到過一次。
他天黑回家,精疲力盡,一言不發,吃他的菜湯。他吃時,他姐姐讓媽媽,時常從他的湯瓢裡把他食物中最好的一些東西,一塊瘦肉,一片肥肉,白菜的心,拿給她的一個孩子吃。他呢,俯在桌上,頭幾乎浸在湯裡
那句極平靜的話剛說出口,他忽然加上一個奇怪的動作,假使那兩個聖女看見了,她們一定會嚇得發呆的。直到現在,我們還難於肯定他當時是受了什麼力量的主使。他是要給個警告還是想進行恐嚇呢?
那人一面吃,一面精神也振作起來了。我哥拿那種好的母福酒給他喝,他自己卻不喝,因為他說那種酒貴。我哥帶著您所知道的那種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把那些瑣事講給他聽,談時還不時露出慇勤的態度。
每次他用他那種柔和嚴肅、誠意待客的聲音說出「先生」那兩個字時,那人總是喜形於色。「先生」對於罪犯,正像一杯水對於墨杜薩1的遭難音。蒙羞的人都渴望別人的尊重。
他走進來,向前踏上一步,停住,讓門在他背後敞著。他的肩上有個布袋,手裡有根木棍,眼睛裡有種粗魯、放肆、困憊和強暴的神情。壁爐裡的火正照著他,他那樣子真是兇惡可怕,簡直是惡魔的化身。
他既肯向她探問,馬格洛大娘自然更起勁了,在她看來,這好像表明主教已有意戒備了,她洋洋得意地追著說:「是呀,主教。是這樣的。今天晚上城裡一定要出亂子。大家都這樣說。
那人拿了那四個蘇。R夫人繼續說:「這一點錢,不夠您住客棧。不過您去試過沒有?您總不能就這樣過夜呀。您一定又餓又冷。也許會有人做好事,讓您住一宵。」「所有的門我都敲過了。」「怎樣呢?」
他費盡力氣,越過木柵欄,回到了街心,孤零零,沒有棲身之所,沒有避風雨的地方,連那堆麥秸和那個不堪的狗窩也不容他涉足,他就讓自己落(不是坐)在一塊石頭上
這個異鄉人在那種溫柔寧靜的景物前出了一會神。他心裡想著什麼?只有他自己才能說出來。也許他正想著那樣一個快樂的家庭應當是肯待客的吧,他在眼前的那片福地上也許找得著一點惻隱之心吧。
新來的客人正轉過背去烘火,那位像煞有介事的旅舍主人從衣袋裡抽出一支鉛筆,又從丟在窗台旁小桌子上的那張舊報紙上扯下一角。他在那白報紙邊上寫了一兩行字
誰也不認識他,他自然只是一個過路人。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從南方來的。或是從海濱來的。因為他進迪涅城所走的路,正是七個月前拿破侖皇帝從戛納去巴黎時所經過的路
人類的遐想是沒有止境的。人常在遐想中不避艱險,分析研究並深入追求他自己所讚歎的妙境。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由於一種奇妙的反應作用,人類的遐想可以使宇宙驚奇
他的膚色紅潤,他保全了一嘴潔白的牙齒,笑時露出來,給他添上一種坦率和平易近人的神氣,那種神氣可以使一個壯年人被人稱為「好孩子」,也可以使一個老年人被人稱為「好漢子」。
我們應當完全信服一個心地正直的人。並且,我們認為,在具備了某些品質的情況下,人的品德的各種美都是可以在和我們不同的信仰中得到發展的。
卞福汝主教謙卑、清寒、淡泊,沒有被人列入那些高貴的主教裡面。那可以從在他左右完全沒有青年教士這一點上看出來。我們已經知道,他在巴黎「毫無成就」。沒有一個後生願把自己的前程托付給那樣一個孤獨老人。
無論對什麼事,他從來總是正直、誠實、公平、聰明、謙虛、持重的,好行善事,關心別人,這也是一種品德。他是一個神父,一個賢達之士,也是一個大丈夫。
我們能想像一個工人經常在熔爐旁工作,而能沒有一根頭髮被燒掉,沒有一個手指被燻黑,臉上沒有一滴汗珠,也沒有一點灰屑嗎?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的最起碼的保證,便是清苦。這一定就是迪涅主教先生的見解了。
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種無可言喻的思緒裡。他整整祈禱了一夜。第二天,幾個膽大好奇的人,想方設法,要引他談論那個G.代表,他卻只指指天。從此,他對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親切。




 2010年4月17日 1:07 PM
2010年4月17日 1:07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