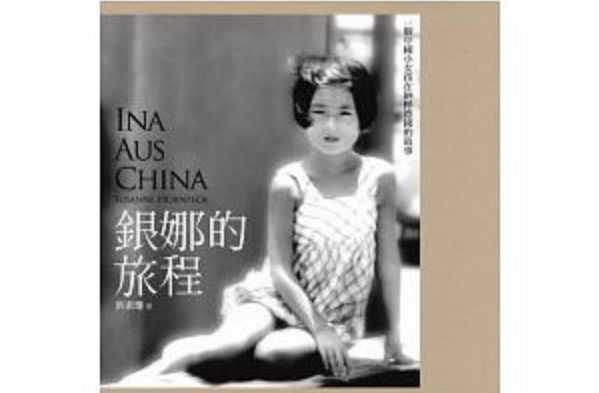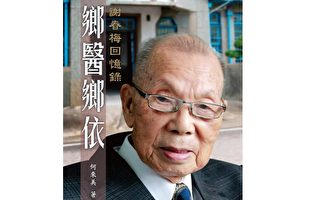這是一段改編自真人實事的故事。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
戰雲密布、人心惶惶,
七歲的陳銀娜從上海飄洋過海,來到德國,
寄養在馮·史坦尼茨太太家。
她踏上的每一片土地,都將成為遠方……
而遠方,有那盼著與她團聚的至親……
*〈新家〉
*1937年10月|布蘭登堡
從此,伊娜有了非常規律的生活:每天早上七點在大教堂的鐘聲中醒來,吃完早飯就和馮.史坦尼茨太太一起進城買東西,伊娜因此走遍了布蘭登堡不少地方。
在伊娜眼中,布蘭登堡根本算不上一座城市,沒有繁忙交通,沒有擁擠人潮,沒有高樓大廈,也沒有巨型郵輪。貫穿城中的幾條運河裡,充其量也只有些許小拖船、漁舟和小遊艇在上面行駛。
一切安詳自在,井然有序:行人走在寬闊的人行道上,寥寥可數的汽車行駛在馬路中間,電車在軌道上滑行,船隻則徜徉在運河上。警察在這兒似乎顯得有點兒多餘。
路上的行人互相招呼、問候,熟識的則停下腳步,親切地交談幾句;還有一些穿著褐色制服的人,以簡短的方式互相打招呼:右手向前方高舉,招呼聲聽起來像喉嚨不舒服在清嗓子似的。
在這兒真像人人都彼此認識,當然每個人也很快就認識了伊娜。這小城不像上海街頭,除了她沒有別的外國人。布蘭登堡沒有人纏著富有異國情調的頭巾,沒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陌生面孔,也沒有深淺不一的各種膚色。人人只說一種語言:德文。
市場是一條規畫得整整齊齊的攤販街,一星期只開放一次,所以又叫做「星期市場」。雖然百科全書上寫著,星期市場就像上海的市場一樣熱鬧,但伊娜可一點兒也看不出來,這兒的市場跟劉媽偶爾會帶她去逛的中國傳統菜場有任何相同之處!
劉媽每天下鍋的菜,都是早上從市場新鮮買回來的:先到種類不勝枚舉的蔬菜攤,葉菜類、豆莢類、根莖類,多不勝數。然後再去賣魚的攤位,看鱔魚在大木桶裡翻跳,看小蝦在水中不停伸著觸鬚……
還有五彩繽紛琳琅滿目的水果攤,攤子上有著形形色色的甜瓜,翠綠誘人的釋迦,晶亮橘黃的小金桔,還有臭氣沖天、滿身是刺的巨大榴槤。劉媽挑水果一定每個都摸一摸,確定是否完好,再狠狠的跟老闆殺價。
市場中混雜著種種氣味,香的、臭的、好聞的、不好聞的,到處都充滿討價還價的聲音,喧嘩叫嚷,此起彼落,人們只能靠手不停的比畫,確認要買的斤兩和價錢。
最後,她們還會到賣酸梅的攤子,酸梅是永遠也吃不膩的零嘴,梅核在嘴裡吸吮半天,依然甘甜可口。通常劉媽會「賞」給銀娜一小包酸梅,或是一塊包在油紙中的現煎蔥油餅。
***
要形容上海的市場,只有兩個字:「熱、鬧」!
熱鬧對中國人來說,沒別的意思,就是代表高興,代表生意好。
在德國則全然不同,這兒只能用「冷」和「靜」來形容,和中國的市場恰恰相反。所有活動都在秩序、平靜和禮貌中進行。水果和蔬菜堆放得整整齊齊,動物都是死的。
「早安,馮·史坦尼茨太太,今天想買點兒什麼?」
聽起來好像有不少東西可以挑選似的:大蔥、白菜、馬鈴薯,也許再來一些不好看也不好吃的小紫蘿蔔和大白蘿蔔。
伊娜喜歡這兩種蘿蔔,只是因為它們的德國名字特別好玩兒罷了。顧客不准碰東西,只能用手指指著想要買的蔬果,然後老闆會秤好斤兩,客人二話沒有,接過東西,付錢走人。
所以對伊娜來說,馮·史坦尼茨太太從德國廚房裡端出來的東西,就跟德國市場給她的感覺一樣,色、香、味全無!但她也知道這麼說並不公平,因為她親眼看到德國市場的東西多麼乏善可陳。不過伊娜也發現了好幾道自己愛吃的菜:洋芋煎餅、雞蛋煎餅加蘋果泥、小麥羹和煎肉餅。
伊娜常常幫忙準備午飯。吃過午飯,馮·史坦尼茨太太會睡個午覺,那段時間,誰也不准打擾。相對的,小伊娜也不會受到干擾,她可以自己玩兒,或是一個人想想心事。
通常她會躺在床上,在腦海裡整理今天新接觸到的事物:新名字、新面孔、新氣味和新口味。但飽飽的肚子和暖暖的床,常常讓思緒一不小心又溜進了劉媽的廚房。在午後陣雨的轟隆聲、唧唧的蟬鳴和爸爸親切的哼唱中,伊娜也昏昏沉沉進入了夢鄉。
驟然回到現實,阿特曼老師兩點半準時按鈴造訪。接著伊娜和老師兩人就會坐在客廳的桌子前面,開始兩小時的學習。首先,他們一起看《圖畫百科》中的一張圖,每天小伊娜都可以自由選擇一個學習主題。難道這整個陌生的世界,就在這本書的封面和封底之間嗎?要從哪一頁來開啟呢?最好還是從身邊的事物開始吧!
譬如說客廳。《圖畫百科》裡的客廳,雖然和他們現在坐在其中的客廳不太一樣,但有許多詞彙,馬上派得上用場:比如飯桌、沙發、餐具櫃、收音機、書櫃等等,只有一個叫「橡樹」的東西,伊娜在馮·史坦尼茨太太的客廳找不到。
圖上畫著一株盆栽裡的瘦小植物,但在上海,這種植物種在院子裡,不僅長得很茂盛,而且可以長得比人還高!不過在馮·史坦尼茨太太的客廳裡有一種東西,書上稱為「收音機」,阿特曼老師卻叫它「人民收音機」。這個東西對馮·史坦尼茨太太來說,十分重要,尤其在吃過晚飯以後。
第二個小時輪到寫字練習。伊娜有一本德國小學生用的課本,她從課本中學習字母和生詞,而且是德式的手寫體。伊娜覺得手寫的德文和口語的德文一樣,都帶刺帶鉤,有稜有角,但是非常實用。
譬如今天輪到「i」上場:「往上往下再往上,最後點一點在頭上」,阿特曼老師教筆順的時候,同時教了一個順口溜幫助記憶。就這麼容易,一個字母又解決了。
而這些構造簡單的字母一共不過二十六個,這對在中國必須和幾千個複雜的中文字奮戰的小孩來說,簡直就是小事一樁!德國小孩根本不知道他們有多幸福啊!
當伊娜明白用字母拼音有多方便後,心中的大石頭終於落了地:如果這二十六個字母,就可以讓人知道所有的生詞該怎麼說,那麼不久的將來,她就可以獨自將百科全書裡所有的字彙說出來,不用再去麻煩誰了。那扇通往新語言世界的大門,不就又打開了一些嘛!
吃完晚飯,伊娜重新坐回客廳。這次是和馮·史坦尼茨太太一起,兩人不再是傍著桌子坐,而是肩並肩坐在沙發上。她們先將白天學的生詞複習一遍,然後馮·史坦尼茨太太會逐一考問,看看伊娜學習的成果如何。當小傢伙的回答還算差強人意時,馮·史坦尼茨太太就會把那個叫做「人民收音機」的東西打開。
在那個時段,有個節目叫做「德國之音」,內容伊娜幾乎一個字也聽不懂。總有一個急促、粗重、氣喘吁吁的男人聲音,情緒激昂的說著:人民異議分子、人民沒有空間、「一人民、一帝國、一元首」、人民同志……
想必是因為「人民」這個詞,總是不斷傳出來,所以收音機又叫做「人民收音機」吧!伊娜比較喜歡聽音樂節目,收音機裡也總是有播。當然,大多又是「人民的音樂」!
伊娜很快就發現了,音樂其實很實用。住進聖裴堤路的第一天,那架客廳裡黑得發亮的直立式鋼琴就吸引了伊娜的注意,以前她從未見過這樣的樂器。幼稚園裡只有一臺風琴,每天早晨,大家一起唱讚美詩時,修女就會踩著踏板用風琴伴奏。
那臺風琴總是可憐兮兮的喘著氣,不斷發出咻咻聲。只有一次在上海跟爸爸去作客,在室內看到一架平臺演奏鋼琴,由一位女士彈奏出極美妙的音符。那位鋼琴家對上海潮濕悶熱的氣候相當不滿,認為會對鋼琴造成很大的傷害。
現在,這麼一架氣派非凡的樂器就擺在眼前,觸手可及。它不會喘氣──伊娜已經偷偷試驗過了──顯然也不會受到氣候之苦。
馮·史坦尼茨太太很快就發現,伊娜會不時撫摸著鋼琴,並小心翼翼的打開琴蓋,用手指試探的按著黑白琴鍵。
「妳想學鋼琴嗎,伊娜?我可以幫妳請一位老師,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我會寫信告訴妳爸爸的。」
「老師」、「爸爸」,聽懂了這兩個詞彙,其他的,伊娜再自己拼湊一下,剩下的就是拚命點頭了。
於是,畢德曼(Biedermann)小姐出現了,她每星期六都會來家裡教琴。雖然伊娜始終搞不懂,為什麼在一位女士的名字當中,會出現「男人」這樣的字!但是她非常喜歡這位新來的鋼琴老師。
她覺得畢德曼小姐不但人年輕,而且一頭金髮真是漂亮極了!尤其她那十隻修長纖細的手指,飛快的在琴鍵上滑行時,真是太迷人了!她的手指總是能按到正確的琴鍵,從不失誤。
雖然畢德曼小姐為了想教她一首簡單曲子,在第一堂課時竟彈出了《小漢斯向前行》那首歌,伊娜也早就原諒她了。
不要,不要再來一遍!她恨死了這首歌和所有相關的記憶。伊娜因為控制不住心中的憤怒和失望,激動的直踱腳,把年輕的畢德曼小姐著實嚇了一跳。
後來兩人達成協議,學習彈奏《雅格兄弟》這首歌,因為這個旋律在中國也有,只不過在中國歌詞裡,沒有「叮噹叮噹」的鐘聲,而是有兩隻跑得很快的老虎。這正是音樂的美妙之處,人人有自己的想像空間,歌詞到後來,其實無關緊要。
於是鋼琴課也順利進行著。伊娜注意聽、仔細看,然後模仿著彈。在每天與阿特曼老師共度冗長、無聊的下午時光後,鋼琴課正是她最佳的休息與調劑。不知不覺間,伊娜的右手已經可以在琴鍵上任意滑行,而左手可也一刻都沒閒著。
但鋼琴還是無法取代所有伊娜想念的事物:像跟同年齡的孩子一起嬉鬧,和寶寶之間的親密友情,聽劉媽講好聽的鬼故事,和廚房裡愛吃甜食的灶王爺。這些全都不會出現在她目前清楚規畫好的日常生活表中。
馮·史坦尼茨太太閃閃發亮、纖塵不染的廚房裡,冒不出灶王爺來,就算有吧,廚房主人也不需要用甜食賄賂他,因為所有的鍋子都光可鑑人,米袋裡也沒有生蟲長虱,灶王爺根本就沒有狀可告。而在幫忙削馬鈴薯皮的時候,也不可能隨意蹲坐在小凳子上,而是必須規規矩矩坐在椅背又高又硬的座椅上。
只有到了晚上,當馮.史坦尼茨太太不需要縫補衣物的時候,她才會問伊娜:「怎麼樣,想不想一起玩點兒什麼?」這時小伊娜就可以從兩種遊戲中選一樣來玩:一種是她從上海帶來的骨牌,另一種是馮·史坦尼茨太太櫃子裡原有的「不要生氣」。
伊娜雖然覺得「不要生氣」的名字有點兒奇怪,但遊戲確實很好玩。每當有一顆棋子——最好是她的紅色棋子——被踢回家了,必須重頭再走一次時,有什麼好生氣的呢!
那就是運氣不好嘛!趕快再擲骰子就是了,擲到「六」就又可以從家裡走出來。而且只要有棋子被踢回家,遊戲就可以一直玩下去,那麼原本規定八點整要去睡覺的,就可以往後延一下了!
***
在聞起來始終有一點地板蠟和咖啡香的屋子裡,小伊娜每天的日程表可是排得滿滿的:早餐、購物、家庭作業、午餐、德文課、練鋼琴……但日子中就是少了點兒什麼。
每當有孩子笑鬧著從街上跑過去,伊娜總是滿心渴望的望向窗外,看著他們一邊玩著抓人遊戲,一邊帶著球追打著穿過磚砌的大門,消失在城堡大院之後。
在這兒,環繞著大教堂,由高大菩提樹和古老舊房子圍成的內院,被稱為「城堡大院」。伊娜還記得,她最後一次和同伴一起瘋狂的笑鬧追逐,是在前來歐洲的船上。從那之後,世界就像被箍進了一件緊身衣裡一樣,束縛在無法表達的語言、層層規矩和必須嚴格遵守的時間表之中。
伊娜動著腦筋:要如何才能到樓下去,跟那些孩子一起玩呢?雖然馮·史坦尼茨太太在午睡的時候,幾乎不可能察覺到什麼,但她總不能一聲不吭的溜出去吧!
在「困境」中,伊娜打開那本翻閱得破破舊舊的《圖畫百科》。這本書在她之前,已經幫助過三個年輕人解決許多問題。
在書中,她發現有個主題叫做〈在公園裡〉,當中有張圖片「遊戲草場」,圖上畫著許多孩子在草原上玩球。嗯,這張圖看起來正合適!
於是有一天,在吃完中飯,洗好碗盤,伊娜照例擦乾餐具之後,她取過《圖畫百科》遞到馮·史坦尼茨太太的面前,翻到「遊戲草場」那一頁,並用手指著那張孩子正在遊戲的圖片。
馮·史坦尼茨太太特意把眼鏡戴上,仔細看了看那張圖,然後越過眼鏡上緣,用審慎的眼光看著伊娜。
「好吧,但是兩點整要回來,聽到了嗎?當教堂鐘塔敲兩下的時候。」
馮·史坦尼茨太太嚴正的舉高了兩根手指對伊娜說。
「妳得先休息一下,喘口氣,才能開始上課。還有,不要在街上亂跑,而且只准在城堡大院裡玩。」
對於那些提醒和警告,伊娜沒有聽懂多少,但訊息夠明確了!伊娜雀躍不已,她興奮地穿上從上海帶來的紅外套,第一次一個人從屋子裡走到外面,再關上那扇厚重的木製大門。
有好一會兒,她站在原地不能動,驚訝於自己的勇氣。好不容易暫時沒人監管,非要好好把握時光不可!
她飛快衝下那打蠟打得光可鑑人的樓梯,一步三階的往下跳。在樓梯轉彎處,她借助在欄杆扶手頂端的大圓球,來個大幅度的迴旋,加速往樓下衝的速度。
衝到門外的人行道上,她首先左右張望了一下。向右是進城的磨坊路,和馮·史坦尼茨太太一起去買東西的時候,總是順著這條路走。另一個方向不用幾步路,就到了城堡大院入口。
伊娜轉身向左奔去,就在要穿過磚砌大門的時候,她回頭望了一眼三樓客廳,有一扇窗的窗簾微微掀動了一下。
老遠,伊娜就聽到了孩子嬉鬧的聲音。有一個棕髮的女孩,年紀大概跟她差不多,另一個金髮的,年紀稍小,綁著兩條辮子,還有兩個男孩,正輪流對著石牆丟球。
沒有人發現伊娜,於是她靠著一棵菩提樹,遠遠瞧著他們。那個大一點的女孩正在丟著球,她口中一邊大聲數著數,一邊拍著手。
她先把球丟出去,在球彈回來之前,她要完成一連串動作,而那些動作愈來愈難:首先只要拍一次手,然後得拍好幾次,再來必須將腿抬高,讓球從胯下扔過,最後還要在原地自轉一圈。
在她玩球的時候,兩個男孩一直在旁邊干擾她,試圖讓她接不到球。
「喂,站在那邊的那個,想幹嘛啊?」一個男孩突然用手指著伊娜喊道。
「嘿,你們看,她瞇著眼睛哪!」另一個男孩也接著喊道。
「又沒有出太陽,她幹嘛把眼睛瞇成那樣啊?」
「你們別惹她!她住在馮·史坦尼茨太太那兒。我看過她們一起去買東西。」
年紀比較大的女孩打斷了他們的嘲弄,小金髮則站在旁邊一聲不吭。
伊娜不需要聽懂就了解。男孩們用食指將兩眼向外拉成一條線,這個動作她再熟悉不過。多謝指教,我知道自己在這兒是個外國人!伊娜生氣的想著。
「我叫伊娜!」她毫不示弱衝著男孩說。想嚇唬我,可沒那麼容易!
「哈哈哈,中國來的小伊娜,中國來的小伊娜!」比較大的男孩開始怪聲怪調叫嚷起來。
噢,還好嘛!伊娜想,至少在這兒我不是日本鬼子!這個開頭算不錯了。
「妳來的地方,一般人都怎麼說話?磬─鏘─瓊,還是怎麼樣?」
「我是中國人!」
伊娜先用中文回敬了一句,驕傲的抬起下巴。
「我是中國人,我來自上海,我今年七歲,我住在聖裴堤路二號。」
伊娜一口氣講完了她能用德文講的話,這招奏效了。
「嘿,妳也會講德文啊,」男孩兒讚許的說:「那妳先前講的那句話是中文囉!對吧?」
伊娜點點頭。
「我叫珞特。」
褐色頭髮的女孩這時候插了話。她個子很壯,至少比伊娜高了一個頭。
「這是英格。我們正在玩『挑戰球技』,妳要不要跟我們一起玩?」
伊娜再次點點頭。德文課本裡也有一個珞特。
「我教妳。」
珞特拿起球對著牆扔過去,在球彈回來還沒有落地之前,她拍了一下手。
「好,現在輪妳。」
珞特把球遞給伊娜。這個簡單!
接下來必須拍兩下手,然後是三下。這也都不難。但再來就必須把球一次從右腿胯下,一次從左腿胯下扔過去,而且還要來得及拍手,最後還必須在原地自轉一圈才能接球,那可真的需要動作很快才行。
兩個男孩早就放棄干擾接球的差事,張大了嘴,等著看新來的玩伴怎麼搞定這個遊戲。
「到後來動作比較難的時候,妳最好把球扔高一點。像這樣,妳看。」
這時英格也插進來了,示範給伊娜看。
「這樣妳就會有比較多時間。」
「時間」、「鐘」、「兩點鐘」,唉呀,糟糕了!
伊娜突然想起了阿特曼老師和馮·史坦尼茨太太的警告。她迅速抬頭望向鐘塔,大鐘的指針正極具威脅的朝兩點鐘邁進。
「上課!」
伊娜因為不停丟球、拍手、轉圈,一下子還喘不過氣來,她吃力的吐出兩個字並指著塔樓上的鐘。
「妳明天還會來嗎?」珞特問。
「來!」
伊娜堅定的回答,雖然她一點也不確定女孩問的意思,但至少她心中渴望對方這麼問自己。
「我會來!」
為了保險起見,伊娜一邊往回跑,一邊又對珞特喊了一次。
「而且我會教妳們玩剪刀、石頭、布!」
最後這一句話,伊娜沒有真正說出口,就算她說了,其他人也聽不懂,因為她只會用中文說。
***
「星期六,瑪爾塔要來看我們。」
早餐時,馮·史坦尼茨太太對伊娜說。
對於好消息,伊娜總是很快就能明白。她正喝著大麥咖啡,差點兒嗆到。有太多事她想要問瑪爾塔,堂姊一回來,語言也就回來了。
這些日子,伊娜總覺得自己像個牙牙學語的小娃娃,結結巴巴講不清一句話,真是討厭極了。有太多的問題和想法積壓在她的腦袋瓜裡,等著堂姊替她清倉。
「她從柏林寄來了一張明信片,寫明了抵達時間,到時候我們可以去火車站接她。」
「好耶!」伊娜高興的歡呼起來。
馮·史坦尼茨太太將瑪爾塔那張沒有圖片的明信片遞給伊娜,她仔細研讀起來。堂姊的德文字十分工整,容易辨認。這些日子以來,伊娜跟著阿特曼老師學完了字母,她開始大聲的,一個字一個字的拼出來:
「親─愛─的馮.史坦尼茨太太!」第一行這麼寫著。
「我已─經─找─到─了一間─房,一切也都安─頓─好了。」
哇!有夠難。伊娜不認得她讀的那些字,但羅馬拼音的好處,就是不知道字義,照樣唸得出來,這在中文裡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想─來─探─望─您和伊娜;如果可─以─的話,我就星─期─六,三十點來。」
「是十三點!」馮·史坦尼茨太太糾正她。
我永遠搞不懂為什麼德國人要把數字倒過來唸!伊娜心中嘀咕著。好了,不管了,繼續唸:「有一─封─我叔叔寫─給伊娜的信也在─我這。」
「爸爸的信!」
伊娜高聲喊著,因為太過激動,明信片從她手中落了下來。
明信片上還寫了什麼,都不重要了。現在,伊娜更殷切期盼著星期六的到來。
但是,為什麼爸爸不把信直接寄過來呢?欸,無所謂了,重要的是她馬上就可以拿到信了。
星期六終於到了。
她們搭乘電車經過聖安娜街抵達火車站,買了月臺票。從柏林來的快車駛進車站時,伊娜伸長了脖子。瑪爾塔是唯一的中國人,在成群的旅客當中,遠遠就能認出。
伊娜拔腿就向她衝過去。
「嗨!阿肥……真高興妳能來接我。」
終於又聽到那熟悉、抑揚頓挫的中文!
「馮·史坦尼茨太太也來了嗎?啊,她在那後邊站著呢!」
「我的信妳帶來了嗎?」
伊娜才剛提出問題,瑪爾塔口裡的語言又換成了德文。
她跟馮·史坦尼茨太太打過招呼後,就熱絡的向她報告別後情況。房間、柏林、翰理、大學……瑪爾塔從車站回家的路上,就這樣說個不停。就算伊娜一路上不斷扯她的衣袖,也無濟於事。
「大人講話不可以打斷!」是瑪爾塔在船上時就再三叮囑的金科玉律之一。現在她是大學生了,當然算是大人了,所以對糾纏不休的小堂妹,自然名正言順的不予理會。
伊娜快要忍不住了。瑪爾塔一定要現在講那些無聊的事嗎?難道她就不能想想,我有多希望看到爸爸的信嗎?伊娜心裡生著悶氣。
馮·史坦尼茨太太似乎也沒有察覺到什麼,她一面興趣盎然,聽著瑪爾塔滔滔不絕敘述著,一面從容不迫打開了大門。
終於,瑪爾塔把大衣掛好在衣帽間裡,開始在包包裡翻找起來,取出了信,並交給伊娜,然後就和馮·史坦尼茨太太一起消失在廚房裡。
伊娜站在走廊上,肅穆的看著手中的信封:信封上花花綠綠的郵票,蓋滿了郵戳,粗紙製成的直式信封,還有用中文寫成的寄信人姓名,這些看起來都那麼熟悉。
這封信和她及瑪爾塔一樣,是經過了千山萬水才來到這裡。當她屏息凝神的從信封中抽出信紙,鼻尖因為心情激動而不自禁的一酸。信紙先包折,然後在上方約三分之一處,又往下折了一折。整張信紙從上至下,是用毛筆寫的,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寫滿了一張。
伊娜一下子愣住了。剎那間她意識到,自己和爸爸的距離不單是遠隔重洋,還包括了語言和文字。她認不得爸爸寫的漢字,爸爸也看不懂她寫的德文。想到這裡,淚水一下子湧進眼眶,一滴滴落在信紙上。幸虧中國的墨汁要比西方的墨水防水一些,伊娜迅速將信又折了起來。
「要我唸給妳聽嗎?」瑪爾塔問。
她手裡端著裝滿東西的托盤,踏出廚房,正要往客廳走去。在昏暗的走廊上,她沒有察覺到伊娜哭了。
難怪爸爸把信寄給瑪爾塔,他知道若沒有堂姊幫忙,我是看不懂信的,可瑪爾塔滿腦子只想著自己的事。但,抱怨委屈無濟於事,現在只能靠堂姊了。
「是的,謝謝!」伊娜輕聲回答。
「還是進客廳來吧!走廊上太黑了,我什麼也看不見。咦……怎麼了?妳幹嘛哭啊?難道不高興收到信嗎?」
這個瑪爾塔,怎麼就是什麼都不懂!
「好,聽著,妳爸爸的信是這樣寫的……」
我親愛的女兒銀娜:
妳好嗎?冬天快要到了,妳去德國也有好一陣子了。我希望妳已經適應那邊的氣候,也習慣了馮·史坦尼茨太太家裡的生活。很遺憾的,我個人並不認識馮·史坦尼茨太太,不過我們兩家一直有著深厚的情誼。
我很高興妳能在德國受到妥善的照顧,因為這兒的情況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妳是知道的,劉媽回了鄉下老家,而我也必須跟著銀行遷到重慶。
一個人在重慶生活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身邊少了妳,少了劉媽,少了廚房裡乒乒乓乓的聲音,屋子裡變得好安靜。我們現在必須耐心等待,看政治的情勢將會如何發展。希望戰爭不要持續太久,妳能盡快回到中國來。
答應我,要不時跟美華練習中文,不要完全忘記妳的母語。
做個乖女兒,好好用功讀書。爸爸非常想念妳。
愛妳的父親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於重慶 ◇(節錄完)
【作者簡介】
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
德國慕尼黑大學文學博士,漢學家,現居德國南部慕尼黑市近郊。從事專業著述及書籍翻譯,曾譯介多位中文名家作品至德語世界,是中、德文學交流的重要推手。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受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派任,於臺灣大學外文系擔任客座講師。在臺任教期間,結識本書主人翁陳銀娜(化名),得知銀娜的人生故事,於是起了念頭,開始撰寫這個中國小女孩在二戰期間的奇妙經歷。
她以十年工夫寫就的「認同三部曲」,地理上跨越了歐亞大陸,時間上從二十世紀上半葉來到二十一世紀初,主題涵蓋戰爭、流亡、離散、融合,透過三位女主人翁銀娜、英格和木蘭的人生故事。
——節錄自《銀娜的旅程》/ 左岸文化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余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