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艾希禮所愛的正是她的這些東西。正因為瞭解這一點,她才覺得生活還能忍受下去。她瞭解艾希禮很欣賞那些深深埋藏在她身上、唯獨他看得見的美好東西,但是了為保全名譽,他只能夠對他保持著一種遙遠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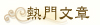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你休想讓一個威爾克斯家的人成為幹農活的能手……或者成為別的有用人才。他們這個家庭純粹是擺設。現在,消消氣吧,別在意我對那麼驕傲而高尚的艾希禮說了這許多粗魯的話。我真奇怪連你這樣一個精明而講求實際的女人居然也會抱著這些幻想不放。你到底要多少錢,打算幹什麼用呢?
她默默在坐那裡,膝頭上攤著那本厚厚的帳簿,驚異得微微張開嘴,心想在塔拉那幾個月貧困的日子裡,她確確實實幹過一個男人幹的活兒,而且幹得相當出色呢。她一直受到這樣的教育,認為一個女人是不能單獨成事的,可是在威爾到來之前,她沒有任何男人的幫助,不也照樣把農場管起來了嗎?
如果她是男人,她一定要把店抵押出去,用這筆錢來買鋸木廠。但是婚後第二天當她輕描淡寫地向弗蘭克暗示這一想法時,他只微微一笑,叫她那可愛的小腦袋瓜不必為生意上的事操心。她居然還知道什麼叫抵押呢,這叫他有點驚訝。
兩個星期之後,經過一場旋風式的求婚,思嘉與弗蘭克.肯尼迪結婚了。她紅著臉告訴對方,他的求婚方式使她沒有一點喘息的機會來拒絕他的熱情。
她凝望著跳得滿臉興奮的人們,心想他們是不是也像她那樣為種種事物所驅使,為已故的情侶、傷殘的丈夫、飢餓的兒女、失掉的土地,以及那些庇護過陌生人的可愛的住宅。不過,毫無疑問,他們是迫不得已啊!她瞭解他們的環境,比瞭解她自己的只略略少一點。
樂隊奏完開場曲以後立即轉入《老丹.塔克》樂曲,這時托米請她跳舞。「你想跳嗎,思嘉?我不敢請你,不過休或者雷內……」「不,謝謝。我還在為母親守孝呢,」思嘉連忙婉言謝絕。「我要坐在這裡,一次也不跳。」
思嘉感覺到了無言的支持,而且腳頭的那塊熱磚也使她暖和起來了,於是剛才在馬車上挨凍時已隱約閃爍的那個希望,此刻便成了熊熊大火。它叫她渾身發熱,心臟怦怦跳著使血液的血脈中迅速循環。力氣也恢復了,在一種難以控制的激情之下她差點要大笑起來。還沒有被擊倒呢。她愉快地想。
她繼續啜泣著,間或說一兩句話,這便讓弗蘭克猜想塔拉的景況一定很不好了。奧哈拉先生仍處於「精神嚴重失常」的狀態,家中又沒有足夠的糧食養活那麼多人。所以她才跑到亞特蘭大來想掙點錢維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弗蘭克囁嚅了片刻,突然發現她的頭已經靠在他肩上了。他弄不明白它是怎樣靠過來的。
聽你這麼說我真高興。宣佈投降以後,我有大約十塊銀元,別的一無所有。你知道他們對瓊斯博羅和我在那裡的房子和店都幹了些什麼。我真不知怎麼辦才好。可是我用這十塊錢在五點鎮旁邊一家舊鋪子上蓋了個屋頂,然後將那些醫療設備搬進去並做起買賣來。
她從消防站走出來時天正在下雨,天空陰沉沉的一片淺灰色。廣場上的士兵們都到棚屋裡躲雨去了,大街上也很少有行人。她看不到哪裡有什麼車輛,便明白自己只有一路步行回家,可路還遠著呢。她一路艱難地走著,白蘭地的熱勁漸漸消退了。寒風吹得她瑟瑟發抖,冰冷刺骨的雨點迎面向她打來。
她的下顎緊得成了方形,她的眼睛變成翡翠的顏色。「你還記得圍城期間在皮蒂姑媽家走廊上的那個夜晚,你說過……那時你說過你是要我的。」他在椅子上漫不經心地向後一靠,瞧著她那緊張的臉,同時他自己的棕色臉龐上顯出一種莫測高深的表情。似乎有什麼在他眼睛後面閃爍,可是他一聲不吭。「
這時他仍然沒有抬起頭來,她仍然看不見他的臉。他毫不容情地把她的拳頭掰開,凝神著它,接著把她的另一隻手也拿起來,把雙手合在一起,默默地捧著,俯視著。「看著我,」他終於抬起頭來說,但聲音顯得十分冷峻。
被他激起來的舊恨宿怨此時還在她心中起作用,因此她很想說些刻薄話。但她還是裝出滿臉笑容,一副逗人憐愛的模樣。他拉了把椅子過來緊靠她身旁坐下,她也就湊過去,裝著漫不經心地把一隻手輕輕地擱在他的臂膀上。
第二天清晨,太陽斷斷續續地照耀著,狂風驅趕烏雲飛速地掠過它的面孔,刮得窗玻璃發出嘎嘎的響聲,在房屋周圍隱隱地呼喊著。思嘉念了一句簡短的祈禱。感謝頭天晚上的雨已經停了,因為她曾躲在床上聽著雨嘩嘩地下個不停,心想這樣下去她的開鵝絨新衣服和新帽子就全完了。
思嘉想起塔拉像銅錢般閃耀的天空下那一行行的棉花和她弓著身子侍弄它們時那種腰酸背痛的感覺。她想起自己用一雙毫無經驗的、滿是血泡的手扶著犁把時的滋味。她覺得休.埃爾辛也並不是特別值得同情的。皮蒂是個多麼天真的老傻瓜呀,而且,儘管是一片廢墟,她還過得真不錯呢!
嬤嬤的機警眼光帶著猜疑和詢問的神色搜索她,但她的好奇心沒有獲得滿足。原來思嘉是在回想那天自己的恐懼心情,覺得太可笑了。那時她被北方佬嚇壞了,被媚蘭既將分娩的緊張狀況嚇壞了,簡直是在心驚膽戰地爬行唉!
話說宋江不負晁蓋遺言,要把主位讓與盧員外,眾人不伏。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卻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裏百姓,若去問他借糧,公然不肯。今寫下兩個鬮兒,我和盧員外各撚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
 2008年5月4日 3:07 PM
2008年5月4日 3:07 PM 第二天一早,思嘉和嬤嬤迎著寒風凜冽和彤雲疾捲的陰沉天氣在亞特蘭大下了火車。火車站在全城大火中毀了,還沒有重建起來,她們是在那堆高出廢墟好幾碼的灰燼和爛泥中跳下來的,它們告訴人們,這裡就是火車站了。
晚餐後,收拾完餐具,思嘉和嬤嬤把衣服樣子放在飯桌上,這時蘇倫和卡琳忙著拆窗簾的緞子襯裡,媚蘭用乾淨刷子刷天鵝絨窗簾上的塵土。傑拉爾德、威爾和艾希禮坐在房間裡抽煙,一面嘻嘻哈哈地看著婦女們在忙合。思嘉身上似乎有一股愉快的興奮之情感染了大家,但他們並不理解這種興奮的意義。
一想到行動,她就昂頭挺胸起來。她清楚,這樁事不會是輕而易舉的。上一次,那是瑞德在討好她,而她自己是掌權人。可如今她成了乞丐,是個無權提出條件的乞丐了。「可是我決不像乞丐去求他。我要像個施恩的王后那樣到他那裡去。他萬萬不會知道的。
誰也不會想起要到這裡打擾她,而她正需要時間來安靜地想一想。剛才腦子裡閃出的那個念頭原來這樣簡單,她不明白以前為什麼她竟沒有想到過。「我要從巴特勒那裡弄到錢。我要把鑽石耳環賣給他,要不就向他借錢,用耳環作抵押,將來有了錢再還給他。」這時候,她覺得大大放鬆了,結果反而顯得虛弱起來。
思嘉走上屋前的台階時,她手裡還抓著那團紅泥。她小心翼翼地避免走後門,因為嬤嬤眼尖,一定會看出她做了什麼大不該的事。她不想看見嬤嬤或任何別的人,她覺得她再也沒有勇氣同別人見面或交談了。她沒有什麼難為情、失望或痛苦的感覺,只覺得兩腿發軟,心裡空虛到了極點。
而他現在正面對著嗦嗦發抖的恐懼,這是她所從未經歷過也無法想像的。因為,她堅信,在這個劫後至殘的世界上,除了飢餓和寒冷,以及喪失家園,還有什麼比這更要怕的呢?而且她思量過,只要她注意傾聽,她是會知道怎樣去回答艾希禮的。
原來上星期皮蒂帕特姑媽已給媚蘭寄來了信,說瑞德帶了一輛馬車和兩匹駿馬以及滿袋滿袋的美鈔回到了亞特蘭大。不過她表示了這樣的意思,即他的這些東西都是來路不正的。皮蒂姑媽有這種看法,這在亞特蘭大頗為流行,那就是瑞德曾經設法夾帶聯盟州金庫裡一筆數百萬的神秘款子跑掉了。
而她竟然那麼傻,曾經以為熬過這段艱難的日子,只要她能夠堅持到春天,就會萬事大吉的。可威爾帶來的這個令人可怕和絕望的消息卻在整整一年累死累活和苦苦盼望之後降臨,這已經是將她徹底壓垮的最後一份負擔了。
1866年一月一個寒冷的下午,思嘉.奧哈拉坐在房裡給皮蒂姑媽寫信,詳細解釋為什麼她自己、媚蘭或艾希禮都無法回到亞特蘭大去同她一起住,這已是第十次寫這樣的信了,她很不耐煩,因為知道皮蒂姑媽一讀完開頭幾句就會把信放下,然後再一次來信訴苦:「可是我真害怕獨自一個人生活呀!」
實際上全家所有的人都喜歡到威爾的房裡去坐坐,談談自己心中的煩惱……嬤嬤也是如此,她本來疏遠他,理由是他出身門第不高,又只有兩個奴隸,可現在改變態度了。待到他能夠在屋裡到處走動了,他便著手編製橡樹皮籃子,修補被北方佬損壞的傢具。他手很巧,會用刀子削刻東西,給韋德做了這孩子僅有的幾個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