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米德大夫寫的有關你的那些話都是對的,巴特勒船長。惟一挽救的辦法是你把船賣掉之後立即去參軍。你是西點軍校出身的,而且……」「你這話很像是個牧師在發表招兵演說了。要是我不想挽救自己又怎麼樣?我要眼看著它被徹底粉碎才高興呢。我幹嗎要去拚命維護那個把我拋棄了的制度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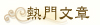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在梅裡韋瑟太太的慫勇下,米德大夫果斷行動起來了。他給報社寫了封信,其中雖然沒有點瑞德的名,但意思是很明顯的。編輯感覺了這封信的社會戲劇性,便把它發表在報紙的第二版,這本身就是一個驚人之舉,因為報紙頭兩版經常專登廣告,而這些廣告又不外是出售奴隸、騾子、犁頭、棺材、房屋、性病藥、墮胎藥和春藥之類。
演完活人畫以後,她不由得要尋找瑞德的眼睛,看看他是否欣賞她所扮的這幅精美的圖畫。她煩惱地看見他正跟別人辯論,很可能壓根兒沒有注意她。思嘉從他周圍那些人的臉色可以看出,他們被他所說的什麼話大大激怒了。
謠傳說,巴特勒船長是南方最出色的水手之一,又說他行動起來是不顧一切和泰然自若的。他生長在查爾斯頓,熟悉海港附近卡羅來納海岸的每一個小港小灣、沙洲和岸礁,同時對威爾明頓周圍的水域也瞭如指掌。他從沒損失過一隻小船或被迫拋棄一批貨物。
皮蒂明明知道愛倫不會贊成巴特勒來看她的女兒,也知道查爾斯頓上流社會對他的排斥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可是她已抵制不住他那精心設計的恭維和慇勤,就像一隻蒼蠅經不起蜜糖缸的引誘那樣。
戰爭繼續進行著,大部分是成功的,但是現在人們已不再說「再來一個勝仗就可以結束戰爭」這樣的話了,也不再說北方佬是膽小鬼了。現在大家都明白,北方佬根本不是膽小鬼,而且決不是再打一個勝仗就能把他們打垮的。
思嘉沒有繼續讀下去,便小心地把信折起來,裝進封套,因為實在讀得有點厭煩了。而且,信中用的那種語調,那些談論失敗的蠢話,也叫她隱隱感到壓抑。她畢竟不是要從媚蘭的這些信件中瞭解艾希禮的令人費解而枯燥無味的思想呀。這些思想,他以前坐在塔拉農場的走廊上時,她已經聽得夠多的了。
那以後一個星期的某一個下午,思嘉從醫院回來,感到又疲倦又氣憤,之所以疲倦,是因為整個上午都站在那裡,而氣憤的是梅裡韋瑟太太狠狠地斥責了她,因為替一個傷兵包紮胳臂時她坐在他的床上了。
思嘉隱約看見一輛馬車在屋前停下來,幾個模糊的人影下了車。有個什麼人跟著他。那兩個影子在門前站住,隨即門閂一響,思嘉便清清楚楚地聽到了傑拉爾德的聲音。「現在我要給你唱《羅伯特.埃米特輓歌》,你是應該熟悉這支歌的,小伙子。讓我教你唱吧。」
她越發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父親會很凶的。她終於知道自己已不再是個可愛的淘氣孩子,不能坐在他膝頭上扭來扭去賴掉一場懲罰了。「不是……不是壞消息吧?」皮蒂帕特向她問道,緊張得發抖。
次日早晨吃雞蛋餅時,皮蒂帕特姑媽在傷心落淚,媚蘭一聲不響,思嘉則是一副倔強不屈的神態。不管他們怎麼議論,我不在乎,我敢打賭,我給醫院掙的錢無論比哪個女孩子都多……比我們賣出那些舊玩意兒所有的收入還多。」「唔,錢有什麼了不起呢?親愛的?」皮蒂帕特一面哭泣,一面絞著兩隻手說。
她要領跳那場弗吉尼亞雙人舞呢。她輕捷地給他一個低低的屈膝禮和一絲嬌媚的微笑。他將手放在他穿著皺邊襯衣的胸口上鞠了一躬。本來嚇呆了的樂隊指揮利維這時立即想起要掩蓋這個場面,便大叫一聲:「挑好你的舞伴,準備跳弗吉尼亞雙人舞呀!」於是樂隊嘩地一聲奏起了最美妙的舞曲《迪克西》。
我同時觀望別的女孩子。她們全都好像是從同一個模子裡鑄造出來的面孔。可你不一樣,你臉上的表情是容易理解的。你沒有把你的心思放在事業上,並且我敢打賭,你不是在思考我們的主義或醫院。你滿臉表現出來的是想要跳舞。要好好玩樂一番,但又辦不到。所以你都要發狂了。講老實話吧,難道我說得不對嗎?
米德大人登上樂台,攤開兩隻手臂叫大家安靜,接著響起一陣鼕鼕的鼓聲和一起噓聲。「今天,我們大家。」他開始講演,「得衷心感謝這麼多美麗的女士們,是她們以不知疲倦的愛國熱情,不但把這個義賣會辦得非常成功,而且把這個簡陋的大廳變成了一座優美的庭園,一座與我周圍的玫瑰花蕾相稱的花園。」大家都拍手讚賞。
媚蘭聽了他的聲音,便轉過身來,這時思嘉才頭一次謝天謝地慶幸自己在世界上還有這麼一位小姑子。「怎麼……這是……是瑞德.巴特勒先生,不是嗎?」媚蘭微露笑容說,一面伸出手來。「我見過你……」「在宣佈你們訂婚的喜慶日。」他補充說,同時低下頭來吻她的手。
但是,對於年輕的單身漢—-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不妨對他們溫柔地微笑,而當他立即注意到你為何這樣笑時,你可以拒不說明,並且笑得更歡一些,逗著他們一直在你周圍琢磨其中的奧秘。你可以在眼角眉梢示意,應許他們多多少少帶刺激性的東西,叫他們千方百計要跟你單獨說話。
當這種叛逆性的褻瀆思想在她心中出現時,她偷偷地向周圍觀察,生怕有人從她臉上清楚地看出來。啊,她怎麼就不能跟這些女人有同樣的感受呢!她們對主義的忠誠是全心全意的,是真摯的。她們所說所做的一切的確出於至誠。而且,如果有人要疑心她……不,決不能讓人知道!
並非城裡所有的花都是獻給南部聯盟兩位領袖的。那些最小最香的花朵都裝飾在姑娘們身上。茶花插在粉嫩的耳朵背後,茉莉花和薔薇花蕾編成小小的花環珮戴在兩側如波濤翻滾的鬈髮上;有的花朵端端正正地點綴著胸前的緞帶,有的不等天亮就會作為珍貴紀念騎裝進那些灰制服的胸袋中。
在午睡時刻,梅裡韋瑟太太和埃爾辛太太坐著馬車登門拜訪來了,她沒有想到憂鬱的心情竟這樣得到了解脫。媚蘭、思嘉和皮蒂帕特姑媽都對這種不適時的來訪感到吃驚,於是趕快起來扣好胸衣,掠了掠頭髮,下樓迎接客人。
那年夏天的一個早晨,思嘉坐在臥室的窗前,滿肚子不高興地觀看好些大車和馬車載著姑娘們、大兵和他們的陪伴人,興高采烈地駛離桃樹街,到林地去採集松柏之類的裝飾物,準備給當天晚上要為醫院福利舉辦的義賣會使用。陽光在枝柯如拱的大樹下閃爍,那條紅土大道在樹蔭中光影斑駁,紛紛而過的馬蹄揚起一陣陣雲霧般的紅色塵土。
查爾斯沒有從他自己最喜歡的那兩個人那受到強有力的影響,也沒有學會粗暴或講求實際,因為養育他長大的家庭溫柔得像隻鳥窠。這個家庭跟塔拉比起來,顯得是那樣安靜,那樣舊式,那樣文雅。
因此思嘉這次到亞特蘭大來,也沒有事先想過要在這裡住多久。如果她覺得在這裡像在薩凡納和查爾頓斯那樣沉悶無聊,那她一個月後就回家去。如果住得開心,她就無限期地住下去。但是她一到這裡,皮蒂姑媽和媚蘭就開始行動起來,勸說她跟她們永久住在一起。
這兩位太太再加上另一位,即惠廷太太,是亞特蘭大的三根台柱子。她們管理著自己所屬的那三家教堂、牧師、唱詩班和教區居民。她們組織義賣和縫紉會,她們陪伴姑娘們參加舞會和野餐,她們知道誰找的對象好,誰的不好,誰常常偷著喝酒,誰要生孩子了和什麼時候生,等等。
思嘉渴望著嬤嬤那雙肥大又老練的臂膀。嬤嬤的手只消往孩子身上一擱,孩子馬上就不哭了。可如今嬤嬤在塔拉,思嘉已毫無辦法。她即使把小韋德從百里茜手裡抱過來,也沒有用。她抱著同百里茜抱著一樣,他還是那麼大聲嚎哭。此外,他還拉扯她帽子上的飾帶,當然也會弄皺她的衣裙。所以她便索性裝做沒有聽見彼得大叔的話了。
1862年五月的一個早晨,火車載著思嘉北上了,她想亞特蘭大不可能像查爾斯頓和薩凡納那樣討厭的,而且,儘管她對皮蒂帕特小姐和媚蘭很不喜歡,她還是懷著好奇心想看看,從前年冬天戰爭爆發前她最後一次拜訪這裡以來,這個城市究竟變得怎樣了。
她的厭煩情緒是強烈而經常的。自從軍營開赴前方以後,縣裡就沒什麼娛樂和社交生活了。所有有趣的年輕男子會都走了……包括塔爾頓家四兄弟、卡爾弗特家哥兒倆、方丹家和芒羅家的小伙子們,以及從瓊斯博羅、弗耶特維爾和洛夫喬伊來的每一個年輕而逗人喜愛的小伙子。
不過兩星期工夫,思嘉便由一位小姐變成了人家的妻子,再過兩個月又變成了寡婦,她很快便從她那麼匆促而很少思索地給自己套上的羈絆中解脫出來,可是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有嘗過未婚日子那種無憂無慮的自由滋味了。寡居生活緊隨著新婚而來,更叫她驚慌的是很快便做了母親。
他垂下眼睛,因為它們跟思嘉那雙鋒利得像要穿透他又似乎沒有看見他的綠色的眼睛恰好相遇了。「他有很多錢,」她匆匆地想,一個念頭和一個計謀接連在腦子裡閃過。
從樓梯頂上的那個凸窗裡,她能看見男人們還在樹下和涼亭的椅子上斜躺著歇息。她真羨慕他們極了!作為一個男人,永遠也不用經受她剛才把經歷的那種痛苦,該多快活呀!
只有媚蘭這個名字的聲音使她恢復了意識,於是她注視著他那雙水晶般的灰眼睛。她從中看到了那種常常使她迷惑不解的顯得遙遠的感覺……以及幾分自恨的神情。




 2008年2月23日 5:13 PM
2008年2月23日 5:13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