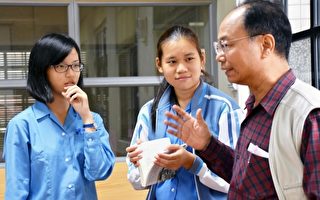每天都有晴好的太陽,爸爸可從床上下來,挪到屋簷下的陽光地裡,蓋上棉被躺在籐椅上。他整個人都瘦了,面上和身架皆骨頭支稜。膚色倒白皙了些,雙目黑亮沉鬱,瘦成了新的。
爸爸常常溫柔地、久久地注視著門前的長河,水上結著一層薄冰。田野裡生著青絨絨的麥壟。他對兄弟倆說:「你們的爸爸不會成殘廢人了!我感覺到身上的骨頭正在長攏。過了年,我肯定就能走路了。」
大年初一早上,爸爸給霄霄和喬喬賞了一個紅紙包的壓歲錢。媽媽和祖母,也各有一份。老的小的,接過壓歲錢時的喜悅表情,令爸爸生出無言的欣慰。正月裡的頭幾個日子,家裏都有朋友們來喝酒,媽媽在廚房裡切滷菜,煎魚,溫酒,做火鍋。兄弟倆放了心,便又心安理得地歡活起來,和台上的夥伴們聚集在一起,帶著煙花、火鞭、萬花筒,沖天炮。去遠遠的田野上放爆竹,放野火燒荒,烤紅薯和玉米,從家裏偷出來的臘香腸,野鴨和米糍粑匯合,夥伴們聚餐。夜晚在荒溝裡點燃的野火,紅焰騰騰的,燒紅了半個黑夜。孩子和家養的黃狗成群結隊地在台上出出入入,氣勢揚揚,呈天不管地不收之態。
過完了元宵。天上下起了濛濛的霧雪,氣溫反倒比臘月裡冷了。打工的人們就在這樣的天氣裡,背著一床棉被出門去了。爸爸坐在屋簷下,和他們一個個地打招呼。男人們問道:「黑狗,你不出門了嗎?」
爸爸輕鬆地說:「不打算出門了,我打算就在家裏種地。」他招呼他們「進來坐一會兒,趕路也不遲。」那些人就放緩了步子,他們將行李擱在窗戶底下,拿椅子坐在屋簷下。
「黑狗,其實誰他娘的想出門呢?誰不想在家裏守著田畝老小,舒舒心心過日子?在家裏終歸沒人欺負你把你不當人罷?可是,出門到外面打工終歸是條養家的路。」
「種地真是種傷心了,棉花也賤,稻穀也賤,辛辛苦苦地耕地薅草,倒搭上肥料農藥,日他娘到頭來一樣都變不出錢來。在城市裡哪怕揀荒貨撿垃圾,都比家裏種十畝地強。」
爸爸陪著他們歎氣:「是啊,誰說不是這回事呢?出門在外沒一天不受氣受累的,就彷彿鄉下人都不是娘養下來的。」然而,他說:「可田裡的地總是要有人來種的。再說,我出門也真是傷心了。再不出門了。」
他的朋友們就嘲諷道:「等著吧,你種一年地,倒莫名其妙欠他娘的一身的款項。都是驢打滾的利息。」
黑狗笑一笑,歎口氣,雙方都沉默著說不出話來了。他們抽著煙,望著長河裡破冰的綠波蕩漾的春水,田野的油菜花開成了黃燦燦的無涯的花海。一隻船從遠方突突突地駛來了,上頭已經坐了許多出門的民工,爸爸的朋友們趕緊招手,招呼船泊到木糶邊,他們背起了行李,緊一緊褲腰帶,往河畔走,回頭又對潘清波揮揮手,道:「黑狗!你留在村裡,我們在外頭到底還安心些。從開春起,我們的女人就都歸你照看了。田畝也都歸你耕啦!我們到年底再回來接管。」
黑狗聽了,暢快地笑起來,大方地應承道:「你們安心走吧,走吧!田畝,女人,我樣樣都伺候得好好的。」
「要比狗日的四黑子伺候得好!別他娘的光調戲不耕地!」
黑狗揮揮手道:「走吧走吧,你們只管平平安安地發財去吧!」
陸陸續續幾天間,台上人家就走了大部份,有些全家都出門去了,房子一把鎖便鎖上了。台上的雞狗成群地在禾坪菜園裡撒歡,飛上稻草垛,幾日便有了頹敗之勢。春雨裡,那些無人踩踏的屋簷下台階上,迅疾地衍生出一層絨絨的青苔。潘渡依然只剩下老人和上學的孩子,長河邊的村莊,寂寥得連歷慣風霜的老人們都覺出了荒涼,老祖母說,她這輩子從沒看過台上人家會這般稀少,越來越少了。
然而,生活還在繼續,驚蟄一到,土就動了,天空轟隆隆地春雷。二月裡是神社日。二月初一「曬土地」老人們組織了一個香火社,原野上的土地廟,紅布神龕上蒙著的一尊眼睛咪咪鬍子老老的土地菩薩,一村的孩子都來給土地爺磕頭了,乞得智慧和福氣。也保佑潘渡今年的收成會風調雨順。二月十九日,要拜觀世音菩薩。鑼鼓香火裡,村莊漸漸地從離別的傷痛裡緩了過來。春雨裡有農夫披著蓑衣,趕著牛下田耕地去了。豌豆花開了,紫朦朦地鑲在油菜花海裡。勞作了一個新年的媽媽,這回獨自一人清清爽爽地乘船回下江娘家去了,她要去接外婆來家裏住些日子。
爸爸在飯桌上對兒子說:「今年,我們家可能要種大約六七十畝地了。別人家扔下荒廢了的地,爸爸都揀起來種。全部種黃麻和棉花。」
爸爸說:「我要騎著摩托車,去城裡馱化肥回來。」他對霄霄和喬喬說:「你們倆個就坐在前面。嘟嘟嘟—–」
「我要買水彩筆,圖畫冊。」霄霄文靜地垂著眼皮說。
喬喬問道:「如果媽媽也想去呢?」
爸爸笑瞇瞇地:「就讓她一個人在後面走著好了。」
夜晚,霄霄和喬喬騎在桑樹的枝椏上。過年時熱鬧喧嘩的潘渡,人家的燈火只亮起一小半。許多的房屋都黑黝黝地靜立在台上。兄弟兩個躺在樹枝上,心裏依然覺出一些淒清的涼意來。喬喬說:「霄霄,我一點都不想上學了,你呢?」
霄霄因為成績好,在這一個問題上是很勢利的。他思考了一下,回答說:「我覺得,學是一定要上的。不上學,這麼小,能做甚麼呢?」
喬喬說:「我想在家裏幫爸爸下地幹活。我喜歡玩。」他興奮地憧憬,天就該溫暖起來了,在花海般的田野上,香暖的春風吹拂,綠茸茸的莊稼,水田埂下隨便掏一個洞,就能捉到泥鰍。夜裡提著馬燈去捉青蛙,呱呱呱呱!不用上學,該多麼自由!
喬喬說:「我打算養一棚鴨子,像念珠兒家一樣。」
霄霄說:「可是你的鴨子會和她的鴨子搞混。一搞混的話,她就要罵你了。說不定要拿竹篙把你的鴨子拍個半死。」他一想起念珠兒來,就心有餘悸地搖著腦袋:「我最怕那個爛嘴巴丫頭了,她簡直越來越會罵人了。」
喬喬滿不在乎地搖搖頭:「不要緊,她要是罵我,我就罵她。」
霄霄很不屑地對弟弟說:「你怎麼可能罵得贏她呢?」
喬喬說:「慢慢就罵得贏了。」他揚揚拳頭,說:「她很怕我打她的。」
霄霄聽到這句話,出了一會兒神,半響他才說:「總之,我和誰都不喜歡相罵,也不喜歡打架的。不管打贏了還是打輸了,心裏終歸覺得很難過的樣子。我就想上學讀書,將來考上大學。」
喬喬敏感地說:「可是,爸爸說大學都是在大城市裡的。大城市裡的人是很欺負人的,他們動不動就會打你。」
霄霄像一個胸懷抱負的人那樣,寬容而溫和地一笑:「不會的。上大學的人是有用的人才。只有像爸爸這樣進城打工的農民,才會被他們欺負。」因為爸爸的遭際,城市這個名詞,早已經傷害了孩子的心靈。他並不喜歡像城市那樣的地方,感覺那裏高樓入雲,寬闊的街道和人群都有著毫無溫度,冰涼的喧囂,人山人海。然而,那裏還有大學,圖書館,天文館,是他小小的閱歷裡渴望抵達的地方。
「那你要去哪兒上大學呢?那你豈不是要一直一直讀書,十七八歲了還在讀書?鬍子都長長了還在讀書?」
「我將來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上大學。然後,去很多很多很遠的地方。」他還想對弟弟說,等他走遍了世界以後,他就會回到潘渡來,和弟弟,爸爸媽媽,老祖母,一起過著相親相愛的生活。然而,那時候,老祖母還會活在人世麼?即便他只是一個孩子,也領略得到人世無常,生和死的相近。死亡就是,祖母不再在家,她睡到村子西頭的墳地裡頭,一捧黃土是她永遠敲不開的門。永遠……想到這裡,孩子的心瞬即地碎了一下,他的眼淚漫漫地蒙住眼眸,遮蔽了咽喉裡的聲音。然而,月光下望過去,他只是靜靜地靠在樹杈間,雙手攀著樹幹,雙腿習慣地架著二郎腿,文靜的小小書生,初具美雅的風度。
喬喬對哥哥這些洶湧的心理活動毫無察覺,他只是滿目欽佩地望著哥哥:「反正,我的成績不如你,要是讀書讀到那麼大,早就被老師打成癟癟的殘廢人了。我長大了也不會進城打工。我就一直住在潘渡。」他計劃道:「我先養5隻鴨子,滿十歲了就養20只,長大了,就養500只。」
小兄弟倆還討論了一個很是羞澀的問題。霄霄認為喬喬如果一生都留在台上,又和念珠兒一起玩,一起放鴨子的話,長大了,怕是只能娶念珠兒這麼一個凶丫頭當堂客了。喬喬的臉紅紅的,他嘻嘻哈哈地笑起來,可是心裏卻已經做出了讓步:真到了那個時候,希望念珠兒不要那麼會罵人就好了。
這長河邊絮語的一對小兄弟呵,沒有人聽見他們的說話。連念珠兒也不曉得她正在被隔壁家的小男孩打歪主意呢。村莊睡著了,長河睡著了,只有他們躺著的樹枝上翠綠的葉苞,只有春風吹著漫野的油菜花的香,只有深藍的天空上滿天的繁星,眨巴著眼睛,閃爍著光芒,溫柔無語地陪伴。(全文完)#
責任編輯: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