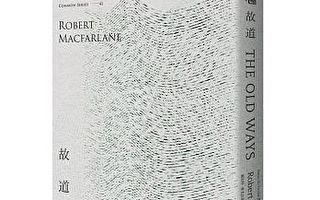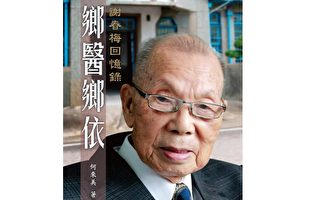(續前文)
過了一段時間,我收到維富先生寄來的信,信中語氣委婉,表示很不幸目前倫敦動物園基層職員並無缺額,不過如果我願意的話,協會在惠普斯奈(Whipsnade)的鄉間動物園倒需要一位實習生。
接到這個消息,比聽到他打算送我一對正值繁殖年齡的雪豹還令我雀躍。
幾天後,我懷著筆墨無法形容的興奮情緒前往貝德福郡,只帶了兩卡皮箱,一個塞滿舊衣服,另一個裝滿博物史書及無數肥厚的筆記本,以便記錄我在照顧動物時的每一項觀察心得,以及從同事們嘴裡吐出來的每一句金玉良言。
十九世紀時,偉大的德國動物商「哈根別克」創造了全新的動物園型態,在他之前,每隻動物都被塞進設計差勁、極不衛生、柵欄密不通風的牢籠內,一般人看不清楚這些動物,動物本身也很難在這種令人作嘔的集中營式環境生存下去。
對於該如何展示動物,哈根別克有一套全新的想法;他不用鐵條橫陳的陰暗地窖,而是給予動物光線與空間,還有人造假山與假石,任牠們攀爬,再用乾的或注滿水的壕溝將動物與民眾分開。
這對當時的動物園權威來說,簡直是異端邪說,他們駁斥這樣做太不安全,因為動物一定會爬出壕溝,就算不爬出來,也會統統死光,因為眾所皆知,若不把熱帶動物關在空氣不流通、細菌叢生的高溫、高濕度的室內,牠們就會立刻死掉!——至於隨處可見熱帶動物日益消瘦或死在這類土耳其浴牢籠裡的情形,權威們卻絕口不提。
後來這批人都跌破了眼鏡,因為哈根別克動物園的動物們個個活得生氣蓬勃,在戶外畜欄不僅健康狀況改善,甚至成功繁殖出下一代。
一旦哈根別克證明以這種方式不僅能圈養出更健康、更快樂的動物,而且還能提供民眾更精采的動物表演,全世界的動物園立刻跟進,紛紛效尤。
惠普斯奈其實是倫敦動物園想超越哈根別克構想的嘗試。協會買下坐落在鄧斯特布爾山丘(Dunstable Downs)上的廣大農場,投下巨資,讓所有園內動物都生存在盡可能接近其自然環境——也就是在遊客眼裡像是自然環境——的狀態中;獅群有森林,狼群有樹林,羚羊及其他有蹄動物則擁有連綿起伏的廣袤草原。
對當時的我而言,去惠普斯奈幾乎就等於去非洲,因為政府提高稅金,逼得大批貴族改行當動物園園主的時代尚未來臨(工黨執政後,對富豪、大地主苛稅,擁有大片土地的貴族無力負擔,紛紛開放莊園,豢養各種野生動物,作為獵場或動物園,一時蔚為風潮,少數幾家現在仍存在)。
等我抵達惠普斯奈後,才發現那是一個極小的村落,只有一間酒吧,和寥寥幾座鄉村小屋,慵懶散立於榛木雜樹林覆蓋的山谷之間,我先到出納室報到,留下皮箱,再前往行政區。
孔雀拖著長尾巴晶瑩閃爍地橫過綠草坪,主車道旁的松樹上懸掛著一個巨大無比的鳥巢,彷彿樹枝推成的乾草堆,巢邊棲滿吱吱喳喳、不斷尖叫的奎克長尾鸚鵡。
我走進行政區,被帶進園長畢爾隊長的辦公室。
他只穿著休閒襯衫坐在裡面,搭配一套極搶眼的橫紋吊帶褲,面前的大桌上疊羅漢似地堆滿各類文件,大部分看起來嚇人地正式,如科學報告一般,還有一堆正好蓋住電話。
隊長起身後,一眼望去他是個身高與肚圍都超乎尋常的男人,加上一顆光禿禿的腦袋,配著一副鐵邊眼鏡,嘴角彷彿總在打量似地下撇,看起來簡直就跟漫畫裡的比利·邦特(Billy Bunter,英國知名漫畫人物,是個總是惹禍上身的高胖小學生)一模一樣。他緩緩地繞過桌子踱到我面前瞪著我,鼻息沉重地朝我噴著大氣。
「杜瑞爾?」
他突然開砲一樣盤問我。
「杜瑞爾?」
他的聲音非常低沉,有點像遠方傳來的乾雷。很多人在西非海岸待了幾年之後,聲音似乎都變成那樣。
「是的,長官,」我說。
榮耀的獅子
看啊,那溫文儒雅的獅子!
——喬叟《良善婦女的傳說》(Geoffrey Chaucer, Legend of Good Women)
當我聽到要從獅子區開始工作,的確有點震驚。我安慰自己幸好當時沒立刻露出不安的表情,但心裡巴望著自己能從比較溫馴的動物著手,例如一群眼眸如夢似幻的鹿……
在一名新人對工作還完全陌生的情況下,就硬往一大群獅子堆裡塞,似乎有欠公平。不過我裝作漫不在乎,逕自前往新的工作區。
我發現該區地處小山丘頂,藏在一排接骨木樹叢和高高的蕁麻叢後。樹叢隨山坡緩緩下降,直到與山谷銜接處戛然而止,再由無數簇柔軟的綠草取代,每簇都像一頂經過兔子囓咬過的假髮,正好庇護草叢下方的螞蟻窩。
這裡視野極佳,可以鳥瞰從山腳迤邐濃橫過整片山谷如馬賽克般的鑲嵌田野,彷彿千百片用粉蠟筆塗過的色塊,在巨大的雲朵陰影行進下不停變幻色彩。
這區的神經中樞是一間搖搖欲墜的小茅屋,屋外圍繞著一片轇轕無垠的接骨木樹林。小屋俏皮瀟灑地戴了一頂忍冬假髮,幾乎完全遮住兩扇窗戶,室內因此總是一片陰暗。屋外掛著一面破爛的布告欄,上面寫著小屋的雅號:安憩園。
屋內傢俱的簡樸可媲美僧院:三把朽壞程度不等的椅子,一張搖搖晃晃、一搬東西上去就像匹受驚的馬會前仆的桌子,再加上一座極醜怪的黑爐子,蹲在角落裡不停從兩排鐵齒中間往外吐煙和大量反芻木炭餘燼。
我就是在這間陰暗的小屋內找到負責本區的兩名管理員:傑斯是個紅臉寡言的人,毛茸茸的白眉下有一對凶狠的藍眼,鼻子的顏色和肌理都酷似一粒巨大的草莓;喬正好相反,棕臉、閃閃發亮的藍眼、沙啞富感染力的笑聲,全身散發著一股詼諧感。
他們吃完被我打斷的早餐後,傑斯帶我參觀全區,向我介紹園內動物及工作內容。區內一端養了一隻名叫彼得的袋熊;接下來的兩個獸欄,一欄養了一群北極狐,另一欄養了一群狸;然後是熊欄,裡頭有兩團大白球似的北極熊,還有養著一對老虎的虎穴。
順著山勢往前走,是另一個住了一對老虎的圍場,最後才是本區的代表動物:獅子。
我們沿著蜿蜒狹窄的步道穿過接骨木樹林,終於來到圍繞獅籠的高鐵絲網前。獅籠占地兩畝,建在山坡頂上,籠內長滿矮樹叢與高矮樹木。傑斯帶我順著欄走,一會兒看見一叢矮樹蜷成一個小谷,一會兒看見一片圍繞水池的茂密草原,獅子們就躺在一株根瘤盤結的火棘樹下,形成一幅絕妙的圖畫。
雄獅艾伯躺在淡白色的陽光下,裹著自己的鬃毛,正在沉思冥想,身旁倚著牠兩位胖嘟嘟的金黃色妻子(南與姬兒),兩隻都睡得正香,湯盤似的大腳掌不斷輕輕抽搐。
傑斯大喊牠們的名字,並用一根樹枝敲鐵絲網,要牠們過來跟我見面。艾伯僅將頭轉過來幾秒鐘,投來一個令人畏縮的眼光,又回頭繼續沉思;南和姬兒連動都沒動。牠們看起來一點都不凶野,反而似乎體重過重又懶惰,而且太驕傲。
傑斯打開兩腳,彷彿站在不停搖晃的甲板上,開始用力咂嘴,同時用他的藍眼狠狠地瞪我。
「現在你給我聽好,小夥子,」他說:
「聽我的話,就不會犯錯。那邊的袋熊、狐狸和狸,你都可以進牠們的籠子,懂吧?可是其他的,千萬不可大意,否則就會被吃掉!牠們或許看起來很溫馴,其實全不是這回事,懂吧?」
他又咂咂嘴,同時觀察我是否把這段訓話聽進去了。我向他保證,除非我真正跟動物熟起來,否則絕不會掉以輕心。我感覺(當然沒說出來)若沒經過正式介紹就被獅子吃掉,豈不有點「沒面子」。
「嗯,你聽我的準沒錯,小夥子!」
傑斯又重複一遍,彷彿預報凶兆似地用力點頭:
「我會好好教你!」
頭幾天我忙著學習,牢記餵食、清掃及其他雜務的程序,這些工作都非常簡單而且規律,一旦上手後,便有較多機會觀察被我照料的動物,研究牠們的習性。我會隨身在口袋裡塞個大筆記本,碰到任何小事都立刻拿出來記錄,傑斯和喬都覺得很有意思。
「跟他××福爾摩斯一樣,」傑斯這麼描述我:
「老是記些鳥事!」
喬喜歡耍我,愛描述一些他目擊到的既冗長又複雜的動物行為,不過他的想像力太天馬行空,吹過頭的很快就被我識破。
很自然的,我的研究先從獅子開始。
既然首次與這種猛獸親密相處,我決定閱讀所有找得到有關獅子的文獻,然後和自己的觀察互相印證。
不出所料,我發現大概再沒有另一種動物(除了神話動物以外)被人賦予更多莫須有的「美德」。
自從不知哪一位完全不懂動物科學、卻對動物充滿熱情的人,封獅子為「萬獸之王」後,舞文弄墨者便互相角逐,不斷提出獅子此名的證據,尤其是古代作家,更異口同聲讚美Felis leo(編注:拉丁語中的「獅子」)的各種性格:溫柔、睿智、勇氣與運動家精神。難怪獅子會被羞怯又謙遜的英國人選作民族象徵。
然而和艾伯與牠兩位太太短暫相處之後,我卻立刻發現真正的獅子跟那些作家的胡謅完全是兩碼子事。
我在普林尼約於一六七四年出版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中發現以下一段有關「萬獸之王」的有趣記載:
「萬獸之中唯獨獅子,凡臣服在牠面前者皆以溫文待之,不予碰觸;凡在牠面前五體投地者,皆寬恕其生命。
逢其凶性大發,盛怒之餘,必將怒火先發洩於男性身上,再轉向女性。除非飢餓至甚,否則從不擾食嬰兒。」
我曾拜讀的另一位古代作家是珀切斯,他以從未目睹獅子的滿滿自信,向我保證「寒帶獅子較溫和,熱帶較凶猛。」
讀後我開始對和艾伯建立友好關係寄予極大的希望,因為我一抵達惠普斯奈之後,天氣立刻轉冷,冰刀似的狂風掃過山丘,令那幾叢其貌不揚的接骨木樹林互相傾軋,不斷呻吟顫慄。根據珀切斯的說法,在這樣的氣候裡,艾伯和牠的伴侶應該都像友善的小貓咪到處嬉耍才對。
隔天我對珀切斯的信心便完全粉碎——當時我迎著強風哈腰弓背,皮膚發青,經過獅籠,想趕回溫暖的「安憩園」避風。艾伯藏在獅籠中靠近步道、覆滿長草與蕁麻叢的角落裡。
我確信,稍早牠一定有看見我走過,決定要在我回來時給我個驚喜。牠一直等我走到牠正對面,才突然飛身一躍,撲到鐵欄上,同時發出令人汗毛直豎的憤怒嗆咳聲,接著弓身蹲下來盯著我看,黃色的眼睛因為我的驚慌而充滿惡意的促狹。
牠顯然覺得這個惡作劇很有趣,當天又玩了一遍。再一次,牠很得意地看著我像匹受驚的馬倏地跳起來,而且這一次他還樂加一等,眼睜睜看我拋出手上的水桶,跌了一大跤,重重摔進一叢長得特別肥美的蕁麻裡。
我因此發現,冷天不僅不會讓艾伯變得溫和,反而讓牠更瘋瘋癲癲,老愛躲在矮叢後面,冷不防地跳出來驚嚇那些正好路過的老太太;我猜想大概因為這項運動在天氣寒冷時有助於血液循環吧!◇(節錄完)
——節錄自《我鐘樓上的野獸》/ 木馬文化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