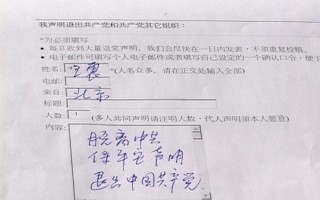【大紀元3月12日訊】我畢生難忘這一天: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我也難忘這一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在這兩個日子中間,整整六十四天,我失去自己的姓名和人格,僅僅剩下這副皮囊和呼吸,成為被關在籠子裡的活物。
一輛吉普車把我送到西村監獄,一位中年軍官把我帶進一個辦事間後就走了。辦事間裡有兩張辦公桌,靠牆一個大檔案櫃,一個軍官給我辦理『入住』手續。和住醫院或住賓館不同,我沒有行李,但必須取下隨身帶著的自來水筆、手錶和穿在腳上皮鞋的鞋帶。取下就取下罷,我倒無所謂,筆和錶這時對我毫無用處,鞋帶屬於繩索一類,本來就是用來捆綁東西的。我不是東西,是人,也教人用繩索捆綁螃蟹似的,捆個結實,剛才在警備司令部才解開,現在把鞋帶拿走,也好,解除束縛嘛。
只是,要我把褲子上的皮帶也拿下來,哪可不行﹗我覺得受到侮辱,拿掉皮帶,褲子還怎麼穿,難道整天用手提著?那辦事的軍官看看我的登記表,微笑著向我解釋道:『你是個知識分子,道理應當可以明白。入獄的人,身上的所有繩帶,都必須取下來放在這裡保管。我們信任你,不會在監獄裡亂來,但你無法保證,其他的人不會把你的皮帶拿去幹壞事﹗比如,用皮帶自殺。』而且說這是歷來就如此的『獄規』。
取下皮帶我勉強可以接受。又因為軍官提到『入獄』、『監獄』及『獄規』等詞語十分刺耳,我不假思索即予回駁。是和你穿一樣軍裝的張代表把我弄到這裡來的,既無拘留證,又無逮捕證,更無法院判決書,我能算『入獄』嗎?
軍官好像不屑與我辯論,一本正經地向我當面宣佈三條紀律:一、不得告訴他人我原來的職務和工作單位;二、在囚室裡不得與他人談及自己的案情;三、不得把自己的真實姓名告訴任何犯人,只須記住自己的編號是一一O八。我真正感到忿恨和痛心,從這一刻開始,我連使用真實姓名的基本權利也被剝奪了﹗讓我記住一個號碼,豈不是要我的命。誰都知道我最大的弱點就是數學盲,兩位數還好些,三位數重複多次勉強可以記住,三位數以上,毫無辦法。直到現在,我可以記憶起從前許多人和事,甚至某些細節,就是記不住自己家的電話號碼。心裡一急,沒想到卻急出一點智慧來。一一O八,後面兩位數,不是正巧與我的名字同音嗎?當時一下子就記住了,到現在也沒有忘記。
獄警帶我走進一條陰暗的甬道,光線從甬道盡頭高牆的小窗口投射進來,我的眼睛不能適應,勉強可以看到兩旁是一式的矮門,一律上鎖,我猜想是兩排監倉。走到左邊最後一個矮門,獄警開了鎖,突然問我:『有你認識的人嗎?』我掃了一眼,監倉裡已有四個人,一律背心內褲,席地而坐,臉無表情。我說:『沒有。』獄警又問監倉裡那四個人:『你們有人認識他嗎?』四人同聲答道:『不認識。』然後,叫我進去,隨手從外面上鎖。我心裡覺得好笑,都說不認識,住進來不就認識了嗎?多此一舉。
這間監倉不到十平方,靠後牆的一半是略高於膝蓋的平台,另一半地板上墊了一塊木板。後牆高處一個加了鐵柵欄的小窗,天花板上一只二十瓦電燈泡,監倉門上端開一小圓孔,下端開一個大一點的方洞,每天兩頓飯就從這個方洞送進來。門旁角落,放一隻木馬桶,大小兩便都用它。每天傍晚輪流一人出去倒馬桶,都有獄警監視。
隨著外面上鎖的聲響,我的腦子突然空白了。我這副皮囊,呆呆地倚牆而立,如果不是還有三寸氣在,儼然一條僵屍。大約有三十分鐘,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甚麼,只覺得有一股無名的情緒,似冰似火,似潮似涌,亂流一般,在周身亂竄。
正不知如何控制自己,忽然矮門外有點動靜,又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同室中年紀最輕的那位『紅衛兵』說:『開飯了﹗』果然,飯菜就從矮門下端的小方洞送進來。我最後一個接過飯菜,是一個兩寸高的黑釉粗瓦盆,剩著米飯和水煮冬瓜。肚子實在餓了,靠牆坐下,埋頭就吃,沒幾下便完事。甚麼味道倒也沒有很深的印象,只覺得如果再來一份,完全有能力打發。二十分鐘左右,粗瓦盆又從小方洞送了出去,自己不必麻煩。監獄裡的第一頓飯,就這樣平淡無奇地嚥下去了。
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兩個年輕人。一個是剛才說『開飯』的那一位,十六七歲,開朗活潑,東北口音,我猜想他可能是中學紅衛兵頭頭,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另一個瘦瘦高高,十九歲上下,一直靠在矮門邊站著,愁眉苦臉,兩眼閃著淚光,一份飯菜,只吃了不到一半。我有意在他身旁坐下,輕聲問道:『沒胃口?』他低著頭,輕輕用廣東話回我一句:『無胃口。』我又輕聲勸他說:『無胃口也要多吃一點。如果不吃飯,身體搞垮了,將來出去半條命,還怎麼工作?』
忽然從監視孔傳來一身警告:『不許亂說亂動﹗』我回答道:『我勸他吃飯沒有甚麼不對罷?』監視孔外的人不再說話,我也給他一點面子,不再說甚麼了。我的判斷大致不錯:從踏入監獄的大鐵門到吃完第一頓飯,沒有見過一個警察,說明監獄已經被軍管會接管了。我所在的監倉,連我在內一共五個人,都是『新人』,沒有一個『老犯人』,說明監獄是臨時為我這樣一類人設置的。這位瘦瘦高高的青年慢慢也不再那麼憂鬱了,飯也吃好了。他悄悄告訴我,他是省體育工作隊的跳高運動員,比賽得過獎牌。因為家庭出身是資本家,兩派對立,他被打成『狗崽子』,軍代表把他抓到這裡來,心裡很委屈。一個月後,他就出去了。臨走,還拉一拉我的手。
那位中學紅衛兵頭頭,說話不多,該吃就吃,該拉就拉,一切都無所謂。我隱約感覺到,他有一種近乎習慣了的優越感,不自覺的流露出來。許多中、高級軍官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不知不覺從父母的軍銜、用小車接送,慢慢養成以『爸爸官大為榮』的習性。小朋友之間有些小糾紛,開口就是『我爸比你爸大』。紅衛兵運動興起不久,這種『優越感』迅速膨脹,很快就發展成一種暴力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甚至還有封建色彩特濃的順口溜:『龍生龍子鳳生鳳,老鼠生仔會打洞』。一副軍裝,一條皮帶,從學校打起,打遍全社會。只有他們最革命,別人都是牛鬼蛇神。
後來鬧得太兇,打死很多人,內部又發生分裂,互相動武,又打死了不少。才不得不用軍隊這個正規的暴力集團,以暴鎮暴,將紅衛兵運動壓了下去。與我同囚室的這位紅衛兵頭頭,到我出獄的時候,仍然關著。我想,他的老子可能是高官,把他關在監獄裡,保護多於懲罰。
小小囚室,不到十平方,卻是相當標準的牢籠。兩頓飯之外,規定的功課,是早晚各一次的革命儀式:早請安和晚請罪。所謂早請安,就是起床後的第一件事,集體立正唱《東方紅》,然後是同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接下來是朗讀《毛語錄》,兩急實在忍不住了,可以臨時通融,到角落的馬桶去解決。不過,在小小的籠子裡,莊嚴的儀式和見不得人的方便同時進,未免有點滑稽。晚請罪在臨睡前進行,將《東方紅》換成《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他照舊,沒那些雜七雜八的事,做起來就方便些。在外面做這兩次儀式,必須高掛毛主席像,加上黨旗國旗,佈置一個『三忠於』的莊嚴環境,大家面對毛主席像,唱歌跳舞讀語錄,嚴肅認真,一絲不苟。這裡是監倉,總不能把毛主席也請進監獄罷。但沒有毛主席像,又覺得失去目標,向誰早請安,向誰晚請罪,誰都說不清。
籠子裡的人數有增有減,很快就有增無減,二十天後,竟然增加到十一個人。我估計,外面正大肆抓人,籠子裡豈止『人滿為患』,簡直是擠壓如沙丁魚。白天磕磕碰碰,已經十分難堪,排隊蹲馬桶,更是一大難題。晚上睡覺,側身個挨個還是躺不下來。好在大家同一籠,共犯難,很快就互相同情,互相溝通,互相貼近,互相體諒。協商結果:讓多數人睡得好些,三個人站著,每隔兩小時左右輪換一次,總算解決了睡覺問題。
小籠子裡關著十一個人,倒使我想起小學時一道『雞兔同籠』的算術題。當年的『雞兔同籠』,在於訓練小學生加、減、乘、除的初級數學頭腦,只是這種數學頭腦,根本無法理解當代『雞兔同籠』的悲哀。同籠中一位河北漢子,首先揭開悲哀的序幕。
他在絕望的時候說:『諸位戰友,如果將來有誰能夠出去,請記住我,把我的事也帶出去!』我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他稱呼我們為戰友,我也把他視同戰友,至於姓名,並不重要。
戰友四十來歲,轉業軍人,廣州沙河一家百貨公司的副經理。兩大派武鬥期間,公司為了保衛自己的安全,推舉他出來主持防禦工作。他組織公司裡同派的人,在大門口和臨街二三樓窗下,堆起沙包,構築起簡單的防禦工事,並通過他與原先部隊的關係,弄來一些槍枝彈藥,使該地區對立一派的武鬥隊,不敢輕舉妄動,這家公司自然成為本地區一個相當突出的『據點』。戰友作為這個防禦據點的頭頭,就被他們單位的軍代表關進籠子裡來了。
進籠之初,戰友非常樂觀,勸大家吃好飯,睡好覺,耐心等待,沒甚麼大不了的事。他常說:『沒打人,沒殺人,怕甚麼!』有一天,戰友被從籠子裡提了出去,臨走還笑著和大家擺擺手。我在心裡為他能這麼快出籠而高興。
第二天傍晚,戰友又突然回籠了。我發現他衣衫破損,臉頰瘀腫,神情十分疲憊,估計他可能『受刑』了。他一言不發,倚牆站著,陷入沉思。我半夜醒來,見他依然站著,就讓出一點地方,輕聲說:『你也躺一會兒罷。』他仍然站著,陰沉的說:『我判斷錯誤。』
過了兩天,戰友又從籠子裡被提了出去。和上次一樣,他臨走時笑著向大家擺擺手。一連三天不見戰友回籠,我估計,戰友已被轉移到別的籠子裡去了。
第四天中午,戰友又回籠了。不過,他的出現,使大家感到意外,還大吃一驚。他不僅衣衫被撕破撕碎,臉和脖子傷痕累累,皮下瘀血,腫脹得都變了形,幾乎認不出來了。戰友靠牆坐著,半天才用嘶啞的嗓音說:『我不服﹗死也不服!』
隨後,我漸漸了解:戰友被他們單位的軍代表提出籠子,交由群眾批鬥。罪名臨時由批鬥的人定,『挑起武鬥的壞頭頭』、『搶劫糧食的土匪』、『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份子』等等,都是當時的『時髦罪』;批鬥的方式也是當時的『流行式』,掛牌、罰跪、毆打。一連批鬥三天,一塊十多公斤重的木牌,用細鐵絲拴住,掛在戰友的脖子上,鐵絲都快吃進皮肉裡去了。這還不算,有人還用特製的竹刀,砍他的頭,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完了,又放回籠子裡。甚麼時候需要,就和殺雞宰兔一樣,再從籠子裡提出去。
我完全能夠體會戰友的感受。在這個意想不到的年代,人性是如此脆弱,獸性又是如此猖獗,只要手裡有權,就可以堂而煌之地打出『革命』的招牌,幹盡傷天害理的勾當。我堅信自己不是雞兔(禽獸),是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一個人,即使無法對社會做出貢獻,起碼不能害人。如果連人性都丟掉了,還有甚麼本錢做人?
戰友的遭遇,引導我作痛苦而不斷的沉思。我意識到處境的險惡,應該向妻子做個交代,讓她知道某些真相。因此,我找到一個當時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讓妻子給我送《毛主席語錄》。這一招果然靈驗,我的信經監獄管理軍官檢查後順利寄出,不久,妻子就找到監獄來了。
這是唯一的一次『籠中會』。妻子在收到我的信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已被關在西村監獄,親人生死未卜、下落不明的痛苦牽掛,是可以想象的。
一知道我的下落,她首先想到的是我的腰痛病,尤其時近中秋,天氣漸涼,一定要注意保暖。她帶來一個大包袱,棉被和秋天的衣物全有,面上還壓著一套紅塑膠皮燙金的《毛澤東選集》和一本小《語錄》。
妻子來探監,完全按照『監規』進行。我被獄警帶出來時,妻子已經坐在長方形大桌子的一頭,見我走近,妻子立即起身要過來,但被獄警輕聲喝住了。我和妻子面對面坐在大桌子的兩頭,獄警就站在旁邊。如果不是這種特殊的場景,我肯定會緊緊擁抱自己的妻子。見到坐在面前的妻子,還是那麼善良,那麼溫柔,那麼美麗,本來準備好一些很重要的話,都變得多餘了。我定定地看著妻子兩只非常漂亮的大眼睛,用平和的語調說:『我住在這裡還不錯,能吃也能睡……』沒等我說完,妻子就把話接過去說:『我看到了,我明白,你放心。我會把孩子照料好,還需要甚麼,告訴我,一定給你帶來。』
聽了妻子這些話,看到妻子眼睛中流溢的光彩,我胸中的閘門頓時打開,愛的激流奔騰而出。見面只有短短十幾分鐘,但妻子給我的激勵,使我走過坎坷的人生。夜深了,籠子裡雖然擁擠,卻也十分安靜。我躺在牆角,輾轉反側,腦子裡放著『籠中會』電影,一遍又一遍,永遠是那樣動人。
我和妻子都是極平凡的人,就像兩塊不起眼的小磁鐵,一次偶然的巧合,碰撞出愛的火花,就互相吸引住了。沒有甚麼神秘的力量,僅僅是與生俱來的這副人的秉性。十多年來,我和妻子閱人極其有限,但能深切感受到人性的脆弱。尤其是由某種『邪說』煽動的無端仇恨,把一批又一批懷有私心的人,變成兇惡的虎狼,殘害一波又一波無辜的生命。我們驚慌,我們恐懼,我們試圖躲避,我們在絕望中掙扎。我們口中也唱著那支歌:『不靠神仙和皇帝,要靠自己救自己。』但我們不知道,最終能夠戰勝『仇恨』的力量,不是天上的大救星,而是自己與生俱來的人性。
籠中無意聽說今年有閏八月,就是說,我會在籠子裡度過兩個中秋節。只是籠中既無明月,又無月餅,月圓人不圓,徒增許多傷感。到了十月一日,吃晚飯的時候,水煮冬瓜忽然加了幾粒豬油渣,才想起國慶節。兩個星期之後,我被提了出去。僅僅由於結算伙食賬,使我明白兩件事:一,坐牢要交伙食費;二,伙食賬結清了,大概不會再回籠了。
7/11/03(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