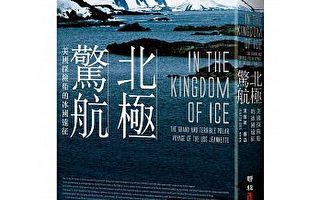一堆燒得很旺的小火苗展現在我眼前,它點燃了我回憶起來的一切情景和事件,將它們燃燒,化為烈焰;如果火舌捲不著它們,不能把它們燒毀,使它們變作焦炭的話,那麼,抖動的火苗也會把它們遮掩住的。
於是,我嘗試另開一個頭,想像自己來到布雷肯瓦爾夫,南森狡黠地眨著他的灰眼睛,幫助我整理我的記憶。
他把我的目光引到他身上去,討好我似地從畫室裡走出來,穿過花園,向他經常描摹的百日草走去,慢慢走上大壩。天空中一道沉鬱而刺眼的黃色,偶爾被陰暗的藍色劃破, 南森拿起望遠鏡,向魯格布爾方向望了一眼,拔腿就跑回家去,躲進屋裡。
我差不多已經找到了一個頭緒。
這時,窗戶被人推開,南森的妻子迪特跟平時一樣,遞過一塊點心來。
許許多多往事,一下子呈現在我眼前:
我聽見布雷肯瓦爾夫學校的一個班級在唱歌;
又看見一個小小的火苗;
聽見父親夜間動身的聲音;
外鄉孩子約塔和約普斯特鑽在蘆葦叢中嚇唬我;
有人把畫家的顏料扔進水坑裡,水坑像鮮艷的橙子似地閃閃發光;
一位部長在布雷肯瓦爾夫發表演說,父親向他致敬;
掛著外國汽車牌號的大型轎車停在布雷肯瓦爾夫,父親也向它們致敬;
我躺臥在倒塌的磨房中,在南森的作品隱藏的地方,夢見父親用繩子拴著一團火,鬆開頸圈,並且命令這團火說:「搜!」
這一切交織在一起,盤根錯節,愈加混亂,直到科爾布勇警告的目光突然向我掃來。
於是, 我竭盡全力整理我那縱橫交錯的記憶,擺脫了那些次要情節的糾纏,使一切清晰地顯現在我眼前,特別是我的父親和他履行職責時的歡樂——我也做到了這一點,把所有關鍵人物都集合在大壩下,排成了閱兵的行列,正要讓他們一個個走過我面前時,突然,我的鄰座普勒茨大叫一聲,在劇烈的痙攣中從椅子上倒下。
這一聲,剪斷了我的全部回憶,我再也開不了頭,只好放棄動筆的打算。
所以,當科爾布勇博士收作文簿時,我交上去的是空白本子。
科爾布勇無法理解我的難處,不相信我開不了頭的苦衷。他簡直不能想像,我記憶的鐵錨竟然找不到定錨點,鐵鏈繃得那樣緊,卻只是虛張聲勢地發出一陣陣鏗鏘聲,至多從深深的河底掘起一團團污泥,因此無法張網以捕撈往事。
這位德語老師驚訝地翻了我的作文簿後,叫我站起來,帶著有點厭惡又疑惑不解的神情注視著我,要求我作出解釋——但他卻又對我的解釋不滿意。
他懷疑我有回憶往事和發揮想像力的善意和能力,否認我對文章開不了頭的說法,只是說:「你的樣子看起來不是那麼回事,西吉·耶普森。」並且反覆強調說,我交白卷是故意和他作對。他不信任我,硬說我是反抗,心懷敵意等等。
由於這類問題歸感化院院長負責,科爾布勇上完德語課便把我帶到藍色的管理所大樓,進入一樓樓梯旁的院長辦公室。
這堂德語課留給我的,只有因為自己的回憶雜亂無章、捉摸不定、怎麼也串連不起來而感到的痛苦。
希姆佩爾院長老是穿著一件短風衣,一條燈籠褲。他正被大約二、三十個心理學家包圍著, 這些人對青少年刑事犯問題表現出狂熱的興趣。
院長的桌子上放著一把藍色的咖啡壺,幾張不乾淨的五線譜紙,其中幾頁有他倉促創作的簡單寫景歌曲,歌頌易北河、溼潤的海風、柔中帶剛的海灘雜草、翱翔的銀色海鷗、飄動的頭巾,以及濃霧中航船急促的汽笛聲。
我們的「海島合唱隊」命中註定是這些歌曲的第一個演唱者。
我們走進辦公室後,心理學家們沉默地傾聽科爾布勇博士向院長作報告。
報告的聲音雖然很輕,但我仍能聽到他又在重複「反抗」或「心懷敵意」這類話。為了證明這一點,科爾布勇把空白作文簿交給了院長。
院長和心理學家們交換了一個憂慮的眼神,然後朝我走來。他捲起我的作文本,打了一下自己的手腕,又敲了一下他的燈籠褲,要我解釋。
我看著這些緊張的面孔,聽見身後還有輕輕的喀喀聲響,原來是科爾布勇正在拉自己的手指。見到一群人圍著我等待解釋,我覺得真是活受罪。
牆角有一扇大窗戶,窗前擺著一架鋼琴。我望著窗外的易北河,看見兩隻烏鴉在飛行中爭食一段軟軟的東西,也許是一截腸子,嚥下去又吐出來,直到這段東西落在一塊浮冰上,被一隻警覺的海鷗叼走為止。
這時,院長把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幾乎是友善地向我點了點頭,再度要求我,當著全體心理學家的面作出解釋。
於是我向他敘述了自己的困境:我如何想起了和作文題目有關的重要情節,後來思緒又如何亂成一團;我如何尋找落腳點,好由此深入回憶,但沒有找到。
我跟他講了許多人物的面孔,因為擠在一堆,分辨不清;還有各種活動穿插在我的記憶中,這一切使我怎麼也開不了頭,怎麼嘗試都終歸失敗。
我也沒有忘記告訴他,履行職責的歡樂在我父親身上是一貫的,因此,為了如實反映,我只好不加剪裁地描寫,無論如何也不能隨意選擇。
院長驚訝地,甚至也許非常理解地傾聽著我的敘述,那些有學位的心理學專家們一邊低聲議論,一邊逐漸靠近我。他們相互碰碰手臂,講了一些心理學術語:「瓦騰堡式的知覺能力殘缺」、「視錯覺」等。特別使我反感的是,他們甚至用了「認識障礙」之類的字眼。
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一切,我再也不願意在這些一定要把我研究透澈的人面前說什麼了——島上的生活我早就受夠了。
院長沉思著把手從我肩上挪開,端詳著它,也許想要鑑定這隻手是否還完整。他轉身在來訪者無情的注視下向窗戶走去,望著窗外漢堡的冬天,似乎想從那裡獲得什麼啟示。
突然,他向我轉過身來,眼皮抬也不抬地宣布了他的決定。
他說,應該把我帶進單獨囚室去,「體面地隔離起來,」不是為了悔過,而是為了不受干擾地體認到寫好作文的必要性。他給了我一個機會。
他進一步說明,一切干擾,包括禁止我姊姊希爾克來訪、免除我在掃帚工廠和海島圖書館的工作。他特別承諾不讓我受到任何外來的影響,並期望我在獲得同樣伙食配給的情況下,寫出這篇作文。
他說,只要我有需要,可以一直保持不受干擾的狀態;他又說,我應該耐心去體會履行職責的歡樂;他還說,我應當仔細思索,讓這一切像竹筍那樣,一點一滴地成長,因為回憶可能是一個陷阱、一種危險,甚至給你時間去回憶也無濟於事。
心理學家們注意傾聽著,院長則近乎友善地握著我的手。對於握手,他是有經驗的。隨後, 他讓人叫來我們喜愛的管理員約斯維希,向他交代了自己的決定,並說:
「孤獨,西吉最需要的是時間和孤獨;請注意,這兩點要確實執行。」
接著,他把我的空本子交給了約斯維希,然後把我們倆打發走。◇(待續)
--節錄自《德語課》/遠流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李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