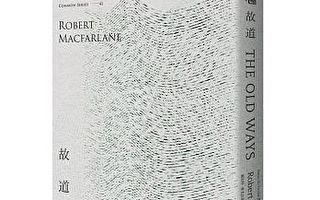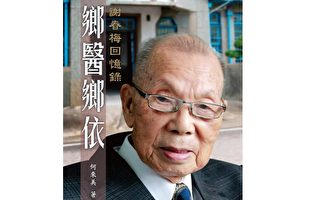(續前文)
*2
歐洲全境的燈火正趨熄滅,有生之年,我們將再也看不到燈火重新燃起。
——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評述一次大戰
*一九三九年八月,法國
薇安·莫里亞克走出清涼、泥灰牆面的廚房,踏入屋外的前院。
在這個美麗的夏天清晨,盧瓦爾河谷四處繁花盛開。白色的床單在微風中噗噗飄動,一道古老的石牆隔開了她家與道路,沿著石牆綻放的玫瑰輕輕顫動,如盈盈笑語。一對辛勤的蜜蜂在花叢中嗡嗡飛舞,遠處傳來火車啪嚓啪嚓的聲響,然後她聽到小女孩甜美的笑聲。
蘇菲。
薇亞微笑。她八歲大的女兒八成衝過家裡,纏著爸爸跑跑跳跳,父女兩人忙著準備星期六的野餐。
「妳女兒是個小暴君。」
安托萬邊說邊從門口露面。
他朝著她走來,塗了髮油的頭髮在陽光下閃爍著漆黑的光澤。他今早一直忙著修理家具,一張椅子已經被他用砂紙打磨得有如絲緞般光滑,他的肩膀和臉頰也蒙上一層薄薄的木屑。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五官不怎麼細緻,鬍渣粗黑,若不經常刮理,很快就會一臉大鬍子。
他悄悄伸手攬住她,把她拉近。
「小薇,我愛妳。」
「我也愛你。」
這是她的世界中最真切的事實。她愛他的一切:他的微笑、他睡夢中的喃喃自語、他打噴嚏後放聲大笑、他洗澡時大唱歌劇。
十五年前,她在學校的操場愛上他,當時她還不曉得什麼是愛情。他是她所有的「第一」——她的初吻、她的初戀、她的第一個情人。
認識他之前,她是個瘦弱、笨拙、焦慮的女孩,一慌張就口齒不清,而她經常慌張。
一個沒有母親的女孩。
現在妳必須是個大人,他們頭一次走向這棟屋子時,爸爸這樣對薇安說。當時她十四歲,雙眼哭得紅腫,難以承受心中的哀傷。霎時之間,這棟屋子從夏日的度假別墅變成某種牢獄。不到兩星期前,媽媽撒手西歸,爸爸自此捐棄父職。他們抵達時,他沒有牽她的手、沒有搭她的肩,甚至沒有遞給她一條手帕,讓她拭去淚水。
但……但是,我只是個小女孩,她說。
再也不是了。
她低頭看向小妹伊莎貝爾,四歲的小妹依然吸吮著拇指,不曉得怎麼回事。伊莎貝爾一直追問媽媽什麼時候回來。
大門一開,一個高瘦、鼻子形若水龍頭、漆黑的雙眼有如葡萄乾的女人現身。
就是這兩個女孩?女子問。
爸爸點點頭。
她們不再是你的麻煩了。
一切進展得非常迅速。薇安搞不太清楚怎麼回事。爸爸把女兒們當成發臭的髒衣服一般丟棄,把她們丟給一個陌生人。
她們兩姐妹年紀差很大,甚至像來自不同的家庭。薇安想要安撫伊莎貝爾——她真的想——但她心裡好難過,根本不可能顧及別人,尤其是像伊莎貝爾一樣任性、毛躁、吵鬧的小孩。
薇安依然記得剛開始的那段日子:伊莎貝爾尖叫哭喊,杜馬斯太太打她屁股。薇安苦苦哀求,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妹妹說,天啊!伊莎貝爾,拜託妳別再尖叫,乖乖聽她的話,但即使年僅四歲,伊莎貝爾已是個難管教的小孩。
薇安被這一切搞得心煩氣躁——喪母之痛、爸爸的遺棄、環境忽起變化、煩人的伊莎貝爾,無人可排解的孤單。
安托萬解救了她。媽媽過世後的頭一個夏天,他們兩人已形影不離。有了他,薇安得以脫逃。不到十六歲,她懷了孕;十七歲,她結了婚,成為「鄉園」的女主人。兩個月後,她小產,迷茫了好一陣子。除了「迷茫」,她不知道該如何形容那段時日。
她窩藏在自己的哀傷中,讓哀傷如蠶繭般裹住自己,無法關照任何人、任何事——哭哭啼啼、纏著她不放的小妹當然是其中之一。
但這些都已成過去。今天風和日麗,她並不想耽溺於往事。
她靠在先生身上,看著女兒跑向他們,大聲宣布:
「我準備好了,走吧。」
「好吧,」安托萬咧著嘴笑笑說:「小公主準備好了,所以我們得出發囉!」
薇安面帶微笑走回屋裡,從門邊的掛鉤上拿下帽子。她一頭金紅色的秀髮,肌膚如陶瓷般細緻雪白,雙眼像大海般澄藍,始終做好防曬措施,以防曬傷。
等她戴好寬邊草帽、拿起蕾絲手套和藤編的野餐籃,蘇菲和安托萬已經走到閘門外。薇安跟著他們走到門前的泥土小徑。
小徑路面狹窄,勉強可讓汽車駛過,直通綿延數英畝的牧草田野,處處青翠嫩綠,布滿鮮紅罌粟花和藍色矢車菊。一片片林木群聚生長。
這一帶的盧瓦爾河谷向來種植牧草,而不是葡萄。儘管距離巴黎不到兩小時的火車車程,但這裡感覺像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光客很少駐足,甚至夏季也沒什麼旅客。
偶爾有部汽車隆隆駛過,三不五時冒出一個騎著自行車的傢伙或一輛牛車,但路上大多只有他們一家人。他們家距離卡利弗約莫一英里,卡利弗是個小鎮,人口大約一千,人們頂多趁著朝謁聖女貞德時,順便經過卡利弗買點東西。
鎮上沒有任何工業,除了飛機場的工作外,卡利弗沒什麼工作機會。方圓數英里內只有這麼一座小型飛機場,而卡利弗的鎮民們也以此為傲。
狹窄的鵝卵石小徑蜿蜒穿過鎮上一棟棟古老屋舍,石砌的屋舍歷史悠久,歪歪斜斜地倚靠著彼此。灰泥從石牆上脫落,青綠的常春藤掩蓋了其後的荒蕪;雖然看不見,但始終感受得到殘破的氣息。
數百年來,彎曲的街道、崎嶇的階梯、陰暗的小巷拼湊出小鎮的風貌。肋骨般的漆黑鐵桿支撐著鮮紅的遮陽棚,陶土花盆中的天竺葵妝點著鍛鐵陽台,各色顏彩為石砌屋舍添增了生氣。
放眼望去,處處皆是誘人一看的景物:一個展示櫃陳列著色彩柔和的馬卡龍,一個粗編柳條籃裝滿了起司、火腿和臘腸,一箱箱五顏六色的番茄、茄子、黃瓜。
在這個晴朗的周末,各家咖啡館高朋滿座,男士們圍著鐵桌而坐,一邊啜飲咖啡,一邊抽著手捲的褐黃香菸,扯著嗓門高聲爭執。
卡利弗典型的一日。拉夏先生清掃他蔬食餐館前的街道,克隆奈太太擦洗她帽子店的櫥窗,一群少年你推我擠地在鎮上晃蕩,一邊踢垃圾,一邊輪流抽著一支香菸。
他們走到小鎮盡頭,轉彎朝著河邊前進。薇安在河邊一處青綠的平地放下野餐籃,在栗樹的樹蔭下鋪上毯子,從野餐籃中取出一條香脆的長棍麵包、一塊鮮濃的起司、兩顆蘋果、一些薄如紙片的火腿,一瓶一九三六年分的伯蘭爵香檳。
蘇菲跑向河邊時,薇安幫先生倒了一杯,擺在他身旁。
時光在暖烘烘、懶洋洋的日光中慢慢消逝,他們心滿意足地閒聊談笑,共享野餐。直到那天稍晚,蘇菲拿著釣魚桿跑開,安托萬幫女兒編紮雛菊花冠時,他才說:
「希特勒很快就會把我們全都捲入戰爭。」
戰爭。
最近人人說來說去總是脫離不了戰爭,薇安不想聽,尤其是在這麼一個清朗的夏日。
她一手遮擋陽光,注視著女兒。遠方的盧瓦爾河谷一片青綠,農田工整,看得出受到細心照拂。放眼望去不見藩籬,亦無分界線,只有綿延起伏的青翠田野和叢叢林木,偶爾可見幾棟石屋或穀倉。白色的野花綻放出小小的花朵,宛如飄浮在空中的丁點棉絮。
她站起來,雙手一拍。
「來,蘇菲,回家囉!」
「妳不能忽視這事,薇安。」
「我應該自尋煩惱嗎?為什麼?有你在這裡保護我們。」
她微微一笑——說不定笑得太刻意——收拾野餐,叫喚家人,帶著大家走回泥土小徑。
不到半小時,他們已經回到鄉園堅固的木頭閘門。這棟石砌的鄉間宅邸已伴隨她的家族三百年,歲月為石材蒙上十餘層不同的灰影,宅邸樓高兩層,藍色的百葉窗,從窗戶可以俯瞰果園。長春藤沿著兩座煙囪攀爬,覆蓋其下的磚瓦。
原本的地產只剩下七英畝,其餘的兩百英畝在過去兩百年中因為家道中落而逐一出售。對薇安而言,七英畝已綽綽有餘。她無法想像自己需要更多。
薇安隨手把門帶上。在廚房裡,黃銅和鑄鐵鍋具懸掛在爐子上方的鐵架,一束束乾燥的薰衣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吊掛在粗拙的屋梁。黃銅水槽因年歲而青綠,水槽大到可以讓一隻小狗在裡面洗澡。
內牆的灰泥處處剝落,露出多年以來的漆彩。客廳裡擺設著織錦花紋的小長沙發、奧布松織花地毯、古董中國青花瓷、印花棉布和亞麻織品,各式家具和布料兼容並蓄,不拘一格。
掛在牆上的畫作有些技藝純熟,說不定身價非凡,有些純屬玩票。種種擺設呈現出一種散漫的美感,顯現出過往的榮華與昔日的品味——有點破落,但不失舒適。
她駐足於客廳,透過通往後院的玻璃門,望著院子裡的蘇菲和安托萬,蘇菲坐在爸爸幫她搭的鞦韆上,安托萬站在她身後推她一把。
薇安把帽子輕輕掛上門口的掛鉤,取出圍裙,仔細繫好。趁著蘇菲和安托萬在外面玩耍,她動手準備晚餐。
她把粉嫩的里肌肉裹上厚切培根,用細繩綁好,在熱油裡稍微煎一下,豬肉在烤箱裡炙烤時,她調理其他菜餚。
八點整,她喚大家上桌。腳步聲轟轟隆隆,談話聲嘰嘰喳喳,大夥一坐下,椅腳吱吱嘎嘎刮過地板,她聽在耳裡,不禁露出微笑。
蘇菲坐在主位,頭上戴著安托萬在岸邊幫她編紮的雛菊花冠。
薇安把橢圓淺盤擺上桌,誘人的香味緩緩飄起——炙烤的里肌肉、香脆的培根、淋上香濃白酒醬汁的蘋果,好端端地擺在盤底焦黃的馬鈴薯上,盤子旁邊擺著一盅佐以奶油醬汁的新鮮青豆,醬汁以自家花園採收的龍蒿調味,當然還有薇安早上烘烤的長棍麵包。
晚餐時,蘇菲跟往常一樣嘰嘰喳喳地從頭講到尾,就這方面而言,她很像她的伊莎貝爾阿姨,兩人都是靜不下來的女孩。
甜點浮島(ile o‑ante)終於登場,輕烤的蛋白霜有如小島,漂浮在濃郁的香草奶霜中,圍坐在餐桌的三人心滿意足,安靜地吃著。
「好吧,」薇安終於開口,伸手推開她半空的甜點盤:「該洗碗了。」
「哎呀,媽!」蘇菲嚶嚶抱怨。
「別抱怨,」安托萬說:「妳這個年紀不該發牢騷。」
薇安和蘇菲走進廚房,跟往常一樣各就各位——薇安站在深廣的黃銅水槽前,蘇菲站在石磚流理臺旁——母女兩人聯手清洗、擦拭碗盤。
安托萬習慣在用餐後抽根菸,薇安可以聞到家中飄散著菸草濃烈、甜膩的氣味。
「我今天說了好多事,沒有一件讓爸爸笑。」
蘇菲邊說,薇安邊把盤子放回釘掛在牆壁的粗拙木架上。
「他怪怪的。」
「他沒笑?嗯,確實不太對勁。」
「他擔心戰爭。」
戰爭。又來了。
薇安輕噓一聲,把女兒趕出廚房。她稍後上樓,在蘇菲臥房的雙人床坐下,聽女兒喋喋不休地說話。蘇菲穿上睡衣,刷牙洗臉,準備上床睡覺,從頭到尾講個不停。
薇安傾身親親女兒,說晚安。
「我好害怕,」蘇菲說:「快要打仗了嗎?」
「別害怕,」薇安說:「爸爸會保護我們。」
說是這麼說,但她依然想起許久之前,她母親也曾告訴她:別害怕。
那是當她父親離家參戰時。
蘇菲依然一臉懷疑。
「但是……」
「但是什麼?別說了,沒什麼好擔心的。好了,睡吧。」
她又親親女兒,雙唇貼上小女孩的臉頰,好一會兒才移開。
薇安下樓,走向後院。屋外悶熱,夜空中飄散著茉莉花香。她看到安托萬坐在草地上的一張鐵椅上,伸長雙腿,身子不自然地斜向一側,顯得無精打采。
她走到他身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他吞雲吐霧,抬頭看著她。月光中,他的臉頰蒼白朦朧,看來幾乎陌生。他把手伸到背心口袋,掏出一張紙。
「我被徵召了,薇安。十八至三十五歲的男子大多都已接到徵召令。」
「徵召?但是……我們還沒有打仗。我不……」
「我星期二就得報到。」
「但是……但是……你是郵差。」
他直直凝視她,忽然之間,她喘不過氣來。
「看來,我現在是軍人了。」◇(待續)
(點閱【夜鶯】系列文章。)
責任編輯:李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