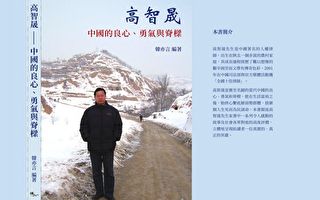對於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我們可以從下面兩個方面去理解:
一、關注生命,同情弱小,呼籲人性,謳歌和諧社會
中國現代史上的兩次權力再分配,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動盪,使許許多多的無辜生靈遭受塗炭。大地在燃燒,萬物均在劫火中歷經磨難,原有的社會失去平衡,舊的傳統(不管是壞的還是好的傳統)被打破了,不管是願意還是不願意,人們均要以最大的沉受量去適應新的社會和新秩序。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塑造的數十個人物形象從表面上看似乎很複雜,其實我們大致可以將他們分成兩種類型:
一類是心懷叵測的「革命者」,他們靠投機取巧輕意地就獲得了權力和利益。他們用手中的權利踐踏生命、踐踏人性、以勢壓人、欺強凌弱……這一類人,以靠心狠手毒當上鄉長的李青山;革命勝利後就急於另娶新歡、橫刀奪愛的、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的解放軍團長陳家根;心術不正,口蜜腹劍、見風轉舵的秘書曹發德;以及被階級鬥爭觀念燃燒而迷失了人性的市保衛部部長的韋貴喜……為典型代表。這些新貴從表面看他們的官職都不高,但是他們是黨的基層幹部,他們最容易接觸群眾、是共產黨人數最多、能量也最大的「地方官」。他們欺上瞞下、魚肉百姓,為了自已的利益,無視黨性,政策、法規……對他們的身邊的同志和上級,也會下毒手!
在《遠山蒼茫》這部長篇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滅絕人性的描寫:邊遠山區一個上任不到三天的鄉長,根本沒有一紙公文,便對跪在他腳下接受鬥爭的地主和兵匪,輕意地發出了處決的命令……
在《孤兒與革命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寫:身為市公安局長的韋貴喜,階級意識濃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階級意識十分濃烈的部長,抱養的女兒恰巧是他最仇視的惡霸地主的女兒;而他的親兒子卻在階級鬥爭的陰影中苦難地掙扎著!但是,當他知道他抱養的女兒懷孕後,得知對方的家庭是「惡霸地主」後,濃烈的階級仇便使他唆使造反派頭目,對自己的失落多年的親生兒子方宇動用了私刑,並使他喪失了生殖能力……做了使自己斷子絕孫的憾事!
在《孤兒與革命家》中,作者還濃墨重彩地描寫了鄢正甫的秘書曹發德,敘寫了曹發德一朝權力到手,便設計非法拘禁自己的老上級鄢正甫,並欲殘害這位老實而令人尊敬的老上級、老首長……
「三部系列長篇小說」除了對這些視生命如草芥,滅絕人性的無情揭露以外,還運用對比的手法塑造了一群謳歌和諧社會,為生存而抗爭、呼喚人性、化敵為友、消除仇恨的人物形象。
這一類人物以共產黨人省政治部部長鄢正甫、起義將領張雲軒、虔誠的基督徒唐維綺、命運坎坷的忠直漢子楊永春、被命運捉弄、從一個苦難走向另一個苦難的地主婆戴敏、被命運殘酷捉弄的水族女人方美英、偷吃禁果的苗家姑娘阿彩、不遠萬里從英國來的傳教士亨利……就是這麼一大群擁有正義感、關愛生命,熱愛生命、待人為善的人群,才使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變為呼喚人性,張揚權利、呼喚法制的作品,成為一部謳歌和諧與進步的長篇巨著!
在《遠山蒼茫》中,作家不惜濃墨重彩描繪英國傳教士亨利。他本是石油大亨的兒子,由於不滿列強對中國的欺壓與剝奪,憤然拋棄自己的石油王國,毅然來到貴州邊遠山區進行傳教,宣揚上帝的仁愛精神,與山裏人結成生死與共的情誼。
有許多評論家說:「亨利使人震撼」。這種震撼不是因為他的決定,而是他在貴州邊遠山區的所作所為,他不圖任何回報;他為迷信的山區帶來科學;為拯救生命而疾呼;為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他用自已的行為而贏得山民的尊敬……在邊遠的貴州山區雙溪坪,建立美好與和諧。他的無私奉獻,不僅感動雙溪坪的人,受到雙溪坪人民的尊敬愛戴,而且,也使受命到雙溪坪來驅逐他的省委重權人物——鄢正甫也深受感動。在《遠山蒼茫》中,有這麼一段畫龍點睛的描寫:
在漆黑的夜色中鄢正甫獨坐在波乜河邊沉思默想——「啥叫忠誠?啥叫犧牲?啥叫無私?啥叫奉獻?……其實人們要看的只是行動,是表裏如一」。
必需指出的是,鄢正甫的反思,是因為我們在農村使用「清匪反霸」、「合作化運動」等不當政策而引發的,通過對比,鄢正甫終於「大徹大悟」了。小說通過鄢正甫的大徹大悟深化主題:強權出不了真理,暴力終究是行不通的,只有人性的複歸,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會層的人以禮相待,和平共處。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才是終極目的。
二、 「人治」社會是中國進步和發展的最大阻礙
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運用對比的手法,先抑後揚,揭露「人治」社會的諸多危害及造成的損失,也描寫了許多由「人治」社會造成的形形色色的許多暴力及違法行為。但是,作家不是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冤冤相報」的方式去解決,而是以「人性」、「人道」的方法去解讀。作家在其作品中高歌正義,通過正義的力量使暴力者省悟,通過正義的呼聲深刻的教訓使暴力者懺悔、自新……這些採用引導,認清是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淡化矛盾、以創造和諧環境、和諧社會的方法,正是張宗銘比一般作家的高明之處。例如在《遠山蒼茫》中的土匪頭劉禮靖,在傳教士亨利和雙溪坪山人的影響下,終於棄惡從善;剛參加土改工作的學生杜進、彭正陽,因為蔑視生命和權利而濫殺無辜,本應以命抵命,但是,亨利認為他們的犯罪是因階級仇恨而生成的,是因錯誤的引導造成的,他為他們真誠的禱告和祈求、以及混血姑娘靈姑和蠱女阿歡在仁愛感召下的救助,終使雙溪坪的山民和受害的家屬原諒了他們,將「神判」時投下的死簽換成了「賠簽」……這樣的淡化矛盾的方式,這樣的在邊遠的山區擁有的古老的民主與法制,就連共產黨人鄢正甫也由衷地欽佩。
在《孤兒與革命家》一書中,階級鬥爭意識十分強烈的韋喜貴,作家讓他知道被他殘害的「階級敵人」正是他失落多年的親生兒子以後,他後悔莫及、無地自容、終於大徹大悟!最後,他主動請求原諒,甚至去營救被造反革派非法拘禁和迫害的原省委領導人鄢正甫。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韋喜貴的行為,簡單地看成是一種贖罪,而應該將這看成是法制觀念在這一類人身上的萌芽。
在社會生活中,人民大眾特別是生活在層低的人民大眾是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張宗銘的小說以大量的篇幅關注他們,描寫他們深受「人治」迫害的種種悲慘的命運,反映他們比任何階層的群體都更期望受到法制的保護。這一條主線,也始終貫穿在「三部系列長篇小說」之中。
張宗銘無愧是中國文壇上冉冉升起的一顆明亮的新星,他的可貴之處是憑自己的良知去寫作,這種創作的方法很可能遭來一些非議(當然是指文革以前,但以後也會有一些思想僵化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我們曾經讀過一些紅極一時的文學作品,也被強迫去電影院(注:在電影院打考勤)去看一些紅極一時的樣板戲,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紅極一時的作品和電影的內容漸漸的淡化了,甚至有的連書名或片名也記不起來,留下的僅僅是失去自由選擇讀書和看戲的痛苦回憶了。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則不同,它不虛美、不隱惡,它是作家良知的表露,它是生活中真、善、美的自然寫照,它是生活中假、醜、惡的真實錄影,它像一面鏡子,形象地逼真地再現那一段歷史的黑白。它不像我提到的那些紅極一時的文學作品,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味、發臭,成為了一堆堆的文化垃圾。
張宗銘的「三部系列長篇小說」像一瓶醇酒,時間越長,味道越甘美。我相信這瓶甘美的醇酒,不僅是中國人喜歡品嘗的,也是屬於國際友人喜歡品嘗的。中國需要更多的像張宗銘這樣有良知的作家,需要更多的像醇酒一樣甘美的作品。@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