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黑暗中苟且求生的民族,一個千瘡百孔、遍地冤獄、民生凋敝的中國,一顆新星,在宦海沉浮中拼搏了半個世紀的胡耀邦終於浮出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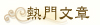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在窒息了三十個春秋的中國,星星的作品,震撼靈魂!特別是汪克平的許多木雕,其中《沈默》表現的正是中國人做人的現狀,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2004年3月,我在美國參加紐約《汪克平藝術作品展覽》的開幕酒會。在曼哈頓「SOHO」,欲匆匆從紐約離美回國的我和急匆匆從巴黎趕到紐約的汪克平,是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的第二次握手!世事和人生恍如隔世,像是在陰陽界上,感概萬千。
 2005年12月12日 4:15 PM
2005年12月12日 4:15 PM 1975年夏秋的颱風季節剛過去,革命委員會又刮起了強大的紅色風暴。一夜之間,成千上萬的群眾被抓進變相的集中營。專政工具們以革命的名義,大割所謂的資本主義尾巴。那時候我剛出差在上海,從電話裏我得知:打辦人員抄了我們工廠,拉去生產原料,使我們企業停產倒閉。我清楚這是縣工交局長蔡繼卓對我們的報復。我不能沈默了,唐吉珂德對風車的宣戰,即是我此時心境的寫照。我從上海打電報給縣政府,列舉蔡繼卓的種種罪行。電波的傳遞,如爆開的炸彈,在海門和黃岩的官場掀起了軒然大波。他們動用了一切專政的工具,向我圍殲過來。
 2005年12月10日 10:01 PM
2005年12月10日 10:01 PM 冬去春至,大地開始裸露出她那茶綠色的胸懷。我騎著白馬,馱著一個大包裹,懷抱著一個鑲著銀子圖案的馬鞍,去公社送還展覽品。
 2005年12月8日 11:51 PM
2005年12月8日 11:51 PM 他是烏魯木齊市有色局的幹部,住在一間平房裏,他為我鋪了地鋪,我住下了。第二天他給我辦好了"身份證明",由其單位蓋公章以他自己作為我的擔保,證明我是個良民,使我順利地在烏魯木齊安置處報了名。和我一起錄用的人將分派去北疆的富蘊縣溫都哈拉良種繁育場工作。多麼動聽的名字——"良種繁育場",一種誘人的新生活在向我召喚。我趕回去謝謝他,留給他幾幅速寫作為紀念,連他的名姓都忘了記,就這樣匆匆告別了。
 2005年12月7日 10:38 PM
2005年12月7日 10:38 PM 一件事,讓我重新正視起現實來。著名油畫家於長拱自殺了。蘇聯油畫大師馬克西莫夫的門生,大白天躲在被窩裏用刀片割斷喉管,求得對塵世的超脫。
 2005年12月6日 4:22 PM
2005年12月6日 4:22 PM 忘不了那個寒冷的早晨,小鎮街道的牆上刷滿了「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標語。一種內心的惶惑:我的姓怎麼會和這可怕的文字連在一起……
 2005年12月5日 10:31 PM
2005年12月5日 10:31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