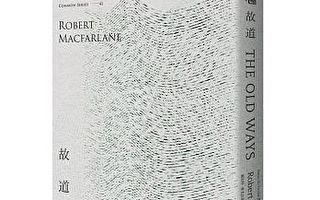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续前文)
2
我坐在家中客厅,音响播着“牛心船长”(Captain Beefheart,译注:美国知名乐团)的歌,外头是湿冷的十一月夜晚。我昨夜在外头待到很晚,因此当牛心船长唱道:“我整天四处跑,月亮留在我的眼底。”感觉超搭的。这种音乐很适合洗漱时听,我便开始听着,却被电话铃声给打断了。我不认得那个号码。
“喂?”
“嗨,我叫约翰.彼德森,我是跟海莲娜.卡尔森要到你的电话。”
“啊,是托索夫(Torshov)的海莲娜和那几个大男生哪。所以是有关房子的事吗?”
两年前我帮海莲娜一家改装阁楼,那是个快乐的家庭,我工作干得不错。海莲娜有位老公和两个儿子,有如一九九○年代红极一时的法国喜剧《海莲娜和一群大男生》。我就是那样称呼他们的,他们大概也觉得很好笑,不过这时我想到约翰.彼德森对此自然一无所知。
“是的,我们住在托索夫,也有间阁楼打算改装.我们在找擅长改装的承包商。外面有很多粗手粗脚的人。”他语气含蓄地说。
“我们想找手艺好的人,所以海莲娜告诉我们,他们很满意你的施工,推荐你……”
约翰跟我说了一些海莲娜一家如何利用阁楼的情形,他们也希望自己的阁楼能做类似的改装。他们所住的合作公寓委员会(housing cooperative,译注:一种共同管理式大楼,住户只购买其住家所占的大楼百分比,因此拥有的是公司股份的间接使用权)好不容易同意,把一部分阁楼改装成生活空间,透过合作公寓委员会系统取得这类同意十分困难,因为很多人不愿改变,认为没有必要。不过他们现在终于买下阁楼,准备改装了。
“我能问你几个关于这间阁楼的问题吗?阁楼是否直接与你们目前所住的公寓相连?”
“是的,客厅有道梯子通上阁楼,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打掉一面墙了,所以我们家是开放式的,客厅和厨房连在一起。”
“你们绘好制图,拿到建筑许可了吗?你们有按照结构工程师的报告去做吗?”
我们继续聊着,彼德森告诉我,设计图已经完成了,工程师已针对改装提供说明及详尽的制图,他们也已申请建筑许可了,应该很快便会核发下来。我跟他解释,我若承包这份工作,将亲自施作所有木工。我发出去的小包,都是与我合作多年的伙伴。承包商之间有个重要的区别—有自己工班,以及外包出去。作为一名工匠、聘雇中介或大盘工匠,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结果我发现,这份工程已发出去招标了,我将与另外两家公司竞标。这样的招标数很不错;若有五家的话,我就不会投标了,因为得标率过低。
对彼德森而言,他得从这份名单中挑出一名承包商,是不是最好的不重要了,因为我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而这跟我是不是高手也没有关系。优秀的承包工了解如何评估得标率,并借此评估客户。把报价单限缩在三份以内的客户,比那些招太多标的人,有更高的机会获得高品质的施工,因为招标数过多,会吓跑那些技术最好的工匠。
招标的办法之一,是先查看十家公司,客户可以检视这些公司的推荐人名单、财务状况及他们想看的事项,然后要求看顺眼的公司,花点时间计算投标的价格。提供推荐人名单并不会花太多时间,但准备报价单则会旷日费时。
如果我是根据上述资料受邀竞标的三间公司之一,我会挺高兴的,因为得标机会颇大。
我为海莲娜一家施作的工程,就是一份现成的好推荐;刚巧他们也仅邀请少数公司投标。
谈话过程中,我得知约翰在挪威国家铁路局上班,按他的说法是担任行政职,而妻子凯莉则在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上班。约翰暗示说,他或妻子都没有改装阁楼的经验,意思是他们对改装工程的实务知之甚微,也清楚表明他们将倚赖得标者的专业。
彼德森夫妇有两名男孩,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原本他们已经开始寻找另一个住处了,但改装机会出现后,便赶紧把握住。他们很喜欢自己居住的公寓大楼和托索夫区,所以决定改装阁楼。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交涉对象一直是住房合作企业与建筑师,他们透过建筑师,与工程师及规划部门联系。改建的理论部分,与他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较为类似,因此他们比较能够理解,不像现在需要的实作部分—建物本身,那样让人摸不着头绪。截至目前为止,彼德森处理改建的行政公文已经一年多了,显然有些不耐烦。那表示我得小心处理,别再给他添乱,在他的担子上加砖头(以我的职业,应该是加木板)。
文书作业的优点是可以更改;只要不付诸行动,纸上谈兵的意义并不大,白纸黑字只能当成某种现实。我不能把东西做出来看看能不能用,再拆掉重盖。如果户客愿意付钱的话,我当然可以那么干,但可能性很低。
对我来说,我会把理论转化成完工后的景象。我会计算螺丝钉、钉子、建材长度,还会计算工时。我在心中创造一部影片,想像自己施工的过程,而制图与说明便是我的脚本。客户最感兴趣的是结果,最在乎工匠宣告完工时,他们所看到的成品,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客户最好还是要能理解书面上的说明。
等工程结束后,设计图和说明便会被遗忘,再也不重要了,仅是阁楼今昔之间的连结罢了。
我是那忙着施作完工的人,而客户、建筑师和工程师大体上则视之为理所当然。这种立场上的分歧,往往造成彼此的距离,建筑师与工程师站在一边,另一边是我这名工匠。
我想大部分工匠都处于相同的处境—我们在施工现场看不到建筑师,却很希望能与他或她直接对话,找出对客户最有利的施工方式。
建筑师多半鲜少莅临现场,而工程师在评估前,往往也不会跑到工地。有时,我会把他们骗出办公室—至少感觉上是用骗的。把他们拐到现场后,我们因应突发状况而得出的解决办法,通常比他们不到场时更佳、更省钱,建造品质也变得更好,使得阁楼改装后,住起来更舒适。
在我执业的二十五年来,营建业中,学院派及工匠之间的合作程度,只能说是每下愈况,变得愈来愈学院了。同时间,工匠们挟其专业,积极地影响建造过程的传统,亦日渐式微。以前那是施工过程中极其自然的一部分,可是当各种苦口婆心的建议不被理睬后,就渐渐不再有人去深思与反省了。
若不曾学会更合作无间的工作方式,你便不会懂得自己错失了什么。我想,许多建筑师和工程师都希望营建业的文化有所改变,大家能携手合作;目前的状态,我认为太过强化自我了。所有的单位各行其是,我们太习惯这种各司其政的工作方式了,觉得很理所当然。
这些基本原则并非依据业界标准而设,换句话说,每位工匠在与所有其他人交涉,包括客户、建筑师和工程师周旋时,都要够机灵才行。所谓“一体两面”,从不同角度切入同一个问题,真的很适用于这一行。@(待续)
──节录自《挪威木匠手记》/大块文化
(点阅【挪威木匠手记】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