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米德大夫写的有关你的那些话都是对的,巴特勒船长。惟一挽救的办法是你把船卖掉之后立即去参军。你是西点军校出身的,而且……”“你这话很像是个牧师在发表招兵演说了。要是我不想挽救自己又怎么样?我要眼看着它被彻底粉碎才高兴呢。我干吗要去拚命维护那个把我抛弃了的制度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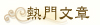
在梅里韦瑟太太的怂勇下,米德大夫果断行动起来了。他给报社写了封信,其中虽然没有点瑞德的名,但意思是很明显的。编辑感觉了这封信的社会戏剧性,便把它发表在报纸的第二版,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之举,因为报纸头两版经常专登广告,而这些广告又不外是出售奴隶、骡子、犁头、棺材、房屋、性病药、堕胎药和春药之类。
演完活人画以后,她不由得要寻找瑞德的眼睛,看看他是否欣赏她所扮的这幅精美的图画。她烦恼地看见他正跟别人辩论,很可能压根儿没有注意她。思嘉从他周围那些人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被他所说的什么话大大激怒了。
谣传说,巴特勒船长是南方最出色的水手之一,又说他行动起来是不顾一切和泰然自若的。他生长在查尔斯顿,熟悉海港附近卡罗来纳海岸的每一个小港小湾、沙洲和岸礁,同时对威尔明顿周围的水域也了如指掌。他从没损失过一只小船或被迫抛弃一批货物。
皮蒂明明知道爱伦不会赞成巴特勒来看她的女儿,也知道查尔斯顿上流社会对他的排斥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可是她已抵制不住他那精心设计的恭维和殷勤,就像一只苍蝇经不起蜜糖缸的引诱那样。
战争继续进行着,大部分是成功的,但是现在人们已不再说“再来一个胜仗就可以结束战争”这样的话了,也不再说北方佬是胆小鬼了。现在大家都明白,北方佬根本不是胆小鬼,而且决不是再打一个胜仗就能把他们打垮的。
思嘉没有继续读下去,便小心地把信折起来,装进封套,因为实在读得有点厌烦了。而且,信中用的那种语调,那些谈论失败的蠢话,也叫她隐隐感到压抑。她毕竟不是要从媚兰的这些信件中了解艾希礼的令人费解而枯燥无味的思想呀。这些思想,他以前坐在塔拉农场的走廊上时,她已经听得够多的了。
那以后一个星期的某一个下午,思嘉从医院回来,感到又疲倦又气愤,之所以疲倦,是因为整个上午都站在那里,而气愤的是梅里韦瑟太太狠狠地斥责了她,因为替一个伤兵包扎胳臂时她坐在他的床上了。
思嘉隐约看见一辆马车在屋前停下来,几个模糊的人影下了车。有个什么人跟着他。那两个影子在门前站住,随即门闩一响,思嘉便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杰拉尔德的声音。“现在我要给你唱《罗伯特.埃米特挽歌》,你是应该熟悉这支歌的,小伙子。让我教你唱吧。”
她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父亲会很凶的。她终于知道自己已不再是个可爱的淘气孩子,不能坐在他膝头上扭来扭去赖掉一场惩罚了。“不是……不是坏消息吧?”皮蒂帕特向她问道,紧张得发抖。
次日早晨吃鸡蛋饼时,皮蒂帕特姑妈在伤心落泪,媚兰一声不响,思嘉则是一副倔强不屈的神态。不管他们怎么议论,我不在乎,我敢打赌,我给医院挣的钱无论比哪个女孩子都多……比我们卖出那些旧玩意儿所有的收入还多。”“唔,钱有什么了不起呢?亲爱的?”皮蒂帕特一面哭泣,一面绞着两只手说。
她要领跳那场弗吉尼亚双人舞呢。她轻捷地给他一个低低的屈膝礼和一丝娇媚的微笑。他将手放在他穿着皱边衬衣的胸口上鞠了一躬。本来吓呆了的乐队指挥利维这时立即想起要掩盖这个场面,便大叫一声:“挑好你的舞伴,准备跳弗吉尼亚双人舞呀!”于是乐队哗地一声奏起了最美妙的舞曲《迪克西》。
我同时观望别的女孩子。她们全都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面孔。可你不一样,你脸上的表情是容易理解的。你没有把你的心思放在事业上,并且我敢打赌,你不是在思考我们的主义或医院。你满脸表现出来的是想要跳舞。要好好玩乐一番,但又办不到。所以你都要发狂了。讲老实话吧,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米德大人登上乐台,摊开两只手臂叫大家安静,接着响起一阵咚咚的鼓声和一起嘘声。“今天,我们大家。”他开始讲演,“得衷心感谢这么多美丽的女士们,是她们以不知疲倦的爱国热情,不但把这个义卖会办得非常成功,而且把这个简陋的大厅变成了一座优美的庭园,一座与我周围的玫瑰花蕾相称的花园。”大家都拍手赞赏。
媚兰听了他的声音,便转过身来,这时思嘉才头一次谢天谢地庆幸自己在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位小姑子。“怎么……这是……是瑞德.巴特勒先生,不是吗?”媚兰微露笑容说,一面伸出手来。“我见过你……”“在宣布你们订婚的喜庆日。”他补充说,同时低下头来吻她的手。
但是,对于年轻的单身汉—-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不妨对他们温柔地微笑,而当他立即注意到你为何这样笑时,你可以拒不说明,并且笑得更欢一些,逗着他们一直在你周围琢磨其中的奥秘。你可以在眼角眉梢示意,应许他们多多少少带刺激性的东西,叫他们千方百计要跟你单独说话。
当这种叛逆性的亵渎思想在她心中出现时,她偷偷地向周围观察,生怕有人从她脸上清楚地看出来。啊,她怎么就不能跟这些女人有同样的感受呢!她们对主义的忠诚是全心全意的,是真挚的。她们所说所做的一切的确出于至诚。而且,如果有人要疑心她……不,决不能让人知道!
并非城里所有的花都是献给南部联盟两位领袖的。那些最小最香的花朵都装饰在姑娘们身上。茶花插在粉嫩的耳朵背后,茉莉花和蔷薇花蕾编成小小的花环珮戴在两侧如波涛翻滚的鬈发上;有的花朵端端正正地点缀着胸前的缎带,有的不等天亮就会作为珍贵纪念骑装进那些灰制服的胸袋中。
在午睡时刻,梅里韦瑟太太和埃尔辛太太坐着马车登门拜访来了,她没有想到忧郁的心情竟这样得到了解脱。媚兰、思嘉和皮蒂帕特姑妈都对这种不适时的来访感到吃惊,于是赶快起来扣好胸衣,掠了掠头发,下楼迎接客人。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思嘉坐在卧室的窗前,满肚子不高兴地观看好些大车和马车载着姑娘们、大兵和他们的陪伴人,兴高采烈地驶离桃树街,到林地去采集松柏之类的装饰物,准备给当天晚上要为医院福利举办的义卖会使用。阳光在枝柯如拱的大树下闪烁,那条红土大道在树荫中光影斑驳,纷纷而过的马蹄扬起一阵阵云雾般的红色尘土。
查尔斯没有从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两个人那受到强有力的影响,也没有学会粗暴或讲求实际,因为养育他长大的家庭温柔得像只鸟窠。这个家庭跟塔拉比起来,显得是那样安静,那样旧式,那样文雅。
因此思嘉这次到亚特兰大来,也没有事先想过要在这里住多久。如果她觉得在这里像在萨凡纳和查尔顿斯那样沉闷无聊,那她一个月后就回家去。如果住得开心,她就无限期地住下去。但是她一到这里,皮蒂姑妈和媚兰就开始行动起来,劝说她跟她们永久住在一起。
这两位太太再加上另一位,即惠廷太太,是亚特兰大的三根台柱子。她们管理着自己所属的那三家教堂、牧师、唱诗班和教区居民。她们组织义卖和缝纫会,她们陪伴姑娘们参加舞会和野餐,她们知道谁找的对象好,谁的不好,谁常常偷着喝酒,谁要生孩子了和什么时候生,等等。
思嘉渴望着嬷嬷那双肥大又老练的臂膀。嬷嬷的手只消往孩子身上一搁,孩子马上就不哭了。可如今嬷嬷在塔拉,思嘉已毫无办法。她即使把小韦德从百里茜手里抱过来,也没有用。她抱着同百里茜抱着一样,他还是那么大声嚎哭。此外,他还拉扯她帽子上的饰带,当然也会弄皱她的衣裙。所以她便索性装做没有听见彼得大叔的话了。
1862年五月的一个早晨,火车载着思嘉北上了,她想亚特兰大不可能像查尔斯顿和萨凡纳那样讨厌的,而且,尽管她对皮蒂帕特小姐和媚兰很不喜欢,她还是怀着好奇心想看看,从前年冬天战争爆发前她最后一次拜访这里以来,这个城市究竟变得怎样了。
她的厌烦情绪是强烈而经常的。自从军营开赴前方以后,县里就没什么娱乐和社交生活了。所有有趣的年轻男子会都走了……包括塔尔顿家四兄弟、卡尔弗特家哥儿俩、方丹家和芒罗家的小伙子们,以及从琼斯博罗、弗耶特维尔和洛夫乔伊来的每一个年轻而逗人喜爱的小伙子。
不过两星期工夫,思嘉便由一位小姐变成了人家的妻子,再过两个月又变成了寡妇,她很快便从她那么匆促而很少思索地给自己套上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可是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尝过未婚日子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由滋味了。寡居生活紧随着新婚而来,更叫她惊慌的是很快便做了母亲。
他垂下眼睛,因为它们跟思嘉那双锋利得像要穿透他又似乎没有看见他的绿色的眼睛恰好相遇了。“他有很多钱,”她匆匆地想,一个念头和一个计谋接连在脑子里闪过。
从楼梯顶上的那个凸窗里,她能看见男人们还在树下和凉亭的椅子上斜躺着歇息。她真羡慕他们极了!作为一个男人,永远也不用经受她刚才把经历的那种痛苦,该多快活呀!
只有媚兰这个名字的声音使她恢复了意识,于是她注视着他那双水晶般的灰眼睛。她从中看到了那种常常使她迷惑不解的显得遥远的感觉……以及几分自恨的神情。




 2008年2月23日 5:13 PM
2008年2月23日 5:13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