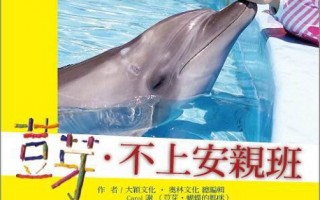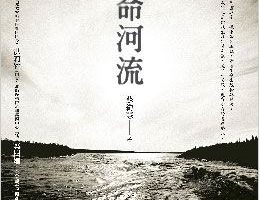1960年代,拉夫拉克爵士(Sir James Lovelock)开始检验地球做为单一生命体的可能性,他后来命名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大大影响了生态学。这种假说宣称地球会创造适合生命的条件,展现自我组织和自我管制的质素,类似于活的有机体。
像免疫系统一样善于“观察”的运动
两世纪前,康德和法国经济学家雅克.杜尔哥(Jacques Turgot)想像人类本身是一个类似的实体,是一个系统,拥有有机体的某些属性。他们并不孤单。从史宾诺沙到甘地,从路易斯.汤马斯(Lewis Thomas)到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哲学家、宗教教师和科学家都很好奇,整个人类物种是否会在神秘和难以理解的方式中整合起来。“合起来看,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心智似乎像个一致、活的系统一样运作。”汤马斯写道。
目前在全世界涌现、由下而上的运动与既有的意识型态,其差别之一是,运动根据“观察”来发展它的概念,而意识型态则根据信仰或理论来行动,这与达尔文和威廉.帕雷(William Paley)时代演化论与创造论的差别一样,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说的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差别一样。
达尔文并未尝试反驳创造论。他是一位田野科学家,希望找出在皇家海军小猎犬号航行时所发现证据的意义。同样的,运动并不尝试反驳资本主义、全球化或宗教基本教义派,但试着找到他们在森林里、贫民区、农庄、河流和城市里所发现的东西的意义。
运动中有意识型态吗?当然有,但是运动根本上是人性的一部分,承担起保护和拯救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接受有机体的隐喻能够应用到人类身上,我们就能想像,集体运动能够保护、修补和复原有机体在受到威胁时,持续下去的能力。若果如此,回应的能力就会像免疫系统一样运作,它依照个人的意向,独立运作。特定来说,数十万非营利组织共同的活动,可视为人类对毒物的免疫反应,例如政治贪腐、经济疾病和生态崩坏。
免疫系统遍布身体各处
正如免疫系统能辨认自己和非自己,运动也能辨认什么是人道,什么不是。正如免疫系统是内部防御的防线,让有机体在时间中存续下去,永续性也是人类持续生存的一种策略。 “免疫性”(immunity)这个字来自拉丁文的“im munis”,表示准备去服务。
免疫系统通常以军事用语来描绘:一种生物学的防卫机制,武装起来击退入侵的有机体。教科书上写着,抗体依附在入侵物的分子上,然后入侵物就会被白血球中和并摧毁。这些描述如此简单又细致,但击退入侵者和疾病的过程,就比较复杂有趣了。
免疫系统是身体里最多样的系统,组成分子有蛋白质、免疫血球素、单核白血球、巨噬细胞(macrophages)等等,一小群细胞同步工作,没有它,我们会因为寻常小事而暴毙,例如一片烂掉的水果,充满数十亿个病毒、杆菌、真菌和寄生虫,对它们而言,我们只是裹着牛仔裤和T恤的肥美午餐。
免疫系统遍布各处,分散在淋巴液里,透过胸腺、脾脏和成千的淋巴结来旅行,后者像小花生一样分散在身体各处。胸腺器官是你之为你的蓝图,是生理学上的存货清单,记录你的基因、过去的疾病和现在的状况,它充斥在淋巴液中,有助于防止任何不是你的东西来接管。
胸腺有益细胞辨认疾病
这些胸腺有益细胞(又称T细胞)是一种称为淋巴球的白血球细胞,几千亿个这种细胞在身体里缓慢流动,能够辨认目前和过去的感染与疾病。就像一个巡回的亚力山大图书馆,藏有病理资料,从血液流向组织,再回来。外来者被认出时,T细胞会传递讯息给B细胞,另一种细胞大队,然后让黏附在接收端的抗体,附着在入侵细胞的表面并中和它。
他们挑出零散的病原体,在这里是蛋白质,在他处是抗原,甚至活的疾病,将他们黏附在囊状树形的细胞上,看起来像个十字,介于牛蒡刺和和尖尖的庞克头之间。黏上些许病毒后,囊状树形细胞留在淋巴结上,保持警戒,那是一种察觉不出来、低程度的反应,病理学的实践正在身体的角落里操演。
摘自《看不见的力量》 野人文化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