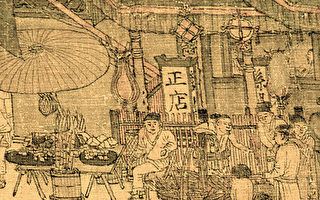少年时唱的歌,必有一些终生难忘,迟暮之年再回味那些熟悉的旋律,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欢乐中去。19世纪后期,日本诗人国木田独步说:“如果说少年的欢乐是诗,那么,少年的悲哀也是诗;如果说蕴藏在大自然心中的欢乐是应该歌唱,那么,向大自然之心私语的悲哀,也是应该歌唱的了。”我的少年时期正值上世纪50年代,生活平淡无忧无虑,没有学业重负,更谈不上悲哀,却充满嬉笑与歌声。那时小学校每礼拜都有专门唱歌的音乐课,至今回想依然历历在目。
教我们唱歌的女老师姓章,约40岁上下,稍有些胖。章老师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记忆中从未见她对学生高声说话,大家都能感受到她的亲切温和。音乐课上,我们学简单的乐理知识和五线谱,也学唱许多歌曲,包括少量世界名曲。有些歌唱过后也就忘了,有些歌声虽未全忘,但也没有兴趣再回想,有些歌却令人一辈子忘不了。还有的歌忘不了,是因为与少年时的往事连在一起。好像是四年级的时候,章老师教过一曲《热血》,是上世纪30年代电影《夜半歌声》插曲,旋律激昂、雄壮: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
学期结束的时候,音乐课照例每人有一个得分成绩,这个得分的依据,是在当学期学过的歌曲里,自由选择一曲,站在章老师的琴旁面向大家演唱,由章老师伴奏。这等于每人获得一次单独登台演唱的机会。那个学期的期末,全班男生先后轮到登台时,都不约而同地选了《热血》。记忆中,女生选择的是一支牧歌。曲名早忘了,不是文革后电影《少林寺》中的“牧羊曲”。那牧歌有淡淡的叙事式抒情,只依稀记得歌词大意,是说黄昏后放学回家,领着羊儿到山坡,“羊儿吃草我唱歌”。这样一幅悠闲宁静、田园诗般的画面,与现今学童“不许输在起跑线上”的艰难重负,真是天壤之别。
不过当年女生中,有两人出乎意料地选择了《热血》,好像有点离经叛道。我对年少时音乐课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是因为其中一名女生与我邻居,她叫宋□□。她家离我们家大约仅50米左右,她与同班女生下午跳橡皮筋,常常就在我们家门口。忘了是在三年级抑或四年级,一次母亲到学校,正当我们课后在操场,我一眼看见母亲拔腿就溜,继而躲在墙角偷偷观望。此时宋□□迎上去,陪母亲到老师办公室,这令我心里暗存几分感激。我至今未忘那首《热血》,是因为《热血》与年少时的生活经历连在一起。
一些与我同时代的人,尤其自称“青春无悔”的老三届,常津津乐道于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于1955年出笼,我们跟着老师机械地学唱,谈不上心驰神往的愉悦。中年后渐渐明白,1955年的前一年,“胡风集团”遭遇大规模围剿,两年后是震惊全国的“整风反右”,从此知识分子齐刷刷地跪了下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听起来有画面感,音乐形象带有明确的粉饰。对于无数知识分子在1957年遭受的灭顶之灾,《荡起双桨》的最大功能就是掩盖。我虽是学唱《荡起双桨》的第一代学生,但随着世事变迁,我对《荡起双桨》的厌恶感与日俱增。“美丽的白塔”与“绿树红墙”,描述的是北海公园,其实只属于红二代。而今还有多少人知道,北京高校不少年轻的右派学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来到“美丽的白塔”边沉湖自殁。
对多数城市少年来说,“荡起双桨”只是春游或秋游时才有的一次体验。对农村与山区少年而言,对于河南、安徽、四川、广西……的广大农村少年而言,“荡起双桨”与“白塔红墙”更是遥远的梦。知道在那个年代里,究竟有多少衣不遮体的少年,是活活饿死的吗?《荡起双桨》的最后一段:“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这更是对极权恶党露骨的阿谀逢迎。所谓“亲爱的伙伴”,明明白白指的是太子党,对广大苦难中的少年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巨大欺骗。曾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少年,以为自己也在“亲爱的伙伴”之列,每唱《荡起双桨》如同阿Q那样的飘飘然,实在是自作多情。专为太子党们“安排幸福的生活”者,是谁?
近中年时,听台湾罗大佑的《童年》,才让我真正产生如痴如醉的亲切感。《童年》中抒发的情怀,仿佛就有我自己的影子:
……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
还在拚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这分明就是我的“童年”,无需“美丽的白塔”,无需“绿树红墙”,更不用“推开波浪”,我喜欢的是《童年》表达的那种懵懂、稚气与真实:
……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
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其实在我年少时,也有一支歌可与《童年》媲美,这就是章老师教的《我们的田野》。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每回想起遥远的少年时代,耳边就响起《我们的田野》。歌声质朴淡雅,无一丝雕琢的痕迹,但旋律展显的意境,却被烘托得诗意盎然。曲调仿佛是娓娓地叙说,悠悠的情调洋溢着自由的气息。每当唱起这首歌,眼前就能浮显出那个时代的田野与河流,蓝天白云下的稻田,还有水边的芦苇与野鸭。年少时,多少次望着雨水敲打玻璃窗,心里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田野”在雨中的样子。文革似乎淹没了这个美妙的旋律,文革后还是忘不了《我们的田野》。可惜时光无法倒流,今天的城市化潮流,人们已无法再回到“我们的田野”中去。毫无疑问,《我们的田野》是我今生今世最难忘的歌: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
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
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平静的湖中,开满了荷花。
金色的鲤鱼,长得多么的肥大。
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
……
“我们的田野”距现今时代,早已渐行渐远。少年时的田野,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教我们这首歌的章老师,大概也早已离开了人世。“碧绿的河水”、“无边的稻田”、“湖中的荷花”、“湖边的芦苇与野鸭”……只能在梦中找寻。上海郊区乡村,一些古镇老街不断被开发、包装,不知不觉就使得“我们的田野”渐渐消失。远近闻名的朱家角、枫泾、新场等江南水乡,成了拥挤的旅游景点。这些景点最醒目的标志,是一盏盏高挂着的大红灯笼下,一家紧靠一家的小吃店,争先恐后地招呼行人;熙熙攘攘的人群,手里捧着一盒盒臭豆腐边吃边走。低头看时,交叉的河流全都污浊不堪。几年前我和老伴赴山东,途经日照、蓬莱、威海、青岛等地,昔日远离城市的田野,到处耸立着一排排空置的烂尾楼。少年歌声中那个“美丽的田野”,究竟到哪儿才能找到?
所幸的是,约十余年前见到网上一段视频,是辽宁少年合唱团演唱《我们的田野》。我好像突然沉浸在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里。几年前又见上海某歌唱家携幼女同唱《我们的田野》视频。六十余年过去了,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们的田野》。毫无疑问,那位歌唱家经良好的专业训练,又有天赋嗓音;少年合唱团也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演唱这首歌。侧耳细听,可惜他们的歌声里,很难寻觅我在年少时《我们的田野》那种风味,也很难找到上世纪50年代乡间田野的气息。尤其在一个细微结点——紧接“碧绿的河水”之后,有一个短促的休止符丢弃了。这个休止符大概就是点睛之笔,音乐是神奇的,失去了这个休止符,《我们的田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我想起1999年,人们在电视屏幕前,聆听澳门学童合唱《七子之歌》:“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没想到歌声一开始,即令人心潮澎湃。不久,上海小荧星艺术团也排演了这首歌,并在电视台直播。小荧星艺术团的成员,大多太过机灵、聪明,他们知道自己是明日之星,他们接受专业的指导,演唱精致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歌声甚至透露出超越年龄的世故。遗憾的是,小荧星们的演唱,缺乏的正是澳门学童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份纯朴、稚气与天真。要知道,那才是歌声最珍贵的要素,完全源自浑然天成,靠模仿学习无法获得。一个城市少年的整体气质,就隐藏在歌声里,谁也无法改变。这与《我们的田野》的原始风貌不能强求,更不能复制的道理,是同样的。
是的!今天的人们,也许永远无法再回到当年“我们的田野”中去了。虽然还有人会唱起《我们的田野》,但那已不再是我在年少时的《我们的田野》。@#◇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