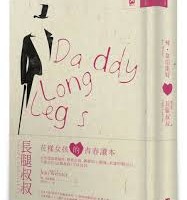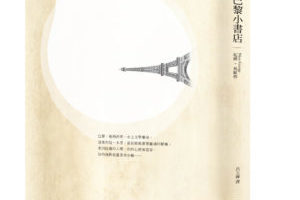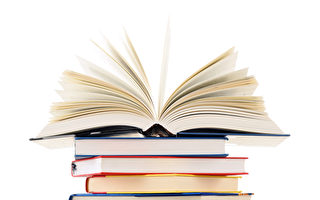书摘:今晚,我们用人生调味(1)

《今晚,我们用人生调味》(平安文化出版社 提供)
耶诞晚餐
我在和爱德华见面之前,就听说了他在太太临终前所作的承诺。
薇乐莉是爱德华的女儿,也是我认识非常久的一位老朋友,她在母亲过世后不久就跟我说了这个故事。
她的母亲宝拉卧病多年,在九十五岁生日的前几天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有一天却突然在床上坐起来,特别指明要跟她亲爱的先生说话。
“听我说,爱迪。”宝拉的语气坚定有力。
“你现在不能跟我一起走,否则我们的小家庭就到此结束了。”
宝拉知道爱德华已经作了决定,他宁可跟她一块死,也不愿独活。
那样不对,她说,而且极力劝他要活下去。等他好不容易同意了之后,她就对着这位结发六十九年的男人唱小夜曲。
开口的第一首是〈我风趣的情人〉,然后一口气唱了1940年代与1950年代排行榜上有名的百老汇音乐剧歌曲和民谣。歌词有一搭没一搭的。
当年他们还年轻,仍然怀抱着雄心壮志,相信自己能在演艺界闯出一片天空。
宝拉的歌声清亮,丝毫听不出她几天来饱受胸腔感染之苦,连说话都很困难。她最后以〈全部的你〉作结,唱得七零八落:
“我爱你的北方,东方,西方,你的南方,但我最爱的是全部的你。”
二十四小时后她就过世了,在2009年十月。她死后的几周内,爱德华哀恸逾恒,觉得几乎不可能守住他对宝拉的承诺。他独自坐在安静的公寓里,坐在餐桌前,他们一家人曾在这张餐桌上吃过许许多多活泼愉快的晚餐。
最后,爱德华住进了雷诺克斯山医院,医师们做了一连串的检验,却找不出他的身体有什么毛病,打算隔天就让他出院。
“恐怕他是不想活了。”薇乐莉说。在医院的等候室里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
那天是耶诞夜,我们说好了一块吃晚餐。薇乐莉推荐了一家医院转角的餐厅,她都陪她父亲在这里用餐。
这是一家没什么特色的第三街小馆子,我们入座后,戳着乏善可陈的红鲷鱼,我们两个都哭了。
这天原本是宝拉的生日前夕,而薇乐莉还没有走出丧母之恸。现在她又非常担心她父亲,怕他会活不下去。
我也不确定在听薇乐莉述说宝拉唱歌的那一段时,为什么会泪崩。
我没见过爱德华,而虽然那是非常催泪的一幕,我还是忍不住觉得部分原因是:我自己的不快乐,也被赤裸裸地揭穿了。
我刚搬到纽约不久,在报社当记者,耶诞节我得出差。我的婚姻眼看也快解体了,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假装一切都好。而且我非常担心离婚对我年幼的女儿会有太大的冲击。
我含糊其词地提出了自己的困境──我不想害薇乐莉在她父亲生病时还替我的问题担心──她建议我和爱德华一块吃饭。
“他很会做菜。”
薇乐莉边哭边说,或许是希望这句话会勾起我的好奇心,等她回加拿大后,我会自愿去探望爱德华(她的姊姊萝拉是艺术家,跟先生住在希腊)。
我不知道我是因为美味大餐太诱人,或者是我只是太寂寞了,连跟一个抑郁沮丧的九十岁老翁消磨时光都变得具有吸引力。可能是想为薇乐莉这个朋友两肋插刀,也可能是对她父亲感到好奇,让我在两个月后来到爱德华的大门前。
反正无论是什么原因,我压根就没想到和爱德华见面竟然会改变我的人生。
为了我们第一次的两人晚餐,我穿了一件黑色亚麻质地的宽松直筒连衣裙和凉鞋。我轻轻敲门,然后又按电铃,几分钟之后,一名高个子年长绅士突然打开了门,两眼带笑,握住了我的手,吻了我的两颊。
“达令!”他说:“我一直在等你。”
***
九十三岁的爱德华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而且“很会做菜”。无论是在口中融化的杏子舒芙蕾、香气弥漫的苹果派,还是纸包香草烤鸡、里斯本风镶小乌贼、法式葡萄酒酱牛排 ……
伊莎贝儿每周与爱德华共进一次晚餐,不仅品尝到爱德华精心烹调的各种美味佳肴,也分享了爱德华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智慧。
刚开始我总是带着一瓶酒到爱德华的公寓。
“什么都不需要带,宝贝。”他说。
尽管我常常会忽略这个建议,我觉得两手空空去吃饭很不习惯。
而且也不需要敲门或是按门铃,爱德华这么跟我说。他一定会知道我来了没,因为我一走进这栋公寓的大门,门房就会打电话上来通知他。况且,他的门也都不上锁。
不过在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坚持要给我一把钥匙,怕的是他在早上或下午在沙发上打盹时,我想过来看看他,门却锁住了。
他给我的钥匙套在紫色塑胶炼上,钥匙环上的小卡片用黑色粗体字写着爱德华以及他的电话号码。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不会真的用这支钥匙打开他的公寓门,可是我很有礼貌地收下了──表示友谊,也每天提醒我爱德华现在是我人生中的一分子了。
每次我带酒去,爱德华都会把我的名字写在标签上,然后塞进门厅衣柜里的临时酒窖里。衣柜是他挂冬天厚外套的地方。
每次都是在我抵达之前,他就选好了佐餐的酒了,而我带去的酒会留待下一次更合适的餐点。
在一次早期的晚餐,我犯了个错,我带了腌鳕鱼炸丸子,这是我根据我母亲的食谱做的。我根本就不该以为他会把炸鱼丸连同他的菜一起放上餐桌。
我毫无预警就把这道菜塞给他。在我们相识的早期,我从来就没想过爱德华准备每一餐花了多少心思。我才刚把那一包用锡箔纸包着的炸鱼丸递过去,就知道我失礼了,我也看出了爱德华有片刻的疑惑。
但他优雅地收下了我的礼物,邀我这个星期再找一天来晚餐,好让我们一起分享炸鱼丸。
爱德华不是势利鬼,也不是让人受不了的吃货。他只是喜欢做事情照着规矩来。
他对自己创造的东西都十分关注──无论是客厅里的家具或是他的文章。他亲手打造了所有的家具,连椅子的布面也一手包办。而且他写诗和短篇故事,一笔一画都规规矩矩,再很有耐心地把草稿重誊在白纸上,写到他满意了才会交给他的一个女儿打字。
他对待烹饪也是差不多的态度,虽然他是在晚年,在他七十几岁时才开始掌厨的。
“宝拉做了五十二年的饭,有一天我跟她说她够辛苦了,也该轮到我了。”他说。
爱德华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要珍惜美好的食物。十四岁时他留级了,他的父母把他送离纳什维尔,到纽奥良去跟他富有的叔叔、婶婶过暑假。
他的婶婶爱莲诺是老师,决定要教会他什么叫纪律,让他回到正轨上来。同时她也决定要指导他做法国料理。
“我被带进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世界。”他说。
回忆起1934年在赫赫有名的安东尼餐厅吃的一餐:“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吃软壳蟹。裹上薄薄的面糊油炸,配上融化的热奶油。真是太美味了。”
他开始烹饪时,借用了安东尼餐厅的法式克里奥菜单,不过他也开心地跟我说,他也能欣赏简单的东西。
他仍能记得小时候吃水煮包心菜:“加上一大块奶油,那种滋味就只有天堂才有!”
而且他到处找灵感:他自称他的炒蛋技术是从圣若翰那儿学到的。◇(待续)
——节录自《今晚,我们用人生调味》/ 平安文化出版社
【作者简介】
伊莎贝儿·文森(Isabel Vincent)
1965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多伦多大学毕业,目前她定居于纽约。
伊莎贝儿·文森是知名调查记者,除为《纽约邮报》撰稿外,报导也出现在《TIME》、《纽约客》等全球各大报章杂志上。她并曾赢得多个奖项,包括加拿大记者协会“卓越调查新闻奖”。其著作《身体与灵魂》获加拿大“国家犹太图书奖”,《希特勒的沉默伙伴》则获颁“犹太大屠杀纪念奖”。
责任编辑:李昀
点阅【今晚,我们用人生调味】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