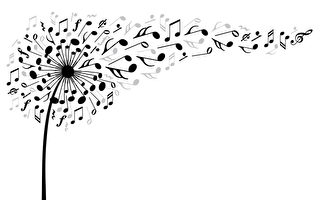井底之蛙
小舅担心我听不懂“上海话”,下班后常过来找我,问东问西。
我说:“早就会了,不难啊!”
他总是用上海话一再叮咛:“处处小心点儿,别给我丢脸啊!”
“谁丢脸了!”
我忽然冒起无名火,大声的“顶嘴”。
小舅拍拍我肩膀,撂下这句话:“翅膀硬了呦!”
是讽刺、调侃还是怒气、失望,我不知道,看到他掉头离去时,我犹然激动得眼眶潮湿。
小舅是“牵成”我的长辈,没有感恩,却还跟他闹脾气,我这是“疯了”吗?
书店打烊后的收拾、清洁工作,还需要两个小时才做得完,当我躺下疲倦的身体,已是近午夜时分。这可以折叠的“行军床”,白天竖起来靠在邻旁厕所的墙上,它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容身之所”;尽管如此克难,也比我之前寄养舅舅家好得多。
我是阿嬷(外婆)抚养长大的。小时候不知有父母,只听说妈妈会寄来生活费。我们祖、孙睡觉的地方,是两个塌塌米大的床榻。
每到睡前阿嬷照例要唱一段“七字调”:
我身骑白马走三关,
改换素衣回中原,
放下西凉无人管,
一心只想王宝钏。
这是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钏》中团圆的高潮剧情,但从阿嬷口中唱出来,却充满“哀怨与悲凄”,这是底层生活者绝望的抒发之声吧,我想。
阿嬷的家在延平北路妈祖宫前面小巷底的大杂院,屋前有一块广场堆放外公买卖的火碳。这里并不是我的家,可是据说出生后我就被送到这里,由阿嬷照顾。
只要有野台歌仔戏,忠实戏迷的阿嬷一定不会错过,她要我拿着小凳子,一起去看戏。虽然我很不耐烦,但小小年纪的我,很懂得“跟班”责任,每每安静陪伴从不吵闹,阿嬷因此常夸我这个“金孙”:早熟又贴心。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似乎天注定,有父母的我,却如同孤儿在阿嬷身边长大。外公去世后,火碳营生只好停滞,我跟阿嬷的生活立刻陷入绝境。
那是我们走避空袭轰炸到“土城”生活数年后,重回延平北路时所发生的悲惨事。
阿公走后,三人变两人,床榻宽敞了一些,阿嬷的歌声依旧,而我长了身高,要继续返回小学念书。
原本在延平北路“太平国小”念两年日式学校的我,如今,忽然升上四年级,学校也改制成“国语小学”。只因战事停了,台湾光复了,天下一夕之间改朝换代,大家都在期待好日子来临。
阿嬷日日盼望女儿、女婿解甲归来,而我对他们的音容早已模糊。我不怕“孤单一人”,最怕在舅舅家看舅妈的“吃人脸色”。
最难忘的一次是阿嬷帮我装便当(便当只有隔夜剩饭,并无菜),不小心盖子掉到地上发出了声响,立刻听到房间传来怒气冲冲声:“哪个人在偷吃?”
疼爱我的阿嬷,担心我到学校饿肚子,总是在我书包塞便当。我知道舅妈很在意,常指桑骂槐让阿嬷难堪。
因此,能到“国华书店”当杂役,我很甘愿。
我选择了像一叶孤舟行驶在茫茫大海的“行军床”——它是唯一对我完全包容的“庇护所”。虽仅一尺半宽、五尺长的局促空间,躺在上面,身体要弯曲,才能安放脚足。但它让我随即进入梦乡,修补工作的体能消耗,让我在次日起身时,又是一个充电十足、精神充沛,不惧烽火的战士。
然而,今夜,我辗转难以成眠,一幕幕跑马灯的回忆:阿嬷曾经拥抱我的体温、舅妈鞭子一样的指桑骂槐……“延平北路、土城、延平北路、三重埔、重庆南路”几度的迁居来去,我像是在做“总结”……
但其实,我的命运才刚刚有转折,不是吗?
无法阖眼的我,反思再反思,今天对小舅发脾气是什么道理?
我面对长辈无论多么委屈,也从未这样无礼,何况小舅是我的长辈。没有他的介绍,我的人生不会有机会走到“重庆南路”。
当时,我的放肆,难道就因为那一句问话吗?
不是的,他的话只是点燃的引信。当时我的内心好像一座急待喷发的“火山”,因为小舅是自己人,就成了倒楣的“出口”。
“自己人”,多少年来,除了阿嬷之外,我没有“亲人”,是孤单所累积的“怨怼情绪”;有时候,愤怒的表现其实是为了掩饰撒娇行为,人只有面对“自己人”,才敢发泄的那个勇气。
我现在明白了,我多么渴望能赖在某人的怀里哭着、闹着……可是为时已晚,小舅一定不会原谅我。
原来,孤单会使人发狂,寂寞会让人犯错,在这一夜,我发现人的脆弱会因无知而衍发悲剧,我如何能够避免坠落于黑暗的角落。
“你要强壮起来,争取自己的活口。”
阿嬷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53年(我十三岁)。
双亲先后从南洋归建回来。
父亲恢复开业,所租的房屋很小,前面当“诊所”,后面做为住所,并没有我可以待的空间。况且,因为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经常夜不归营,影响到次日医诊工作。诊所无人看诊,病患抗议,母亲无奈——夫妻俩一碰面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当时的我,念初中二年级。在自我认同的那个年岁,家中丑闻让我几乎要窒息,只得离家逃到阿嬷身边。当时,阿嬷再度收留我,却像在交代遗嘱一样郑重,给我这霹雳之语(你要强壮起来,争取自己的活口)。
三年后,小舅把我带到“重庆南路”。
这是我的“重生”吗?
尽管杂役工作很辛苦,却因争取到“自己的活口”而倍感欣慰。毕竟,我做到了阿嬷的嘱咐。
小舅是“读者书店”(远东图书公司前身)的员工,它就在“国华书店”隔壁。他曾说台湾人要在外省帮的天下讨生活,总是“矮人一截”。他要我收敛娇气,完全的接受这样的现实才是“上策”。
位于台北市城中区的重庆南路,在清朝时期北段称为“府前街”,南段称为“文武街”。日治时代,重庆南路称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华的街道”;当时附近的衡阳路称为“荣町通”,两处合并为“台北银座”。
这一带有百货公司,银行、钟表店、金饰银楼、时装店、茶庄、布庄、餐厅,是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红酒绿。
1947年(民国36年),国民政府迁移到台湾,总统府及各部会均集中于城中区。老蒋总统特别下令,将“府前街”、“文武街”更名为“重庆南路”,期勉国人要效法八年抗战“重庆精神”,在台湾生聚教训、整军经武,期能早日完成“反共复国大业”。
其中位于衡阳路口的“新高堂”书店,是日治时代台湾最大的书店。它成立于1896年,1915年在重庆南路扩大营业,成为战前台北的书店龙头,在20年代大量引进世界各国的书籍,发挥了打开汉语阅读大门的角色。
不仅如此,“新高堂”书店三层楼高的红砖建筑也成了重庆南路的地标。在大厦落成的前一年,日本人拟定的台北都市计划中,城墙拆除、道路规划已趋完成,各地搭火车来到台北的人,一定会经过重庆南路。逛书店买书的行为,潜移默化,渐渐使民众养成阅读习惯,造就了书街人流的氛围。
战后“新高堂”由“东方出版社”接手,位于“文武街”的“太阳号书店”,由“商务印书馆”进驻,其它如“文明堂”、“杉田书店”等,也都曾在“台北银座”缔造浓厚的书香气息。
在百废待兴的光复时期,聚集知识与教育核心的“书街”,洋溢着台湾知识分子求知与受到启蒙的光辉。
战后随着政府来台的第一批人员,除了负责接收的官员外,要数“上海人”最多。这些进驻“最繁华街道”的人,因为地缘与资讯的流通,抢先在紧邻政治大道旁的街道购置房产。当然,主要是他们本来就是“商人”,深谙经商之道,能嗅到生意气息,也有足够的投资财力。
“国华书店”的薛颂留老板,原在上海开设“布匹印染工厂”,上海沦陷之前,他们当机立断结束事业,扶老携幼,全家十来口渡海到台北,变卖所携带的大量黄金,买下了重庆南路一段66号的三层楼房,并登记“国华书店”为事业基地。
于是一个接续一个,大批的上海人纷纷集结在重庆南路上,成为后来“书街”的先锋,而衡阳路更造就了“小上海商圈”的美名。
当年,日本书店收摊遣返后,台湾的书籍全部由“上海”供应,除了“商务印书馆”以分店经营自家的出版品外,其它书店也都由进口取得货源。但是上海沦陷后,轮船无法直航,海路阻断了,大陆的书籍只得先输往香港,再以邮包邮寄到台湾。
所以,我这个学徒每天最重要的差事,就是到邮局提领大宗包裹。这些包裹是当时台湾人的精神粮食。有文艺书、知识书、专业书、字典、辞典等等。
收货后,我依照各地书店或单位来的订单分配再转批发,都采用固定合作的“货运”车送达。
我的第二桩工作,就是开三联单、计算货款、抄写订单资料,然后分装包裹、捆绑、张贴收件条。当货运车到达时,有送出的,也有退回的。我必须清点退货,核对单据,计算货款,誊写细目存档,以供下次订货时的参考。
可见重庆南路的上海帮,当时不但扮演了台湾书籍的总代理,更是掌握台湾人思想的流向。
这些书店经营,店面卖书只是其中一项,最大的收入是政府发包的“教育政策”。从小学、初中、高中、五专、大学的各类教科书,都分配在这些上海人手上。
其次便是来自自制的出版品,无论是学生的课外读物、辅助教材,还是文学、科学、史地、哲学等等,都采用“翻印”或“改写”方式,以慢慢取代大陆进口的书籍。
直到两岸断绝,台湾出版社如雨后春笋的成军,很多书店的资深伙计纷纷离职自设门户,分食着出版事业这块从原来保守、封闭至突然跃进的大饼。
因为,当时很多知识资源被操控,社会大众反应极端饥渴,政府只好开放出版条件的法规限制。
时值1956年,是我来到“国华书店”满三年整。这天,老板对我说,书店即将更名为“大中国图书公司”,会扩大营业项目,鼓励我再接再厉,并称赞我的能力。
言下之意似乎表示我通过了“试用期”,也就是学徒“出师”了。
当天下班后,我赶紧跑去向小舅报佳音,并为曾经顶撞他的失礼正式致歉。
这些年来,我时时刻刻记着这个教训,每天都在琢磨内心脆弱的地方。我深知自己要从卑微到强壮,得去除一些偏执的习气与念头。我致力于怎样融洽的在“外省帮”里做人、处事;如何从“矮人一截”这样的现实中,摸索着关键的专业知识。
小舅说:“不提过去了,你现在才真正是翅膀硬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知道我博得老板的信任与称许,是靠着“苦力”,我来了三年,经手处理了千万本的书,但我没有翻开过其中一本,更不要说阅读内容文字,说穿了,我仍然只是一只“井底之蛙”,我又能有什么“打算”?
小舅说:“我很高兴,你没给我丢脸,你算是给台湾人争了一口气呢!”他忽然哽咽了起来,也许感触到学徒生涯的不堪,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说:“去吃排骨面,今天要豪气的庆祝!”
每天晚上在武昌街城隍庙前摆出的面摊,是军旅伙夫出身的大叔掌厨。他的独家绝活,就是排骨面。这是当时我们最高境界的大餐。◇#(节录完)
【作者简介】
黄开礼
从书店里的一介小学徒成为拥有一家出版社的发行人,黄开礼看尽了重庆南路书街的繁华,回首往事,他将自己的经历与见闻娓娓道来,带领读者重回充满油墨味和书香的那段岁月。
——节录自《书街旧事》 /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杨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