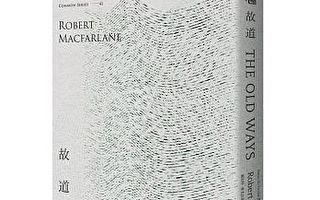人走了,时间也过了,
画留下来了,时间停止在那里?
这幅画变成了历史。 台湾是不是这样?
很多生命在生锈,而后腐掉?
“会落雨吗?”
大伯问,身边站着新的大姆(编注:大伯母)。
“中午以前不会落。”
建墓师抬头看看远外山顶,有白色的云翳窜了上来。
墓地散布在低山四分之一的高度以下的山坡上。墓地里,挤满着坟墓,有大有小,四周长着杂草,只有零星的矮树。
阿公,镇上的人叫他虬毛伯,因为他有一头卷发。
这是阿公的墓地,拾骨以后,改建成家族墓。
建墓师把烟蒂一丢,用脚踩了一下,看看还有些烟,再踩了一脚。
墓地下面,是一片稻田,是一片绿色,第二季的稻子,已长到一尺多高了。
一部计程车在墓地入口处停下,一个穿着深灰色衣裙的女人下来,匆匆越过墓地和稻田之间的小路。
那是大姑。
“这时候也塞车,不像话。”
大姑已满身大汗,一边急喘着气。
大伯和父亲商量,决定为阿公拾骨以后,在阿公旧坟地点,盖一个家族墓。墓已盖好,今天要把先人的骨瓮移过来。骨瓮有五个,曾祖父母、祖父母和大姆的。
阿祖贫穷一辈子,从小到处流浪,有时打零工,有时摆摊子,或做流动贩,卖番薯、卖土豆,或杏仁茶等。其它,更早的墓,找不到了。因为阿祖并没有告诉阿公。
家族墓有一点像土地公庙,比小型的土地公庙大一点,比中型的小。
家族墓的内层是阶梯式,有五层,每层可放八个骨瓮。
以前,家族的五个墓,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每次扫墓,几乎要花一整天的时间,东西奔走。
这次家族墓完成,重新安置骨瓮,父亲和大伯商量过,要不要请二伯。二伯已过继给舅公,已改姓石。实际上,阿公最疼二伯,阿公是船伕,二伯小时候也时常上船找阿公,有时还会和阿公在船上睡觉、过夜。二伯和大伯,以及和父亲的关系,完全维持着亲兄弟的情谊。
二伯,以前叫阿公姑丈,后来就跟大伯、父亲他们叫阿丈。那时候,在农村或小镇,还有人不叫自己的父亲阿爸,而叫阿丈或阿叔。
要请二伯,就要请大姑。
大姑大二伯将近十岁,在二伯还没有出生之前,已先过继给舅公了。因为舅公一直没有小孩。
大姑对舅公很不满,舅公死后,自己去公所,把姓改回来,不再姓石。
大伯按照建墓师的指示行事,点了一把香,分给大家。
“怎么不写‘陇西’?”
以前,在墓碑的上面,在显考的两侧,都刻着“陇西”两字。这次,新的家族墓上刻的是“李家墓园”。
“大姊,你知道‘陇西’两字代表什么?”
父亲问她。
“代表李家呀!李家的墓不都刻着‘陇西’二字,表示我们的祖先是从陇西迁移过来的呀。也就是我们的祖地呀。”
“你知道陇西在哪里?”
“在大陆呀!”
“大陆的哪里呀?”
“……”
“元玲,告诉大姑陇西在哪里?”
“在甘肃。”
“在甘肃……”
“你知道甘肃在哪里?”
“好了,好了。你们读书较多,就要欺负人。反正,我也不会埋在这里。”
大姑说,转头过去看看小姑。
小姑丈回中国去了,一年回来一次,回来领退休金,而后再去中国。在台湾只住四个月,也就是在中国的时候有八个月,占了五分之二。听说,在那边还有二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父母在他可以回去之前,就已过世了。他回去,还为他们建造一个家庙。
“你会埋在这里吗?”
“不会。不过,我也不知道要埋在什么地方。”
小姑说,低下头。
建墓师依序把五个骨瓮放到墓屋里。最上面的是男女二位阿祖,旁边两侧是阿公和阿妈。男女阿祖是放一起的,阿公和阿妈却分在阿祖两侧。他们为什么不放在一起?
依照建墓师的说法,这样才能放更多的骨瓮。如果一代一层,只能放五代,阿祖,阿公和阿姆,就已占了三代,剩下的,只能供应两代。
不是放在阿妈旁边,另外一侧,阿公的旁边留了一个位子给大伯。
那新的大姆呢?
大伯和新的大姆,现在住在一起,不过他们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在户籍上并不算是正式的夫妻。实际上,他们都是再婚,大姆有自己的子女。
“我们要住在一起,要互相照顾。”
大伯和大姆都这么说。
“怎么这么小?”
大姑看着右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家族墓,看起来像庙宇,有中型的土地公庙那么大。
“原来的地,只有这么大。”
父亲说。
的确,周围都是坟墓,紧紧靠在一起,无法扩大。
“有够了。里面有四十个位子,现在子女少,四十个位子,不够十代,也可以用八代了,一代二十五年,也二百年了。有够了。”
建墓师拚命说,又点了一根香烟。
二伯话最少,从头到尾,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二姆没有来,因为堂姊在美国生产,她去照料了。
不过,元宏堂哥有来,还带了女友来。元宏堂哥曾经带女友来看过母亲。二姆出国前有交代他,叫他有事要找三婶,也就是母亲商量。他预定要在九月间结婚。
大伯的小儿子,元德堂哥生病,没有参加,他的大儿子元福堂哥有来,还带来了两个小孩,一女一男来参加。
我的大哥元昌,当导游,目前人在日本。二哥元裕,在美国读书。
“小心喔。”
大堂哥的两个小孩,在墓地里跑来跑去。那个小男孩已跌倒三次了。
“姊,你将来也要放在这里?”
“我才不。”
“为什么?”
“我是女孩子。”
“为什么女孩子不可以?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不能像阿祖他们,放在一起?”
“大概是吧。”
“姊,我的狗狗死了,要放在里面?”
“也不行。”
“为什么?”
“它不是人。”
“呃。”
他应了一声,看来,他还是不懂。
“元玲,你读什么?”
上香之后,大姑他们在烧纸钱,二伯忽然走到我的身边问我。
二伯最像阿公,有一头虬毛,人也比大伯、比父亲高大一点。
“中文研究所。”
“硕士班?”
“对。”
“师大?”
“对。二伯也是师大毕业的?”
“对,那时候叫师院。你的论文写什么?”
“《十日谈》和《聊斋》的比较研究。”
“什么?”
二伯显然有点吃惊。
“为什么?”
“自从上研究所之后,我一直想着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什么位置。”
“快来烧银纸了。”
大姑转头过来,喊了一声。
“你,以后要教书?”
“对。不过,如果可以,我还想攻读博士。”
“要走研究的路?”
“我也曾经想过,也许,我也可以尝试创作。”
“你的计划真不少。”
“二伯,听说你喜欢画画?”
“你怎么知道?”
“母亲说的。”
母亲和大姑他们在烧银纸,银纸的纸灰扬起在空中。
“二伯,你画什么?”
“海报。”
“什么?海报?”
“电影院的海报,也叫看板,就是把印好的小海报,画成大海报,挂在电影院上面。”
“呃。”
我有点意外。
“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呢?”
“主要是画静物,画风景,也画人物,不过不多。”
“画插图吗?”
“还没有想过。你为什么问?”
“我说我想创作,想写剧本、小说。其实,我最想写童话。”
“真的?你写童话,我可以帮你画插图。”
“真的?”
“当然是真的。不过,那很不一样。”
二伯说,从口袋拿出纸和笔,迅速画了起来。
“你看。”
二伯画了一只蚂蚁,有动作,有表情,看起来好像在指挥,额头还洒下汗水。
“二伯,你好像在画我?”
二伯只是笑着,没有回答。
“二伯,我已决心要写童话,你一定要帮我画插图。”
“好呀。”
“快收好,可能要落雨了。”
建墓师说。山顶上的云,已罩到头上来了。◇
——节录自《红砖港坪》/ 麦田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余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