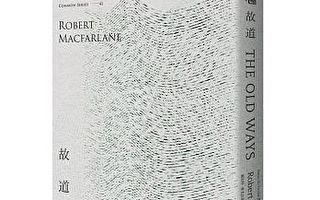小说:英格的孤岛

1938年11月9日,纳粹发动了捕杀犹太人、砸毁犹太商店的全面破坏行动,史称“水晶之夜”。方克斯坦家的糕饼店也未能幸免于难。
方克斯坦太太当机立断,果决地采取行动:一方面把先生从集中营里救出来,一方面想办法买到了船票,夫妻俩带着独生女儿英格,从布兰登堡出发,踏上了未知的流亡旅程,前往当时唯一张开双臂接纳他们的城市──上海。
当爸爸妈妈开始在十里洋场为了生存而奋斗,小英格则开始了她的冒险之旅:探索陌生的城市、融入陌生的人群、战胜陌生的语言,甚至灵活地运用中国朋友伊娜送她的筷子大啖中国菜。
方克斯坦夫妇视流亡上海为“困坐愁城”;但对英格而言,八年的“客居”却让她拥有了新的家乡。
〈又一场战争〉
一九四一年|上海(岁次辛巳‧蛇年)
自从跟三毛出游过一次后,英格食髓知味,迷上了城市探险活动。但因为不可能常常过生日(一年过了两次,英格已经非常感谢),她的导游又不能如期望中地经常陪她,英格只好独自出征。
身为“无惧的探险者”,而且又已经十三岁了,当然可以做个独行侠了!大家既然都那么放心,让她一个人每天“跋涉”到虹口去上学,那也没人能阻止得了她,在固定往返的过程中,将活动的范围稍稍往外扩张一点。
最让英格留恋的还是黄浦江,尤其是一大早,当清风拂面,波浪和缓拍岸。有一个公园直接座落在江边,她每次坐电车经过时都可以看到。它位在一个三角地带,就是苏州河汇入黄浦外滩的转角上。
在一个美丽的初夏早晨,英格没考虑多久,就决定在外白渡桥那一站下车。翘掉一小时希伯来语课,实在不是什么损失,找到一个让校方相信的借口,也不会是什么难事。
在公园入口的地方,她先仔细阅读了一下牌子上整整十大条的入园规则,上面写着:这座公园是专门为“外国侨民”保留的,狗不准进入,脚踏车禁行,保姆务必要把小孩看好等;还有,只要自己乖乖走在路上,不要乱跑,而且“穿着得宜”的话。
英格瞧了瞧自己一身上下:没问题,今天穿的是制服,她应该是被准许进入的。于是,她便施施然信步绕过一大清早还空无一人的音乐凉亭,慢慢朝河岸大道上的一张座椅晃去,在那里有最佳的视野,可以观赏外滩的风光。
眺望了一会儿江上往来的船只,一艘斜着船身,横渡江面的小船,引起了英格的注意。只见一位船伕在船尾摇着橹,引导着船朝东岸行驶。对岸是一片平坦的田地,除了一些工厂的仓库和厂房外,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可看;至少和矗立在外滩上那些雄伟壮丽的建筑相比,中间的差距可是天壤之别。
英格必须眯起眼睛,才能勉强不让小船离开视线,她看到船上的乘客都在对岸下了船,但马上又有一批新的乘客上了船,然后小船就又悠悠晃晃地从对岸划了过来。
啊,是渡船!英格惊喜的发现。
倒不是她想去造访荒凉无趣的浦东,而是坐这样的渡船一定不会贵,但却又终于可以到江上游览一番;这可能是英格唯一可以负担得起的“水上郊游”活动了。她牢牢记住了小船在浦西这边靠岸的地方,随即站起身子,搭上了下一班电车。
这个公园我不会再来了,英格在去学校的路上想着:没有中国老百姓在那里练太极拳,没有摊贩在卖茶叶蛋或其它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小孩在放风筝,一点儿也不热闹。
一个地方既不“热络”也不“吵闹”,那还有什么乐趣可言?我已经太“中国”了,英格心里想;特别为外国人保留的公园静地,对我来说已经太无聊了。但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在那里发现了有渡船可搭,而且已经计划好了她的下一次出游。
***
当英格抵达学校,例行的“早点名”当然已经过了。每天早上全校师生都要齐聚一堂,接受点名,被叫到名字的学生必须大声回答“到!”,以示在场;可惜英格没有死党罩她,帮她代应一声。
“我今天搭的电车,钩住上方电缆的集电弓老是滑出轨道。”
英格向哈特维希太太解释迟到的原因。
“我们必须等司机一次又一次地把它挂回去,才能继续往前开,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哈特维希校长上下打量着英格,眼中不无怀疑,但最后只用英文说了句:“请你用英文再说一遍,好吗?”
“喔,对不起,哈特维希太太,我忘记了。”
英格马上表示了歉意,并用英文又说了一次谎。
***
不久学校就放假了,英格决定要实践她的计划。不过这次出游的造型,不再是“穿着得宜”的在校学生,而是一身轻便的中式夏装。
她搭电车抵达外滩,很快就找到了坐渡船的地方。在一座木造的小桥头上,已经有好几位乘客等着上船。
“来回一趟多少钱?”
英格用中文询问票价,并被告知一趟来回是三毛钱,相当于买两张葱油饼(英格现在已经很习惯,以具体的吃食来换算价钱)。用两张葱油饼就可以渡河一趟再回来,值得一坐。
渡船靠岸了。从船上下来的乘客,肩上都挑着巨大的箩筐,或装着蔬菜,或关着活鸡。英格等他们都上了岸,才小心翼翼地走过搭着的木板,登上了摇摇晃晃的小船。
她把船资数给船伕,侧身挤过同船的渡客,坐定在一条狭窄的木板条上。然后不可避免地,再一次上演了“你问我答”的戏码,这出戏英格已经和黄包车伕及卖菜太太们,不知预演过几百次了。
“你是哪国人?”第一个问题总是问她从哪里来的。
当然,谁叫她金发蓝眼,要不引人注目也难。
英格总是很自豪地跟人家说,她是来自“美德之邦”,是从“德国”来的。就和她中国名字的情况有点类似,中国人很尊重地选了一个高标准的“德”字,来称呼“Deutschland”,可惜这与实际的情况并不一定相符。
“你今年多大?”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个问题。
英格从经验中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稍微蒙混一下,因为中国人很难猜测西方人的岁数,反之亦然。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对于这个问题,英格的回答总是能马上赢得好感。一个能做出好吃糕点的烘焙大师,是任何社会都欢迎的成员,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用。
但当对方提出“你们为什么来上海?”这个问题时,情况就有点儿复杂了。
英格的回答是,因为她的国家正在打仗,但同船的人全都善意地对她笑着说:“但这里也一样啊!”
第一波好奇心暂时止住了。由于“祖国都在打仗”这基本的共同点,英格从所有的人那里都获得了出游的口粮。
现在英格终于可以靠着船舷,好好享受这趟水上之旅;她仔细观察船伕如何闪躲来往的船只,让风肆意吹过自己金色的发梢。可惜横渡黄浦的航程太短,他们转眼已经靠岸。
新认识的朋友热情地和她道别,叽哩呱啦地说个没完,接着另一批带著作物要去市场卖的农夫,又装满了一船。
英格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她每天在市场上买到的新鲜蔬菜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她终于看到了位在这座大城对岸的农田腹地,上海的补给站。
回程中,外滩一览无遗地展现在眼前,英格再次感受到那份雄伟壮阔的气势,就跟两年半前她抵达上海的时候一样。当船上的“问答”游戏又要开始时,英格没有兴致再玩一次了。她想要静静欣赏一下江上的风光,于是只耸耸肩,用中文回答了一句:“听不懂。”
问题解决了。但是,中国人却不会忘记关照最重要的一件事:“吃饭了没有?”即使是不会说中文的老外,也不能饿着肚子。
于是英格不仅“心满意足”,还加上“肚满胃足”地从她那充分值回票价的泛舟之旅,回到了位于静安寺路的家。
虽然三毛没有什么时间和英格一起再在城市中四处探险,但却谨守承诺,在荒废的哈同花园里固定教授她功夫。这样的坚持,自然看到成效。他的学生每天在后院里勤奋练习,现在的身手已经不容小觑。
“很好。”
当英格准确地识破了他虚晃的一招,从容不破地避开,一向吝于称赞的师傅,也不禁脱口叫好。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已经不再是个小不点儿;眼前在跟他对打的,是个身材高挑,已经逐渐呈现女性体态,几乎长得跟他眼睛一样高的大女孩。
“你得想些新花样了,师傅,”她嘲笑着对他说:“这一招我早就知道了。”
这话岂可容徒弟再说一遍?身为师傅的权威,三毛绝不容许英格质疑。
疾如闪电,他以拳和腿对英格的右侧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逼她为了闪避,不得不松动下盘。这一招果然奏效。当英格意识到那只是佯攻时,为时已晚,三毛已经牵制住她的左脚。现在要撂倒她易如反掌,他用左手缓缓对她的肩膀施压,使她的身躯逐渐朝后仰倒。打得兴起的英格让自己的身体全然放松,整个人向后倒下,仰躺在柔软的草地上。
这一招三毛可完全没有料到,他原先预期英格至少会抵抗一阵。这下过剩的推力带着他的身子也不禁往前倾倒,最后同样着地柔软──倒在他学生的身上。
为了化解尴尬,两个人开始放声大笑。三毛一个翻身,马上站直了身子,他将英格一把从地上拉起来,试着将局面变成教学的情况。
“好,我们现在马上再试一遍,这样你才知道,刚刚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于是两个人再次摆好对打的姿势。英格心里其实清楚得很,刚刚她是哪里做错了。但她现在也很清楚,和三毛一起躺在草地上,被他那温暖厚重的身体压着的感觉,有多好。
所以,当三毛再次使出先前的那一招,英格也故意又犯了和先前一样的错误。于是两个人又都摔倒在草地上。这次三毛也没有马上爬起来,好像在考虑要不要放弃这个不受教的学生。
“你没救了,丫头。”他最后说。
三毛已经很久没对她说这句话了。以前,每当他想要让英格知道,她有多幼稚、多愚蠢时,就会用这个小名叫她。但这一次听起来,似乎不再像以往那么确定了。
***
上海湿冷的冬天,比英格预期中来得早。十一月底的一天下午,英格照惯例在放学后搭电车回家。她还是站在车厢外固定的老位置上,现在已经冷得几乎快让人受不了;但那里还是有着最佳的视野,可以眺望沿途的风景。
电车刚驶过跑马场,现在转进了静安寺路,当英格正在奇怪,怎么路上的人潮愈来愈拥挤时,耳边突然传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那首耳熟能详的团歌。
发生什么事了?
英格对这首进行曲再熟悉不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就位在西摩路和新闸路的交叉口,也就是“嘉道理犹太学校”原址的对面。要说两个地方是隔壁老邻居,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她“读”幼稚园的时候,常常隔着篱笆偷看他们的乐队在空地上练习。她最喜欢低音喇叭了,那个像支大耳朵般围绕在吹奏者头上的大家伙,发出来的浑厚低音,总是直达脊椎,让全身发颤。
每个星期天,该乐团在军中的主日崇拜结束后,都会在静安寺路上另一个大型电影院“夏令配克大戏院”举行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全上海皆知,深受中西人士喜爱。但今天是星期五,不是星期天啊!
街上拥挤的人潮,让电车行进的速度宛如蜗牛,下一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得了。英格当机立断,跳下车厢,挤进了好奇观望的人潮。
果不其然,迎面而来的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乐队,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一列背着沉重行囊的部队。兵士们的背包上绑紧了行军帽,左肩荷着枪,整支队伍正朝南京路和外滩的方向行进。军乐团的指挥高举着长长的指挥棒,带领着乐团,节奏分明地向前迈进。
但这首一向让英格心情愉快的进行曲,今天听起来却有种不详的感觉。这些士兵要到哪里去?就像童话《捕鼠者》里完全不能抗拒笛声的老鼠,英格想都没想,就一路跟着行军的队伍,又折返往学校的方向走去,一直走到外滩。
那里的人潮更为汹涌,在“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码头前的广场上,停放着一排排黑色的轿车,从车上插着的旗帜可以看出,都是各国使节的座车。
黄浦江上停泊着两艘美军的运输船:一艘是“麦迪森总统号”,船上已有很多士兵不断向岸边的群众挥手;另一艘是“哈理森总统号”,海军乐团的先头部队正在分乘小艇,准备登船。
英格鼓足了勇气往前冲,追上了走在乐队尾巴梢,没有太多表现的大鼓鼓手。她一边踏着跟队伍一样的步伐,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用英文问:
“你们要去哪里?”。
“去菲律宾。”
“你们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
英格的心情一下子沉入了谷底。
这是怎么回事?原本跟英国人一起维护公共租界安全的美国士兵,现在全部要离开上海?
一定发生什么事了。眼前这出让人忧心的撤军戏码,英格不想再看下去。她调转头,搭上了下一班回家的电车。
拥挤的人潮这时候也已渐渐散去,英格最后是用飞奔地跑回家,但当然还是比平时晚了很多。
方克斯坦先生早已收工,夫妻两正等着英格吃晚饭。
“怎么现在才回来?不知道我们会担心吗?”
妈妈语带责备地问。
“那些美国海军!”
英格结巴地说,完全没有理会妈妈的问题。
“他们全都上船到菲律宾去了!现在谁要来保护我们呢?”
“你说什么?”
整天待在烘焙坊里的爸爸,竖起了耳朵。他知道女儿这些日子以来,相当注意政治局势的变化。
当妈妈正要继续训诫英格时,他出声阻止:“让她先说,玛丽安娜,这事情很重要。”
于是英格继续说下去。父亲的眉头随着她的描述,愈皱愈深;对女儿提出的问题,他没有答案。
日子一如往常地过去。除了在虹口的巷弄间,增加了更多巡逻的日本士兵外,自从美军敲锣打鼓地离开上海后,这一个星期似乎没有其它的变化。
至于英国的步兵,大家后来也都知道,早已经在好几个月前就从虹口及新加坡撤走了。所谓世界两大强权在上海保护租界的军力,就只剩下两艘炮艇还停靠在黄浦江边:一艘英国的“北特烈号”,一艘美国的“威克号”。
***
星期天夜里,也就是十二月八日星期一的清晨,英格被一阵轰隆的炮声吵醒。原本蜷曲在英格臂弯里的来福,也从梦中惊醒,一溜儿烟似地躲到沙发底下去。
什么人在这个时候放鞭炮啊?现在既不是西洋新年,也不是中国新年;难道十二月也下雷雨吗?还是又有什么特别的拜拜活动,非要在一定的时辰驱鬼迎神的?
英格听到隔壁房间里已有动静。她看看闹钟,四点刚过,爸爸已经要去烘烤房准备开工了。打着哆嗦她走到一扇面朝东方的天窗前,向外眺望。远方天际微微泛着红光。怎么,太阳已经要出来了吗?通常这个时候在冬天,太阳根本见不到踪影的。英格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轻声叫唤父亲,希望不要吵醒妈妈。
“老爸,发生什么事了?”
方克斯坦先生走进房间,把门在身后关上。
“你怎么已经起来了?”
“你没有听到炮声吗?还有,东方的天空好红呢。”
自从生活在上海后,英格也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学会了如何辨认方位。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先到费德勒家去一下,看看他们起来了没有。你跟你妈留在家里。”
父亲坚定的语气让英格意识到,糕饼大师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她从窗户看着父亲朝烘焙坊走去,不一会儿就和费德勒先生又一起出现,两个人匆匆离开后院,消失在车道入口。
随后晓春也出来了,显然今天的早班时段,要由她和中国员工来接手。
英格把来福从沙发底下逗弄出来,紧紧抱在怀里,重新躺回床上。灰暗的晨光从天窗透进来,她看到自己呼出的白烟,飘散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
这个时间最可怕了,爸爸当初不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抓走的吗?不幸的事情似乎都发生在清晨,所以最好赶快把它睡过去就算了。
问题是,她心里充满了不安,想要再睡着已不容易;但她又不想叫醒母亲,因为也许根本就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来福好,天塌下来也与它无关。
小公猫把头枕在英格的胸前,一边听着小主人的心跳,一边满足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英格用指尖顺着它那一身虎斑似的毛,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就这样,两个小家伙终于又都进入了梦乡。
***
英格一如往常地被闹钟吵醒,当她昏昏沉沉拖着脚步,踏进隔壁的房间时,突然发现爸爸正轻声地在跟妈妈说话。
“咦,你怎么在这里,没去烘焙坊,老爸?”
然后她渐渐忆起了一大清早发生的状况。
“对了,今天早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英格,我们这里恐怕也要打仗了。你今天留在家里。”
打仗?不用上学?英格既惊慌又惊喜,她本来就还一片浑沌的脑袋瓜,现在更纠结不清了。
于是爸爸开始讲述早上经历的事。英格一下子全醒了过来。
两位糕饼大师搭上最早的一班电车,往外滩方向前进。这班车载着的,通常是最后一批刚从酒吧或妓院出来的寻欢者。当电车应该在“华懋饭店”向左转,然后继续朝外白渡桥行驶时,却被一群荷着枪、上着刺刀的日本士兵拦了下来。
车子不准再往前去,所有的乘客都必须下车。在外滩的河岸大道上,两个人看到了不可置信的一幕:整条黄浦江好像都在燃烧,水面上红烟密布。他们花了好一会儿功夫,才弄清楚起火之处。
英国的炮舰“北特烈号”身处烈焰之中,英国水兵正想办法要从下沈的炮艇中往岸上逃;很显然的,还有很多受伤的士兵在船上。而当他们朝美军的“威克号”望去时,心里开始有数大概发生了什么事。
在那艘美军的炮舰上,日本军旗正大辣辣地飘扬着,日本士兵则在甲板上不断来回穿梭。映着昏暗的天光,日本军舰“出云号”巨大的身影,极具威吓地矗立在河道转弯处。
“日本人一定是趁着天黑,从他们停舰的地方就直接把两艘船给轰了。”
方克斯坦先生语带猜测的说。
“这简直就是偷袭,而且双方的实力也相差太多了。‘出云号’是艘装甲巡洋舰,另外两艘只是小小的炮艇,艇上的兵力还被调走了大半。日本人等于是把军舰开到隔壁攻击,然后就强行登上了炮艇。”
“但日本人怎么敢去和英、美两个世界强权挑衅呢?”
方克斯坦太太不解地问。
“因为他们都撤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英格忍不住激动地嚷了起来,毕竟她亲眼看到了部队撤退的那一幕。
“现在真的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对付日本人了。”
“我想,你说的恐怕都对。”
父亲对女儿的话表示赞同。
“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日本人正从飞机上空投传单。”
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窝得皱巴巴的纸,把它铺平在桌面上。英格看到上面写的有中文和英文。
“他们要让我们知道,日本天皇已经跟英、美两国宣战了。十点的时候将会向公共租界区的居民宣布,日本已经正式占领、接收了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地盘。日后我们将属于‘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而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着想,至少上面是这样写的,请大家保持冷静,继续正常生活。话虽如此,你今天还是不准给我去学校,小鸭子。”
对不用去学校这件事,英格毕竟没有办法真正高兴起来。◇(节录完)
——节录自《英格的孤岛》/ 左岸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余心平